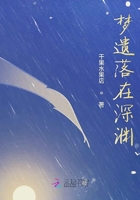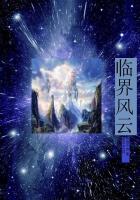陈晓诗不知道,是不是有的人天生就像她一样。害怕周围的环境改变,害怕别人谈论她,害怕别人去猜测她,甚至害怕一个陌生人对她的注视。
她一直都觉得这样是病态的,但是,改变很难,尤其是当她连改变自己都感到畏惧的时候。就像她认为做白描这样的人很轻松,然而真的让她像白描一样顶着大家的议论还要我行我素,她怕是怎么学也学不会的。
越来越像她的,是伊琳。她开始听说别人在传她喜欢程蓝青。她确实害怕自己隐藏了那么久的秘密被当做笑话来说,她害怕别人给她编织更戏剧性的传言。她从前都不在意被评论的,可是现在,她知道害怕了。从那次陈晓诗被传奇怪的传闻开始,她了解了,大多数人对于别人的看法都不是自己生成的,都是在外界的引导,熏陶下形成的。而且,大多数人讨厌的人很多也是好人。那么,会不会有一天,所有好人坏人都同时针对自己,自己被那样对待。
她应该是容易莫名其妙地被讨厌的那一种吧。从前有陈晓诗和她在一起,她不需要和不必要的人谈话,交流,就那样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封闭起来,就留一个小小的圈,够她们存活这样就够了。可是有一天,自己因为害怕陈晓诗看穿自己的嫉妒,太害怕被她看穿了,害怕她觉得自己不一样了,把她也推出这个圈子。最后自己就在这个只有自己的圈子里痛苦的活着,不管周围是喧闹也好,寂静也好,不管自己是难过也好,绝望也好,也都这么活着。最后有一天,发现,自己已经不能改变了,她丧失了改变自己的能力。
分数条到了,那一直都是残忍的东西。罗列着数字,然后把这些坐着的人们分为各种等级。而奇怪的是,被这样分等的人却没有因为分数条的存在而悲哀,而是因为比别人高几分而得意,或是比别人少几分而消沉,他们从来没有想想,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习惯被以这样的方式定位了。。
伊琳看见自己的名字仅仅靠着班里的最后一名,心里紧了一下。不过,好在还是在这个班呆着,就算是倒数也要在这呆着,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去适应一个新的班了。
同样纠结的是陈晓诗,她看过这些陌生人谈论她时眉飞色舞的神情。那一刻,她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有异能的动物一样,为了给无聊的人消遣用的。白描帮她把桌子椅子,还有书都搬到A班去了,她深吸了口气,低了头,准备走进去时,却被白描一把拉住。
“看看这个教室里坐着的人,你有做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么?”在后门白描指着他们,“就算他们有各种版本揣测你,把你说的十恶不赦,那又怎么样呢?就算你是那样的人又怎么样?他们顶多花费大把的口水,跟在你后边,想要看你难堪的样子,满足他们凌弱的心理,然后你就自愿充当这个被欺负的弱者么?你凭什么这样啊?”
陈晓诗沉默了许久,抬起头看着白描,“我不是弱者”
气氛从她进来的那一刻,就开始变了。
各种各样的神情,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米兰此时正在发英语卷子,看见这些孩子的表情,突然感觉有种莫名的恐惧,什么时候,十七八岁的孩子脸上,开始有了这些表情。为什么大人的语气,动作,表情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孩子身上了。
“E班来的啊?欢迎欢迎!诶呦,从来没见过E班的人进来这的,得吃多大的苦才能爬到这个位置啊,太不简单了。”一个男生站了起来,满不在乎的劲儿,自以为吊儿郎当的潇洒,想把大家带领到一个正确的“立场”。
“所以,听起来,似乎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我能进这个班,都是托您的福了。您不用站起来,太客气了,不过,我为什么不认识您呢?”陈晓诗扬起头,笑意盈盈,“只是想讽刺我是E班的吧,一辈子没见过E班的人长什么样子吧?那今天我来教你,E班的人,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一个鼻子,还有一张嘴巴,很神奇吧?大自然真是太奇妙了!”陈晓诗坐到了最后一排,“下次忘记了E班的人长什么样子就过来我这看看,我可以借给你放大镜,看看我们到底是怎样的生物,还有,会不会变异?会不会吃人?”
陈晓诗觉得讨厌自己的人肯定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坐着这些人们大部分都和刚刚的男生,抱着同样的心态。米兰看着那些A班的人,这些没有人情味的,每天只知道努力学习,然后用分数作为嘲笑别人,伤害别人武器的人,恰恰以后可以上好的大学,接触上流社会,操纵着普通人的生活。而那些善良的孩子,最后却往往看着他们的脸色,努力的生活,还是要比他们低一等,最后,他们会这样安慰自己“上学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这么嚣张,以后活得果然不错,这一切都是注定了。”
可是,真的是这样么。
陈晓诗坐在座位上迎接着各种回头看她的,或好奇,或厌恶,或鄙视,或轻蔑的眼光,还是很不习惯,不过已经不是害怕的快活不下去的时候了。旁边的白描已经拿出书来预习了,看见她不被干扰的时候,陈晓诗总会很安心。
透过手机屏幕的镜面膜望着神情复杂的陈晓诗的程,总有想保护她的冲动,不管什么时候。别人嘲笑她是E班过来的时候,她会想起是她妈妈把她弄去E班的,这样的她,该多难受啊。他心痛了一下,短暂的,却深刻,真实的,痛了一下,像有什么扎了一下似的。
陈晓诗,现在,你的感觉也是这样么?
伊琳望着他专注的神情,“心痛不是这样的,心痛是一枚长长的针,扎进去的时候,疼一下,拔出来的时候,当它与你最脆弱的肌肉摩擦的时候,那个过程才是最痛的。你一直不知道吧。”伊琳在心里悄悄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