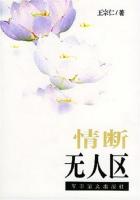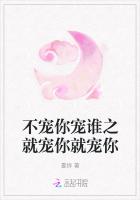老家的家
女儿雨点儿:妈妈,你小时候最喜欢什么?
我:穿新鞋,看沙子上的新脚印。
雨点儿:长大呢?
我:梳两条长长的辫子。
雨点儿:现在想干什么?
我:变成你,重新做女儿。
七月份的娘家之行,是出嫁以后最久的一次——整整一个月。到家后,对一切恍然有隔世之感,但不到一分钟就习惯了,像是乘着一束光一下又回到了十多年前。
每天早上,小城的高音喇叭依然放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和童年时一模一样。外面的世界已经把各种流派、歌星淘汰了多少次了,可这里还是一如往昔,像是专门为了给我亲切。
早起的老父亲把“新闻联播”放得震耳欲聋,母亲大声“嘘”着,让他关小音量,不要吵醒我们。父亲有些耳背,听不清楚,直到母亲冲过去,他才恍然大悟:“啊?”母亲压低嗓音嘁嘁嚓嚓数落着,那声音像麦克风里的耳语,更具穿透力。机子关了,老父亲踮着脚在屋里踱步子,嘴里唱着老歌:“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并按照他的感觉切分那些音符,把歌词念成韵白的味道,唱得快乐而有特色。
我禁不住在被窝里哈哈大笑起来。有时我有种感觉,好像正在经历的某个时刻和很多年前的某个时刻分毫不差,甚至完全是一种重复,一个动作、一种衔接、一幅场景都一模一样,你禁不住要向后看一看,想要抓住它,像猫要抓住自己的尾巴一样。那是一种瞬间的幻觉。可我在卧室里听到的爸妈演出的那生动的一幕,的确是十几年前某个星期天的早晨的重复,那语言、声调、气氛、结局都如出一辙。只是那一次我在发脾气吼叫,这一次我却开心大笑。
我在父母的身边长到十九岁,他们始终像空气一样环绕身旁,那分舒适、习惯,与生俱来。后来离开了家,走进大学、走进单位、走进小家庭,只感到身上的分量越来越重。一个毫无顾虑的少女成了一个多角色的成人,是同事们的同事、丈夫的妻子、女儿的母亲、公婆的媳妇,这么多的头衔都不是虚设的,每一个都实实在在,沉甸甸的。
回到父母跟前重新做女儿真好,我觉得女儿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角色。
住在父母的家里,无论是勤勉还是怠惰,无论是热情还是沉默,也无论贪吃还是嗜睡,父母永远都认为那是最有理由的,最必要的。即使每日里什么都不做,游手好闲去公园洗树叶,也能奇怪地从他们的眼里看到褒奖和满足。父母的心像个无形的容器,专门为了容纳女儿的,比天还大。在这样的空气里我的每个细胞都像躺在水里游泳,它们在唱着我能听到的歌:“世上只有妈妈好……”
我自己的女儿雨点儿已经六岁了,在老师面前是个聪明听话的学生,在小朋友中是个宽容可爱的玩伴,在生人面前是个腼腆文静的姑娘,在爷爷奶奶膝下也是最乖巧伶俐的孙女,就连在喇叭花面前她都温柔得一如花仙子,抚啊,闻啊,凝望出一腔的深情。可只是在我们——她的父母、她最亲近的人面前,又要发脾气,又要使性子,一句话不投机便转身不理人了,好端端地想着法和你别扭,冲着你端给她的牛奶说:“你烦死我了!”有一次她甚至嚷着:“我要让大灰狼吃掉你们!”好像你不是她的父母,而是她的天敌一样。这让我很伤心,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凶。我本以为她会对我们最恭敬、最体贴、最温柔,就像我期望的那样。把这种失落说给老公听,他嘿嘿一笑道:“你都快老了,在父母面前还不是那样?”
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这才真是骑着毛驴找毛驴,还一直找不到呢。
父母的家是我身心的栖所和老家,是我终极的慰藉;而我也该成为女儿的栖息地,任她在上面打滚、撒欢儿、翻跟头,哪怕弄得一片凌乱。
房东
女儿长到五岁以后便常常对我说:“妈妈,我什么时候能有一间自己的小房子?”
那时我们一家三口住二居室的单元房,一间做客厅,一间当卧室。女儿睡在卧室自己的小床上。因为还小,我没考虑让她单独睡一间屋。可她却一脸天真地说:“客厅当我的房子吧,你们要用,就向我借。”
可我们除了睡觉,总得借她的客厅活动,她这个小房东的主权也就名存实亡了。她又问:“妈妈,究竟哪间当我的房子呀?”我知道她并不敢单独睡,只是想有一方自己的领地,完全是心理上的需求。客厅是不行了,卧室三个人都得睡,厨房又是我的地盘。无奈之余,我玩笑道:“那就厕所吧。”她虽一脸扫兴,却没拒绝。
女儿在卫生间里时常常是最自在的。这个平时性格内向的小姑娘,只要一关上门坐在小便盆上,就旁若无人,兴致大发,自己编自己导,说她的说,唱她的唱,把幼儿园里发生的事很立体地再现成一台人物众多的大戏,热闹得很。那时,她完全是个忘我而自由的小人儿。
六一儿童节,我送给她一把四色小雨伞,她爱不释手,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我对她说:“今天妈妈要给你修一间漂亮的小房子。”她很兴奋,格外顺从地任我摆布。等她躺好了,我撑开那把小伞,斜靠在她肩旁,然后用一个橘红色的毛巾被棚上去。她立刻喜不自禁地笑出声来,还说:“留个窗户,留个窗户。”
暑天七月,我带她去看姥姥。姥姥家有一张分上下两层的茶几,女儿便常常钻进下一层,躺在里面玩。她一定把上层当做天花板了,她认为已经睡在自己的小房子里。一天午睡时,酷热难当,气温接近40℃。我去客厅看睡地铺的女儿,但只有她的小表姐睡在地上。我正纳闷,只见双层茶几从上到下严严实实地盖着一条大毛毯,我揭开一看,女儿光溜溜地躺在下层昏睡着,浑身像水洗的一般。我责备小表姐:“你真不懂事,这样捂着,她会给热死的。”小表姐嗫嚅道:“她说要我给她搭个小房子。”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有了搬家的心思,只为了女儿。
女儿大了,渐渐渴望着独立,她不仅需要热热闹闹的大环境,也需要一个独处的小天地在那里做她想做的一切。
看女儿的画就会发现,她特别喜欢画房子。她画的房子都是她精心设计的,有苹果城、茶杯屋、靴子房、蘑菇楼等等,形状各异,花样翻新,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个房门口都摆着一双拖鞋。我想那房子里一定纤尘不染,别人是不便常常进去的。
后来,我竟发现老公也爱守在厕所里不出来,仔细一想,他早已如此。问他待在里面干什么,他就不耐烦:“让我单独看看书、想想问题行么?”其实我又何尝安静过,我常常希望他们父女两个一起外出,让这房子归我,只要三天五日都行。
一天我和老公在街上的小饭馆里等饭。从窗口望出,只能看见一些脑袋移来移去,像是被人用杆子挑着走,男女老少,来来去去。那些脑袋看上去个个都装得满满的,重重的,可它实际上却是每个人的一方自由无限的空间,一间与生俱来的大房子。
我不禁想:我们每个人都像有一个脑袋一样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就好了。
“我不是动物,我是人物”
女儿上小学了。入学的前几天,她嘟噜着脸,不让提及此事一个字,不小心说了,她便像猫被踩了尾巴似的,完全是一派如临大敌的样子。
第一天送她去学校,刚走到教学楼门口,上课的铃声突然响了,所有的孩子都像受惊的小动物一样突噜噜往教室里奔。女儿一怔,接着回过头来看我,脸上有新鲜、惊奇、兴奋,好像还有点嘲弄,那诡秘的一笑所传达的复杂心情实在是难以言传。
这天放学回到家,她伏在我耳边说:“其实上学挺好玩的。”我笑着推开她,使劲点点头。小孩就是这样,什么话都当悄悄话说,哪怕屋里只有我们俩,就好像她对我的这只耳朵说话,怕我的另一只耳朵听见似的。
上了几天学又对我说,老师让做1个大口袋,10个小口袋,50个圆纸片,100个小棍棍。我故意说:“烦不烦哪!”这回她显得特别通情达理:“妈妈,你别烦,上学就是这样的。”
一个多星期后,她自己跑去上学了,不再让家长送。接着就能自己买冰棍、打醋、打酱油了。星期天早上,她提前起床出去买了面包,冲上速溶咖啡,居然在床上为我这个“贵妇人”开早餐了。我按捺住自己的惊讶,假装这一切都很平常。可我的心里却在想:怎么刚给学校送去一个懵懂小姑娘,就还来一个仙女。
刚开始学的是拼音。借助拼音朗读,常常使女儿哭哭笑笑的。哭的时候是因为读得太苦,鼻子尖上全是汗豆豆,她喊着:“我真是苦命人呀!”笑的时候是读通了一篇,突然发现读的是个很有趣的故事,就会说:“这蜘蛛可真倒霉,是吧?”那一阶段我常为她伴读,听她那结结巴巴、不断重复的朗读,心里像被猫抓一样难受,忍不住说她:“怎么读成这样?我听得心里长毛了!”她再读,读顺了,便问我:“这回心里长的是什么?”“绿绿的小草。”她就高兴了。
拼音日渐熟练后,便常对我说:“妈妈,给我一块bù(布)”,“我要一双kuài(筷)”,“今天我得了huā(花)”。看到一个扎独角辫的同学便说人家的脑袋像个“ɑ”,家里的小椅子是个“h”,大肚子阿姨是个“d”,总之满眼满嘴都是拼音。
开始学汉字后,眼睛里又只能看见汉字了,广告牌上的、罐头瓶上的、电视机里的,只要有点眼熟的,就照猫画虎地念。一次看到一个招牌上的“奖”字写得上下脱了节,便喊:“快看呀,这个字的裤子快掉了!”那时识字不多,但胆子很大,经常搞得错误百出,把“陈冲在好莱坞”念成“陈冲在好菜岛”,自己浑然不觉,却把她表哥上学时的一个笑话拿来讲给同学听:“我哥哥把‘调度就是命令’念成‘调皮就是命令’,哈哈哈哈……”,笑得好不开心。
再以后,女儿常常满脸官司地思考问题,老成的表情配上那张稚嫩的脸,真让人不胜同情。一日,她突然说:“妈妈,我没有生物钟。”“你有,每个人都有。”“我不是生物,怎么会有生物钟?”她反问我。“生物分植物和动物,你是动物,高级动物……”没容我说完,她严肃地反驳道:“我不是动物,我是人物。”
除了这些学习的成果,这个幸福的小娃娃居然还被唤起了忧国忧民的热心肠。一次问我:“妈妈,你知道谁是石三伢子吗?”“是你们班的新同学吧?”“不对。”“咱们楼上的孩子?”“更不对!”“电影里的人物?”她不想再听下去:“是毛——主——席!你怎么连咱们的大救星都不知道?!”搞得我这个老前辈煞是狼狈。学过《刘胡兰》的课文后,她又来了:“如果当时我在场,让我和刘胡兰只死一个,我就说:‘我’!”那张小脸仰起来,眼神散开,她在幻想着那个悲壮的场面。我急忙问:“你为了什么呀?”“为了让咱们中国多一个共产党!”
一次学校动员同学向地震灾区捐款,女儿将家里历年积攒的硬币从瓷小猪的肚子里倾倒出来,乐滋滋地带到学校去了。没有多久,我忽然听人说国家回收分币,某一年的一分硬币可值几百元钱。我将这件事告诉了女儿,很有点懊恼折财的意思。可她却一拍小手,两眼放光地说道:“太好了,那灾区的人不是会更有钱了吗!”
女儿的生命就像一株清晨的葵花,娇嫩而灿烂,常常突然照亮我的心,让我把自己的杂念赶走。自从有了她,我便时时得到着这种净化、感染和反省,它来得是那么无心和随意,却带着难以抵挡的力量。每一个孩子的心都像纯金,哪个成年人真正配去教导这颗心呢?
郁闷童年
自女儿雨点儿上学以来,性格日渐开朗,天性中的羞怯、内向已被克服了不少。她在班里虽不能成为轴心人物,但也快乐得像一颗怡然闪烁的小星星。看得出,她正慢慢变成一个生活的热心参与者。
可有一天,雨点儿的脸上挂着我从未见过的沮丧。她坐在镜子前木然地端详着镜中的自己,然后轻轻地举起双手放在脸颊上,突然动作夸张地撕弄着自己的脸,像要扭曲它、毁掉它。她做着种种狰狞可怖的面目,有时竟被自己的怪样子逗得“格格”笑出声来。我问她在干什么,她突然转过脸来说:“妈妈,你想知道我们的新老师是什么样子的吗?”接着她就开始表演刚才的那一幕,她几乎要把眼角撕裂,嘴唇拉豁了。“嗨嗨,嗨!”我阻止她。
雨点儿疲惫地垂下自己的手,像是做了徒劳无益的事:“我无法使自己变得像新老师那么丑,我最难看的样子也比她好看。”她有气无力地说。
我知道他们这个学期刚换了班主任,大家都很不适应,作为家长,我心里也不无担忧。三年级是小学最关键的一年,学生已从初步认识转到深入理解的学习阶段,本是趁热打铁的好时节,可原来的班主任老师这学期退休了,接班的是一个刚从师范毕业的年轻姑娘。
这个新老师肯定挺难做,一切从头学起不说,所有的言行都有着老教师先入为主的模式做着限制和比较,有五十多双清亮的眼睛做着监督,她再努力也会因为不合老教师的规范而受到学生不自主的抵触。
那天我第一次去开新老师的家长会,亲眼见到了她。大出意料的是,新老师的长相不仅不能用“丑”去“诬蔑”,反而是很美的:身段窈窕,面容秀丽,全身以高贵的黑色为基调,一头齐整的乌发盘在脑后,令脑袋精致而玲珑。
我心里暗暗惊呼:孩子的话真是不可靠。我也一边感到奇怪,一向善于观察的女儿这次何以有如此大的偏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