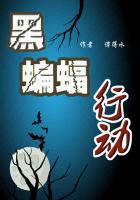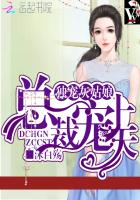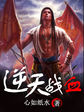两所大学在后来的几百年当中分别形成了各自的学术优势,牛津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多出成功的政治家、首相和名律师,英国有11位首相都毕业于牛津大学。思想家培根也是这里的学生,发现彗星的哈雷先生更是这个学校的骄傲。而剑桥则以在自然科学领域建树累累而闻名于世,它的学生先后有78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就一所大学而言,它的获奖人数是世界之最。达尔文、华兹华斯等都是剑桥的学生。
牛顿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学生,后来又成为这里的教授,他住在这里长达30年,使该校的数学研究达到卓越水平。牛顿曾为剑桥大学设计过一座数学桥,是木头构成的,一颗钉子都不用,完全是利用物理学的各种原理来结构的。后来有学者研究这座桥,把它拆了重建,但再也不能恢复原状了。牛顿是第一个获得英国王室爵士头衔的科学家。
剑桥大学由三十多个学院组成,图书馆藏书无数。剑桥的图书馆享有获得一册英国所有出版社出版的任何书籍的权利,这是少数国家图书馆享有的权利。但我想,每个出版社都会把为它赠书的义务当成自己的荣誉的。
我国上世纪的著名诗人徐志摩曾游学于剑桥大学,他的名诗《再别康桥》就是写剑桥的。康桥是剑桥的别译,而诗中所写的有着“柔波”“金柳”的河正是那条穿城而过的卡姆河,也叫康河,它是剑桥城闪闪发亮的领带。
徐志摩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老约克
在英文的地名里有很多带“纽”字的,就是新的意思,比如纽芬兰、纽黑文、纽西兰等,这说明还有一个这样的旧地名,而纽约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例。它译全了应该是“纽约克”,也就是新约克的意思。我们这一次就去了那个先于美国纽约克而存在的老约克,它就叫约克。
约克是个古老悠久的城市,在历史上曾被丹麦统治过,也被罗马人占领过。罗马人修筑的要塞和古城墙,形成了最早的约克城。古城墙至今遗迹犹存,它使约克仍环绕在中世纪的氛围中。
约克城内著名的约克大教堂耗时250年才建成,是全英国规模最大的哥特式建筑。它以灰色和绿色等深色为主调修建,漂亮而伟岸。虽然它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但依然结实挺拔、完好如新。清澈阳光的照耀使它散发出沉静的光辉,周围的每一棵树都因为站在这样高贵的建筑旁边而显得古意盎然、气度不凡。
欧洲的教堂给人的感觉是,它兼具了人和神共同的灵性和庄严。
在约克的古巷里我没有听到那至今还经常响起的来自中世纪的优美钟声,但我听到一阵微弱凄清的笛声,它像是从一根真正的木器中发出。循声探去,看到一个年轻的女人穿一身黑衣坐在一个街角上吹笛。她的目光遥远落寞,和当下这个时尚世界拉开着隔世的距离。这使年轻的她像一个格格不入的幽灵,以至于我无法判断她内心的情绪:她这样吹笛是因为忧伤还是孤寂,独自坐在街头是为了自娱自乐,或是才艺表现,还是向路人乞讨。
我是一个东方人,没有看懂她向路人昭示的某一种也许明确的含义,但我想她应该不会是为了赚钱,据说在英国,失业的人也有政府救济金,不会挨饿的,况且她躲在寂寥的角落里。
这是我此行唯一有机会关注过的当地人。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不能和那里的人有所交往,让我感到空落落的。我们像走在彩色的空画片里。
小箱子上的自由
我们上次去俄罗斯的时候,曾看到有一些怀旧的人聚集起来,擎着红旗在那里聚会演讲。我们尽管听不懂,但也能感觉到他们中间荡漾着一种红色革命的气氛。聚会者专心地抒发着自己的理想和坚持,而路人们则各走各的路,互不妨碍。这倒让我们感觉到现今的俄罗斯有一种自由的空气,再也不那么压抑了。
按理说,像英国这样的老牌西方国家,更应该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可居然不是呢!在那里,人们的言论也明确地受到限制:政府在一个叫海德公园的地方,专门为要发表异端言论的人辟出“自由论坛角”,允许他们到那里去发表言论。但即便你到了这个地方也不能毫无顾及地开讲,你得先找到一个小木凳子或小箱子,然后双脚站上去,表示离开英国国王的土地,这时你才可以发表不同政见或破口大骂。
这个做法像个认真的娃娃游戏,既幼稚又算有规则,既保全了一点王室的面子,又给国民一个发泄的余地,还是颇有童心的。
时间中的大英博物馆
英国最有名、最值得国人骄傲的财富之一是大英博物馆,它是世界上著名的四大博物馆之一,其他三个是法国的卢浮宫、俄罗斯的冬宫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已经有250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博物馆,拥有将近700万件藏品,稀世之宝数不胜数。在这些馆藏中以埃及、希腊和中国的最为有名。我们在这个异地他乡的国度,见到有这么多在我们本国博物馆也不能见到的中国国宝,我们脑海里出现的最直接的画面就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情景。英国人在历史上到处殖民,侵略、掠夺了全世界各国的大量财宝和文物。
我看到有一个来自非洲的刻有浮雕的精美柱子,从底层一直高耸到二楼上来,整整高达两层楼。类似的木雕、石雕还有很多。
不能想象哪个个人有能力把这么巨大的物件私自运到一个国家,更不能想象哪个个人有能力把全世界上下几千年的宝贵文物弄到自己的国家,装备出一个举世闻名的博物馆。一看这就是政府行为、国家行为。奥地利人斯坦因因为在中国考古成就显赫而得到过英国的国籍和女王加封的爵士头衔。
我参观大英博物馆的时候心里感到特别惊讶:里面的文物摆放得近乎堆砌,太密集了,太多了。博物馆里全是内容,几乎没有形式感。本来那些宝物每一个都价值连城,单独放在任何地方都会光芒万丈,但在大英博物馆里,它们却像商店里的商品一样彼此拥挤在一起,反而显不出光彩了。据说由于收藏品太多,展馆根本放不下,展览品也总在不停地更换。参观者、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偶尔一去的参观者,能够看到的也不过是一部分,更何况我们在里面只能呆上个把小时,我们能看到的又是这部分展品的一部分。
这个豪华至极的聚宝盆现在对全世界的参观者开放着,而且都是免费的。在这个博物馆里你能穿行于几千年前的雕塑和各种文物中间。它们大多没有防护,和参观者之间也完全没有距离,站在一个躺着的法老面前,你可以俯视他脸上亘古不变的表情,在他似乎还蠕动的唇边聆听无声的教诲。在这里我们超越了时空,走近了世界,走近了历史,也走近了人类的文明和智慧。
参观了大英博物馆,看到这个博物馆将全世界的瑰宝完好保存、奉为神圣,并庄严地再次展示给全世界的时候,心里又会觉得庆幸,英国当时的掠夺行为到现在产生了另一个客观结果,那就是保护了这么多的历史见证、文明见证,可以说就是汇聚和还原了世界文明史。而且现在还很好地利用着,使后人得以目睹这些瑰宝,包括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后裔。这又不能不说是对全人类的一种贡献。
很多事情随着历史的变迁也在发生着变化,因为全世界时刻都在变化着。当年被国人骂做“文化窃贼”的一批外国探险家,现在也已被重新评价。这的确是个悖论,让人尴尬。但屈辱是一个事实,意义又是另一个事实,两事实间还有着深刻的联系。世界人民该怎么面对呢?
希腊政府在上个世纪的很多年当中都在为英国运走巴特农神庙的雕塑向英国政府交涉,甚至提出用其他的文物进行交换的建议,但都没有成果。他们2005年已开始兴建巴特农神庙博物馆,这个向英国索回文物的决心还将坚持下去。
世界上的四大博物馆我已经看过三个了,都是走马看花,也都没有看完。收藏品种的丰富和数量的巨大是它们共同的特点,要想真的一一欣赏,得在你的一生中专门为它安排出时间。
看过这些博物馆之后,我才对世界级博物馆有个实在的概念了:所谓的“博”,不仅指时间上的悠久,而且指空间上的辽阔,上下几千年,纵横五大洲。中国自古以来安分守己,从不曾向谁出击过、进犯过,自家有的也有很多没有保住,更不会藏着别人家的宝贝。故宫历史博物院共有文物150万件,大多是中国清代皇室藏品,数量、质量都很可观,但也没有可能跻身这四大家族的行列了。
游览这几个博物馆我还得到一些特殊的印象:
巴黎的卢浮宫是最舒展的,它讲究形式感,艺术品的摆放都充分突出了它们杰出的品质,所以它的展品最具有打动人的魅力。从另一方面讲,它也是最考虑参观者感受的,给了你充分领略的空间。我觉得这符合了一个艺术博物馆的最好初衷。舞蹈家邓肯在自传《我的一生》里曾写道:“我们日复一日地去卢浮宫,直到关门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去。我们在巴黎没有钱,没有朋友,可我们什么都不缺,卢浮宫是我们的天堂。”
俄罗斯的冬宫博物馆是最具有文物保护意识的,里面有很多工作人员是中老年妇女。她们时刻睁圆了明察秋毫的锐目,凭着自己经验丰富的洞察力,在你还没有掀起镜头盖的一刹那,她就已经制止你了。不仅如此,当你在纸上记下一个作品的标题的时候,她也会充满怀疑地询问你,好像这样一个举动就能把那宝贝的魂魄摄走了似的,结果参观变成一种被跟踪的过程。当然,她们的行为是出于对国宝的责任和爱护,都是大家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只是感到有些分散观赏的注意力。
在大英博物馆里参观则是最自由的。很多文物毫无防护,去不去触摸,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因为周围常常一个工作人员也没有。所有的展品都可以自由地拍照,尽情地闪光,只要你有时间和耐心。这倒让人怀疑起来:抢来的东西就不珍惜了?
在伦敦阿尔伯特艺术博物馆参观的那次,突然有个很年长的工作人员大声跟我讲话,我吃了一惊,以为自己违反了什么规定。但看他的模样非常热情,笑容可掬,不像在责备我。原来他是请我坐一把椅子,一把有浮雕的银光闪闪的金属长椅。这又把我吓了一跳,我以为那是一件展品,可他不断地说“坐下、坐下”,并极力用表情告诉我,绝对可以坐在上面休息。看来他是位对女士很有爱心的老绅士。为了不拂他的盛意,我小心翼翼地坐了一下,马上又站起来了。
英国的博物馆是慷慨、热情和有礼的,可我们怎么去遗忘曾经有过的那些屈辱历史,怎么让自己带着毫无保留的尊敬像去接受一个老绅士的热情那样去接受这个国家所表现出的好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