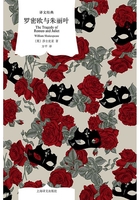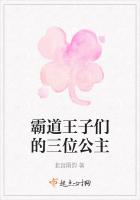M:你好!
前一段时间我到武汉出差去了,回来以后才看到你关于稿子的询问。谢谢你的意见,很有建设性。但今天我不想说稿子,只想说说此次出行的感受,正好借机以告诉你的这种方式,让我把旅途的见闻记录下来,一举两得。
不过从武汉刚回来的这两天我不太舒服,最显著的感觉是,在每分每秒里感到自己被空气榨干,好像有只无形的手在贪婪地汲取和挤压,任何有潮气的地方都是它的源泉。皮肤打皱了,变硬了,头发每一根都想独立地飞起来,鼻腔里微微干疼。我心里有点吃惊,莫非我才离开了几天,就变成南方人了?
武汉的梅雨季节,淫雨霏霏,潮气袭人,我觉得我的膝盖以下都是微湿的,关节吱吱呀呀的。房间里陈旧的地毯散发着经年的腐败味道。我住在三楼,但房间也没有因此显得干爽一些。在这样的气候里变化最奇妙的是我的头发。本来那是一丛很蓬勃的庄稼,这时好像突然都失去了筋骨,坍塌下来,软绵绵地贴在头皮上,如婴儿的胎毛,把我变得毫无神采。在武汉的雨季,我的头发太软了,就像风里的植物挪到了水里。瞧,我还是地道的北方人么。
在武汉的时候我曾为了一部稿子,到过它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叫随州。
关于这部稿子的工作有些枯燥,于是我对邀请我们来的朋友詹先生说:“这是你的地方,我们不能来过还像没来过一样,你带我们出去玩儿吧!”
其实我并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好玩的,只是想弄点变化出来,削弱些枯燥的感觉。
就这样偶然地,我参观了位于随州城西擂鼓墩的曾侯乙墓。
曾侯乙墓,就是出土编钟的那个墓穴。编钟,我早就知道的,它被称作“古代世界的第八奇迹”;但我从来都不知道曾侯乙墓,更不知道随州。
曾侯乙是春秋战国时一个诸侯国的国君。从他的墓葬看,他生前真是势力庞大,生活奢华。曾侯乙本人酷爱音乐,很有艺术修养,是个极尽享乐的人。他死后还在这些方面表现出很多难以舍弃的愿望和要求。
曾侯乙墓一共出土了14500多件文物,包括青铜、铅、锡、金、玉、石、骨、角、漆木、竹、丝、麻、陶等,涉及音乐、手工艺、雕塑、绘画、书法、冶金铸造、天文学、车马兵器、琉璃提炼等等。我不想把资料都抄给你,只想对你说说参观后在我心里久久萦绕的、无法忘记的感受。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曾侯乙墓里的那些乐器,共出土125件,包括编钟、编磬、各种鼓、琴、瑟、笙、箫和一些已经绝世的战国乐器。那架举世闻名的青铜编钟由65个大小不一的钟组成,每个钟都能发出两个乐音。它的钟架自重1850多公斤,其上还要负载2560多公斤的钟体,一共重达4410公斤。编磬由32块石料片构成,石料是石灰岩和大理石成分,古代叫做“磬石”或“鸣石”。我不知道现在最大的乐器钢琴有多重,但人们搬家的时候都是可以整体搬走的。所以钢琴根本无法和这些古代乐器的庞大规模相比。想象一下,古人们摆开阵势,用这样的巨型乐器演奏的时候,那该是多么隆重和壮观的场面。
曾侯乙墓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乐器博物馆,它被今人称作是“地下音乐宝库”。在这个了不得的墓穴中,关于音乐还不止这些,那位曾侯乙先生还企图让他在另一个世界的“家”充满生前的生机和美感:有21个女人为他做陪葬(还有一只爱犬),她们的年龄从13岁到26岁不等,每个人都有单独的、制作讲究的棺木,这其中除了爱妃、宠妾和侍女,其余的是专事演奏和歌舞的低龄女孩。
毫无疑问,曾侯乙生前十分地喜爱音乐和女人,将两者视为珠联璧合,甚至视为生命结束后死亡黑暗中的一线希望,视为同生同死的伴侣和搭档。他很多情,又很残忍,他不得不死,又非常留恋。由于他的艺术家气质,也由于他的君王权势,我们这些今人才得以目睹他那个时代的音乐世界,以及2400年前的各种生活场景。我觉得他还是挺伟大的。
不瞒你说,我当时对曾侯乙墓一无所知,去的时候就像去任何一个平常的地方,对于如此远古的奇迹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在这次不经意的参观之后,我心里的震惊很久都不能平复。我很奇怪,为什么那个朋友竟没有主动对我们提起这样一个世界级的景点,那应该是当地人莫大的骄傲呀。但我还是感谢他,如果没有他的那部书稿,我永远也不会有机会来到随州这个小地方。
关于那21个陪葬的女人是以什么方式毫发无损地安卧在自己的棺木里的呢?这一直是大家猜测的一个谜。你认为呢?
说到曾侯乙墓历几千年而不朽的保存方法也是让人惊奇和开眼的,谁也想不到它是从古到今地泡在水里。
这座墓的底部低于地下水位,当封墓后,水渐渐渗入墓中,把一切淹没。水除了对尸体、丝织物等有腐蚀作用外,对竹木质、铜、玉、石还能起到养护作用,对盗墓者来说也是天然屏障。虽然曾侯乙墓也曾被盗者凿洞,但却未遭劫掠。所以这座墓的珍贵和完好据专家说属国内罕见。
当时发掘墓穴时人们最初看到的是一池清水,15000多件文物都是在毫无预知的情况下从深水里打捞出来的。有一幅图片叫“编钟出水”,而不是出土。发掘者在发掘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惊喜:随着水位逐渐降低,每个层次都有意想不到的宝物露头。打捞到巨大的青铜编钟时人们已是大喜过望,但下面又出现了编磬!想象一下,考古学家的发掘过程真是大喜过望、惊心动魄的过程,怪不得那么多人乐在其中。
我们在随州博物馆里看到的棺木和漆器的原物,居然花纹依旧,色泽如新,有些出土漆器现在依然泡在水瓶里。湖北人都说木头最好的保藏方法是用水泡着,叫“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看来这个方法是有千年铁证的。
还忘了说青铜器呢。曾侯乙墓里出土的青铜器登峰造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世界罕见,湖北省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几乎就是它的专门展馆,那制作工艺和铸造技术放在当今也是不可思议。
有一对美观巨大的“青铜鉴缶”,上面铸着巧夺天工的浮雕,我并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但非常喜欢它的壮观。后一打听,它居然是战国年代的冰箱,制成双层,中间可以放冰块儿降温。其中的一只现在已搬到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我后来在那里参观时又与它不期而遇,不禁喜出望外。它那么美丽,又那么先进,谁能不喜欢呢?
关于曾侯乙墓墓葬的内容实在太多了,仅就那座设计独特的、带有“灵魂出入通道”的墓室就有专著问世。这座墓的意义之于音乐、古文字、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建筑、冶炼等都有着非凡的意义。我说不全,你亲自去看吧。我的参观是偶然撞上的,但你可以怀着期望去,多大的期望都不过分。
参观完了曾侯乙墓,再看随州,我知道我来到了一个看似很小却极不寻常的地方。瞧,那个走路很带劲的德国老头,胸前插着一支看得见袅袅香气的栀子花,表情沉醉得很,他一定游历过世界上很多著名的地方,幸亏他没有漏掉随州。
M,你说怪不怪,因为对曾侯乙墓的惊叹,我对随州这个原本陌生的地方也开始刮目相看了,总觉得它既然有着那么不同寻常的祖先,总得有些与众不同之处。
随州位于湖北和河南的交界处,是我们平时耳闻的神农故里——始祖炎帝的诞生地。炎帝曾在这里“创耕耘,植五谷,尝百草”。除了有着丰富的古代文明,随州还山清水秀,天高云淡。但当地人的口音是我所听到的方言中最难模仿的一种,夹有不标准的湖北话和同样不标准的河南话,刚听时,会误以为是说话人在学说方言时走调了。莫非当年的曾侯乙先生也是这种口音?真不知道它该归入哪种方言。
随州市有一条穿城而过的大河,叫涢(音:Yún)水。河面很宽阔,像沙滩一样平坦,河岸两边有垂柳摇荡。据说枯水期到来的时候,河床干涸,青草萌生,人们在河道里放牧牛羊,像古人一样逡巡奔跑,一派天然田园景象。过了枯水期,涢河又重新诞生,到了梅雨季节,水位达到最高,河水异常宽阔,泻水闸要全部打开。
有一天我坐车从桥上经过,看到有成群的人站在桥边的河岸上专注地观望河心,好像发生了沉船或溺水的事件。我忙问当地人那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回答说:“没出什么事。”我很奇怪:“那他们在看什么?”那人温温吞吞地说:“看水。”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看水?水不是天天都有吗?”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随州人的一种爱好,一种仪式,一种生活,他们喜欢看梅雨季节水位最高的那一次河水,俗话叫“看大水”。这一次正巧被我赶上了。
我也下了车跟着众人看大水。那河水果然浩浩荡荡,汹涌澎湃,像个壮观的活力无限的生命。人们携着老人,抱着孩子,成群结队地来到涢水岸边看大水。他们脸上的表情像去看一场演出,又像去赶一个集会,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朝一个方向聚集着。有时还会看到几个人突然奔跑起来,追逐着某个浪头和水花,想要赶到它们前面去。
难道这一片水和那一片水有什么不同吗?我看看水,里面并没有什么异常的东西;又看看他们的脸,还是一片专注。
他们到底在看什么呢?
也许是在观察我看不懂的鱼情?或是通过水预测来年的什么景象?也许在追赶某个已经故去的亲人的亡灵?或是在遵循古人的什么嘱托?抑或是体验那种逝者如斯的真实感,看无形的时间从脚下有形地流过?
不知道。
如果只是乏味地看看,怎么会有世世代代的人乐此不疲,怎么会有“看大水”这样的隆重遗俗呢?
我这个外来人不能懂得随州世居者的内心原动,但对“看大水”怀着莫名的兴趣和羡意,觉得这个传统和风俗里包含着难以言传的深意。况且那水真好看,像活泼泼的生命,跑得飞快,它要急急地奔到哪里去,奔去那里干什么,你一点也不知道,它留给你的全是悬疑。
M,这就是我急于想告诉你的旅途印象。不是每次出差都能这样怀着意外的高兴回来,到现在我心里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去呢。
别忘了我的提醒,你一定要找机会去随州,去看曾侯乙墓。没去过的人不懂得后悔,去过以后才会知道如果不去可真后悔。
关于稿子的事,我会专门跟你谈的,现在已经开始为插图忙活。
谢谢!再见吧。
武红
2002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