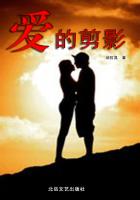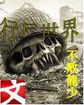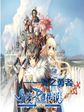抓饭铺
我们单位的斜对门、胜利二巷的中间有一个家庭抓饭馆,很小,面积只有10多平米。屋子很暗,也很简陋,支着三张覆盖着塑料桌布的台子。做抓饭的灶台支在屋外的棚下,为店面腾出一点地方。当那只大锅敞开的时候,热腾腾的一锅美丽景象就诱惑了过路的每一个人。
男主人叫阿不都热合满,女主人叫塔依曼,是一对40多岁的中年人。每次看到他们又忙碌又安静的样子,总让人想起“患难夫妻”这个词。去那里吃饭的次数多了,慢慢知道,他们都是不景气单位的内退、下岗职工,有两个孩子在上中学,还需要供养。这个店面每月要交纳房租费450元,但不知每天的抓饭可得多少利润。
阿不都家每天的生意就是一锅抓饭,外加一些烤肉串。据女主人说,这里地方偏,行人少,做多了没人吃,每天来的都是老顾客。凉菜和热红茶是奉送的。一大碗油亮亮的素抓饭2元钱,加肉的6元。很多人喜欢吃素抓饭,再外加几串烤羊肝,经济而美味。每次到抓饭铺吃饭都有温馨感,跟女主人聊聊天,把想吃的东西向她嘱咐一番。看他们两口子唇齿相依的和谐与默契,心里会很纯净。那种贫困中的吃苦和微笑是感染人的,总觉得有希望,充满了吉祥。他们静静地忙碌着,辛苦着,把所有的心血倾注在那一锅抓饭上。他们的抓饭做得的确好,肉嫩、饭香、色泽鲜亮,碎玉般的饭粒和橘红、金黄两种胡萝卜的调和,呈现着最柔和、温暖的感觉,家的感觉。
每次有朋友来,去的最多的就是阿不都抓饭馆,既省钱,又讨好。他们说,这是乌鲁木齐最好吃的抓饭,还拍了照,作为小吃的景点写进了导游书,希望阿不都家的抓饭也火一把。我很开心,他们真要发了,我也有一份功劳。
那天又和朋友去阿不都家。女主人塔依曼在穿肉串儿,她穿的肉串儿里除了平时的羊肉、羊肝、羊心、羊肠外,还多了一种不认识的东西:肠衣色,比较厚实,有些层次,一片片的。我问她:“这是什么东西?”塔依曼说:“羊的乳房。”“也能吃?”“好吃。平时我都拿不来,今天才拿来。”
我们吃了很多年烤肉了,还从未听说过烤羊乳房。朋友说,尝一尝吧。第一次吃这个不寻常的东西,心情也很不寻常,结果没感觉到是什么味道。塔依曼问我:“好吃吧?你每天都吃,****会长大的。”
说这话的塔依曼简直就是个穿平民装的女巫,手里没有魔棒,有羊乳房。
买西瓜
夏天的清晨有时会去早市。
早市上的蔬菜既丰富、又新鲜,还特别便宜。比如两个又黑又紫、泛着光亮的大圆茄子才卖一元钱,着实让我意外。可我身后的老太太还在嘟囔:“一元钱才两个茄子,价格还没下来!”这话让我又感意外,她们一定买过更便宜的。她们都是早市专家。
我最喜欢去西瓜市场。
清晨的瓜市排成一行,由墨绿和翠绿组成。各个品种的西瓜都会闪闪发亮地向你招徕,那种光泽就好像是它的笑容。
在这里,你可以免费饱餐一顿西瓜,有子的和无子的,像冰糖一样,又凉又甜。
无子西瓜长得溜圆,好像更甜些,但我总觉得那甜有点儿别扭,瓜本来应该是有子的,人把它弄到哪里去了?人加入了瓜的事情,我就不太信任。所以我买的十个西瓜里只有一个无子的。
我喜欢买西瓜。虽然吃不了太多,但想着它被切开的那美丽一瞬间,就觉得有一个好事在那里等着,欣喜得很。旺季的时候,瓜的价格特别便宜,每公斤才三四毛钱。花很少的钱就能得到那么多的喜悦,真是满足。
瓜农在做生意的时候情绪极好,不断地给你往袋子里装,要大给大,要小给小,就像一个特别慷慨的人。他们照例是会帮着你送回家的,但装的时候却不想着是自己要背的,我就说:“再装,你怎么背得动?”他说:“没关系!”用小车送到楼门口,他对我讲:“你得抱两个。”“这么大,我只抱得动一个,我还要给你开门呢。”他也没话说,居然也就把九个大西瓜背上来了。我说:“下次不会装这么多了吧?”他就笑了。我给他两元钱,他还说谢谢我。
西瓜一个个被我搬到储藏室里,它们绿得发黑,黑得发亮,益发显得硕大,我就欣赏一会儿。
买到一堆大西瓜的时候,总是比买到日本瓷器还要高兴。
可我的心里还是有遗憾:市场上还有那么多西瓜不能都属于我。
冬天
乌鲁木齐的冬天是北国的冬天,严寒笼罩,空气宁静。风环着城外的山丘像散兵游荡,却很难冲进城池。城里的空气如一潭死水,自己和自己撞击着、拥挤着,渐渐地浑浊起来,无孔不入地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冲刷得乌曲麻黑,连麻雀也不放过。无风的寒冷是温和的,它像漆黑中的亮眼睛给冬日的人们一些安慰和自由。
遇到拉雾天气,空气不再轻盈,很有浓度地荡漾着,沉重地垂落在人们潮湿的发际,密封住地上升起的每一丝气息,可以闻得到它包裹住的一切市井味道和湿漉漉的水气。每呼吸一下,仿佛吸进的不是虚空的气体,倒像是喝了口粥,稠糊糊的。空气真像一锅没有米粒的粥,令人饱胀。抬头可见深远处的湛蓝天空,它在我们头顶的高处明净开朗地凝视着,却不属于这个城市。这令人非常惆怅。
街上的每一寸土地都被鞋底踩脏,街上没有一双干净的鞋。
可在某一天早晨推开门你就会很惊讶:下雪了!
一个突然间改变颜色的世界显得比以前更大,一个倾泻着金银财宝的世界,比哪一天都富丽。这种突变完全是悄无声息的。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像下雪这样既声势浩大,又悄无声息。谦虚是什么?谦虚就是下雪。
雪像细密的丝线飞走着,把天和地连起,把今天和明天连起,把过去和未来连起。
雪很充沛、铺张,一点不糊弄。有时大如羽片、有时碎如齑粉,但都劈头盖脸,铺天盖地。它保持着自己远古的风范,没向这个时代学点弄虚作假的玩意儿,它说:什么叫与时俱进?我不懂,我只喜欢寒冷中的我自己!
冬天最喜欢的就是下雪,它像夜色一样掩藏污秽和凌乱,使一切变得宁静和美感,它就是洁白的夜色。
树的悖论
九月从广州回来后,温度低了二十多度,人们都穿着毛衣和厚外套。人在室外还能坚持穿两件衣服,但待在屋里身体就会渐渐地冷却下去,直至四肢冰凉。晚上要想为自己保暖,就得穿着棉袄、棉裤和羊毛袜子,否则钻进被窝睡觉的时候脚冷得像冰,很久无法入睡。乌鲁木齐每年的十月上旬和四月下旬是快供暖和刚停暖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挺难过的,室内只有十三四度,那是人们一年中在屋里衣服穿得最多的时候。
今年的温度是突降的,因了一场大雪。那一向喜人的雪因为不合时宜而变成了一场灾难。我从南方回来后,看到马路上的一些树像被雷劈了一样从中间分开,折断倒下——它们是被那场大雪生生压断的。而这样的断树那么多,有好些断在腰粗的树干处。马路上到处是树的残骸,尸横遍地。
人们也许会说,雪是轻盈的,怎么会压断坚实的树呢?
九月是夏天刚过的季节,树本身还枝叶茂密,每片叶子都饱满结实。叶子们傻乎乎地尽量兜满了一大坨儿雪,制作出一个个美丽的绿叶冰激凌。雪在叶子里没有很快地融化掉,每棵树上就结着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冰激凌。树身终于吃不消了,它无奈地倒下去了。
树夭折于自己供养的叶子,夭折于那些叶子的健康和热情。树愈是供养得好愈是被重压,愈是茂盛的树愈是被葬送。这简直就是一个悖论。
看到每一棵残树,你仿佛都能听到它支撑到最后的时刻所发出的那种死亡叹息,那是无奈的、断裂的、疼痛的声音。可据人们描述,那天的雪景可真是美得让人惊叹,乌鲁木齐处处繁花,“花重锦官城”。
看到园林处的车在街上为树收尸,已经是第二天了。
我问老公:“像这样的自然灾害,人们为什么不预防和抵抗呢?听了下大雪的天气预报,园林处就该出动去把树上的雪摇下来。”
老公说:“雪是半夜下的,那么多的树怎么摇?除非是发动市民。”
如果他们事先发动市民,一定会有很多志愿者参加的,我愿意去摇。乌鲁木齐本来树少,可当树变成尸体的时候就显得惊人的多。那些死去的大树是多少年才长成的呢!
雪灾发生在2003年9月27号。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很美,可岑参没写过雪后的断树和它们死去的声音。
城市风景
星期天我到街上去干洗衣服,回来经过乌鲁木齐著名的西大桥。
西大桥是城里最漂亮的街景,北望红山峭壁和古塔,东眺皑皑白雪的博格达峰,绿茸茸的青山苑小丘也迤逦在它西端的桥头。很多行人愿意停在这里照相。
西大桥是前几年新翻修的,栏杆全用不锈钢,有同色的浮雕。桥下是街边的草坪公园,人们在里面休憩和晒太阳。公园的边沿有一条流速很快的河。河虽湍急,但一看便知很浅,整个河床都是人工用水泥修筑的。河的一侧还有一条同样用水泥砌成的小支流,比人的身体略宽一些,它的源头挡着一块铁板,小渠里仍然注满了水,而且水深流缓。
当我从桥上经过的时候,看到桥下的草地上有五六个一丝不挂的赤身孩童,他们正一个接一个地在那条小支渠里漂流,身体和水平行,水面上露出圆圆的小屁股。漂到一定的地方就都爬上岸来回到原地重新开始。那天的天空浓云翻滚,时而露出太阳晴明灿烂,时而乌云压顶一片阴霾,风也吹得有力,气温只有摄氏20来度。赤身孩童们一离开水面就浑身瑟缩,抖个不停。
我仔细看去全是维吾尔孩子,都有十二三岁,其中唯一有个穿三角裤的孩子,那是个女孩。她的身体已经明显地发育,胸部的轮廓甚至超过她的身高和同龄人。她面向大街的时候用双手拢在胸前,朝向小伙伴时就袒露相向。
这一幕出现在闹市街头的奇异景象,好像突然把人们带到了某个乡村麦田的水洼旁,带回了曾经的一个纯真年代中,那感觉极其梦幻。
于是有了一些人傍着桥栏驻足观望。
桥下最小的看衣服的孩子见有很多人朝着那边看,以为在看自己。为了不辜负大家的注目,他觉得自己应该有所作为,于是就开始跳起了麦西来甫。他的脖子、胳膊、肩膀都开始抖动出一种节奏,整个身体就好像听到了鼓点,那姿态老到得让人发笑,他的脸上还挂着挑逗和俏皮。他只有六岁的样子。
公园的园林工突然来了,他呵斥那些游水的小人鱼,命令他们穿上衣服。
这时看衣服的小家伙停止了舞蹈,把笑脸换成怒容向着观望的人,他觉得人们不该再看下去了,因为他的哥们儿都光着屁股。情急之下,他捡起一块石头朝桥上投来,石头击中金属发出哐啷的脆响,惊吓了过路的人,他就笑得前仰后合,觉得自己对哥们儿很有用。
当孩子们穿上衣服之后,刚才的一群没长翅膀的天使突然就变成狄更斯《双城记》里的人物了,他们的衣服油污破旧,简直像电影中的道具。
我看到这个场景时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是那个女孩。起初,我觉得她真泼辣,有男孩子的勇气,不怕冷,而且内心原初单纯;后来,我又为她担心起来,觉得人们的目光都会伤害到她。我望着桥上那些引颈观望、兴致盎然的男人们,真想把他们的眼睛用乌云盖起来。
我觉得这繁华的俗世和杂乱的目光配不上这角落里美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