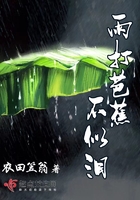喀纳斯最好看的是水。到过喀纳斯湖源头的人们都说,那里流出的不是水,简直是牛奶。这是由于上游冰川强烈融化带来大量乳白色的粉状冰渍物所致。它的湖水是一种掺了牛奶的绿色,绝不透明,像温软流动的琥珀。天光稍暗时,湖色更艳,湖水显得浓稠,凝固着一般;阴天时湖水变为灰绿色,晴天的早晨又呈蓝绿色。它的色彩可以随着春夏秋冬、阴晴晨昏而不断变幻,被誉为“天然景泰蓝”。
喀纳斯湖像尼斯湖那样有着引人入胜的湖怪传说,据说有个日本人独自游过湖后就发疯了,不知道现在好了没有。
而我到喀纳斯完全是为了来看那些六月里开得漫山遍野的芍药花儿,那些袅袅娜娜如站在山坡上招手的玫瑰色小女孩。都说看景不如听景,但唯独这一景超过了我的预料,还我一个由来已久的梦想。我希望的人间花园就该是这样的:杂草丛生,牵丝攀藤,有名的花和无名的花竞相开放,既平凡又亲切,既辽阔散漫又错落有致。风像它们的梳子轻轻梳理或野蛮操作,让她们向岩石和小蚂蚁鞠躬。我则置身其中,看每一朵花最单纯的表情,听她流淌着自己颜色的声音。
在喀纳斯还有另一种花儿——世居者蒙古族图瓦人的孩子们。
那天我们走到了阿勒泰最北边的一个村子——禾木村的小学校。这是一所同时教授蒙古语、哈萨克语和汉语的学校,它恐怕是全中国使用语种最多的学校。学生全是图瓦人的长着红脸蛋儿的孩子,真像花朵。
校园黑板上用汉语写着一句“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们稍一哼唱,大大小小的孩子就都跟着唱了起来,发音像汉族孩子一样准确,其实他们还没学会说汉语呢。
一行的同伴突然对我说:“你看,你做的红花台的小花怎么贴在那个小家伙的脑门上呢?”
我做编辑工作,“红花台”是我十年前出版的一种给小学各班级使用的评比台。
那时女儿的老师经常让她在一张全开纸上打格子,在格子里抄上全班同学的名字,然后给表现优秀的同学贴上红纸剪的小花,最后根据红花的多少进行评比。因为经常画很费事,我才想到了这个题目,觉得做出来所有的学校都能用。小红花是用不干胶做的,很方便,所以完全可以贴在脑门上,就像刚才的那个图瓦孩子。而同伴恰巧是红花台的美术设计。
可谁会相信十年后小红花还能开在中国西北角图瓦人的小学校里呢?不相信!
我们赶紧走进了他们的教室。孩子们也蜂拥而入。
红花台赫然贴在墙上。
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冲过去,真的在那张纸上找到了“责任编辑:武红美术设计:段离”的字样。我们就好像高考被录取了那样兴奋。
此时我们才知道,我们更喜欢在遥远的地方找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