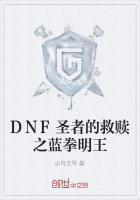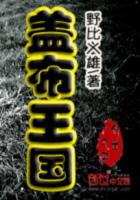这位是非的小妾暗中监视了她和长炳入夜同床的事, 而且把这件事告诉了于皓。于皓问女儿有没有这种事,她没有正面回答提问,显出很冷淡的态度,并趁机说那小妾搬弄是非。
她和长炳商量的结果,认为住在这里并不方便,那小妾看见过他们的事,必然还要闲扯是非,一旦被她父亲知道确有其事,不仅不答应说不定还会生气而病倒,所以,她为了避免让父亲生气,决定离开此地。
还有个原因是那四个卫兵老跟着长炳有碍他们的手脚和行动,想趁机打发他们回新疆,而她和长炳南下杭州,甩掉这四个盯梢的“尾巴”。
于彩琳给这四个“尾巴”买好了去新疆的车票,让他们先回去,她说她和长炳随后就回。那四个卫兵不敢违抗,请示长炳的意见,长炳当然同意他们先走。
这四个卫兵只好提前先走了。
过了两天,于彩琳和长炳拎箱挎包地走进火车站,准备乘南下的火车去杭州。
她的老父和父亲的小妾亲自到车站送他们。她的老父亲依依不舍地叮嘱她一路要小心, 特别嘱托长炳要好好保护他的女儿。
就在此时,突然传来了清脆的枪声,长炳应声倒地,挣扎了几下便一命归天了。火车站人来人往,非常混乱,听到枪响后人们更加惊慌失措,一时秩序大乱,那开枪的人早已趁人群慌乱之际逃得无影无踪。
于彩琳见长炳死在枪弹下,悲恸不已,伏在长柄的身上哭得死去活来。
于皓一见此情此状, 心中已明白了他的女儿和这个蒙古小子关系不正常,便立刻让司机去报警,而警察勘查了现场后,拍摄取证,便打发他们把死尸抬走,等候处理结果。
于皓在他女儿的要求下,用小汽车把长炳的尸体运回公馆。
等了两天,得到警察局的回答,说凶手不知去向,尸体可以先埋了。
于彩琳十分悲痛凄哀,她亲自为长炳设灵堂,以汉人的仪式举行了祭祀,然后将尸体装殓入棺,埋在京城最好的坟场中。
在举办长炳的丧事过程中,于皓本来很冷淡很不安,但拗不过于彩琳的一再哀求,只好出面主持这件事。
于彩琳俨然以妻子的身份为长炳举办了隆重的丧事, 引起人们的猜疑和议论,使于皓的处境很狼狈。
事后他追问女儿为何如此失态如此哀怜? 女儿流着眼泪讲述了与杨增新毫无感情的话, 细说了她备受冷落备受孤寂形同囚徒的凄哀生活。
她承认了与长炳的私情并打算与他远去杭州结为百年之好的计划,也说明了打发走那四个卫兵的目的。
于彩琳对她的父亲说她将向杨增新提出离婚, 然后去杭州陪伴自己的母亲。
于皓听完女儿的话, 心想都怪当初自己为了讨好袁世凯把心爱的女儿远嫁新疆,使爱女受了许多委屈。
他感到内疚而又悔恨,但又觉得女儿太任性,不考虑后果就跟一个蒙古男人私奔是有点太鲁莽了,结果让那小伙子丧了命。
他也感到事情很蹊跷,但又理不出杀人的头绪,无法证实究竟是不是杨增新暗中指使人干的。
但他的女儿说肯定跟杨增新有关系, 她说她很了解杨增新这个人的个性,他会暗中派人干出杀人的勾当。她想这肯定是那四个卫兵干的。她请求她的父亲能出面干预这件事,让警察局查出那四个卫兵的行踪。
她的父亲也同意女儿的看法, 认为这次谋杀事件与那四个卫兵有关系,只要能查出他们,就可以追出幕后的策划者。
于皓便向警察局提交了报告, 指出事件的性质并要求追查那四个卫兵。
他的要求被接受了,过了三天警察局长请他来办公室面谈,他依约而去,受到热情而友好的接待。
警察局长很客气地给他倒茶递烟,寒暄几句后,便从抽屉里取出一份调查报告给他看,他看过之后立即泄了气。
原来那是火车站出示的调查报告, 证明那四个卫兵的确在事件发生的前两天已经乘火车离开了北京。
警察局长又说为了慎重起见, 通知北京所有的警察去各个旅馆查找那四个卫兵,结果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警察局长说这件杀人案肯定不是那四个卫兵所干的。于皓听后也只好相信了这样的结论。他回家把情况告诉给女儿于彩琳,她苦无证据,只好忍痛等待警察局的破案结果。
长炳之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谁杀死了长炳呢?
于彩琳的怀疑是正确的, 她判定是杨增新派人所干的也是正确的,但她怀疑是那四个卫兵所干却是错误的。
那四个卫兵的确已经走了,他们确实没干这件事。那么究竟是谁干的呢?
是杨增新指使他的侄子杨应龙干的。杨应龙带领另外两个亲信化装后来到了北京。他们三人住在离于皓的公馆不太远的一家旅馆里。
他们跟那四个卫兵并没有接头。
他们怕被那四个卫兵牵扯出来。
杨应龙派两个亲信化装后在于公馆附近监视, 一旦发现长炳出来立即报告他。
这天,当长炳、于彩琳和于皓及其小妾一出公馆的大门,杨应龙的两个亲信立刻发现了, 一人追踪着, 另一人报告了杨应龙。
杨应龙从亲信的汇报中知道他们是去火车站, 便化装后去了那里,果然看见他的另一名亲信正守在火车站等他来。
杨应龙头戴礼帽,鼻翼上夹一副墨镜,穿一身黑色西装,外穿一件时髦的风衣,那样子很像一位经商的阔老板。
他的两名亲信也化装后在暗中保护着他,为他打掩护。
杨应龙的枪法很高明, 从他掏枪到开枪只在一眨眼间就可以杀死人。
这种高超的枪法是他从小练就的。在杨增新的枪手中他被大家称为神枪手。
如果他不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杨增新绝不会派他来北京当杀手。
当长炳和于皓说完话刚一转身时, 躲在一辆小车内的杨应龙立即伸出手只用手枪随意地那么一点, 长炳的太阳穴便被子弹洞穿了,他当即倒地身亡。
杨应龙立即让他的亲信开车逃出了火车站。在预定的地点,他们停车后溜走了。而在预定地点守候他们的另外一名杨应龙的亲信则继续把小车开到一个停车场,停下后溜走了。
那小车是他的一个亲信偷来的,按预定时间开到了火车站。
杨应龙的两个亲信不仅是高明的杀手, 而且也是开汽车的高手。
所以,他们配合得相当好,衔接得很准确,时间掌握得很及时,没有出现任何差错,顺利地完成了刺杀的任务。
刺杀后的第三天,他们坐上到天津的火车,下车后在天津玩了两天,便又转道绥远省归化城,沿着骆驼运输道折回新疆。
长炳本人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又是外地人,北京警察局以无法查清凶手为名搁置了此案。于皓也并不热衷于对此案的追究,认为追究得太厉害会使他女儿的名声更坏, 弄不好会惹恼了杨增新招致意想不到的灾祸,所以,他只好就此罢手,以此搪塞,堵住女儿的嘴,落个清静。
长炳被杀的命案也就不了了之。
于彩琳终于也就此罢手。
杨增新在暗中得意地笑着,心想:我不仅摘掉了绿帽子,而且还要了你长炳的命, 看谁敢再拈我的门前花, 再惹我的院中草?
长炳虽然死了,但于夫人的心还在长炳的身上。她在梦中与他幽会、戏笑,显得快乐无比。
然而一到白天,她却苦闷难耐,感到人世的残酷与命运的不幸,凄恻地流出热泪来。
她不愿意生活在白天,而愿意生活在黑夜,她特别喜欢夜里做梦, 惟有在梦中她才可以和长炳见面而沉浸在情意缠绵的云雨之中共享愉悦。
她讨厌杀死长炳的北京城, 更讨厌那多嘴多舌的她父亲的小妾,她决意到杭州去见她的母亲,诉说心中的不平与烦恼。
在离开北京之前, 她瞒着老父亲乘坐轿车到长炳的坟上祭奠了一番,哭诉了心中久憋的闷气,向死去的情人依依告别。
她在父亲的佣人的护送下,乘上南下的火车到了杭州,与她母亲团聚了。
她向母亲无遮无掩地哭诉了所发生的一切不幸的事情,得到母亲的同情和怜悯、宽容和爱抚。
自此她和母亲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起, 她感到了母爱的伟大与永恒,她以一颗执著的坦诚的心侍奉她的老母亲,她决心永远不离开她的慈爱的母亲了。
她通过她的老父亲电告杨增新,提出与他离婚,表示永远不再见他的面,永远再不去新疆。
杨增新表示了默认,他再没有和于彩琳联系,也不再过问她的任何事。
于彩琳至死也没有再来新疆,更没有提起过杨增新。
看来他们压根就不应该结为鸾俦。
他们的分手早在意料之中。
人的婚恋往往难以捉摸。
杨增新在政坛上独霸一省,可谓呼风唤雨的枭雄,按理说于彩琳应该以有他为荣为贵了,然而事与愿违,于彩琳不仅不以他权大势重而自豪,反而感到受了莫大的屈辱,对他产生出极大的反感与蔑视,表现出极大的反抗与背叛。这说明爱情的真谛在于异性之间的情之共鸣、心之同一、爱之真切,而不在于官高权重。
凡是倾倒在高官门下的女人没有几个是真心爱其权贵的,从古至今,屈指算来为数不少,但都不是情之所至,而是另有所图的。
于彩琳的母亲不幸逝世后,留下了孤苦伶仃的于彩琳,她父亲特意派人来接她去北京,但她执意不肯去。后来她父亲又亲自来接她,但她已皈依佛门,在杭州风景秀丽的玉泉寺当了尼姑。
于皓赶到寺院里看到已经削发为尼的美丽的女儿正在敲打木鱼,不由老泪纵横,涕泗滂沱了。
他不由悔恨自己的缺乏理智的过去。
他不由为自己家门的悲剧而感到揪心的痛苦。
然而世事多变,沧海桑田,风雨难料。他也无奈,只好怅然而归,将满腹的辛酸深深地埋在心底。
杨应龙等人返回迪化向杨增新报告了长炳被杀死的消息,他闻讯十分满意,嘉奖了杨应龙等人。
杨增新派人打扫于夫人住过的房间, 将所有她用过的床单和被褥以及茶具等物全都烧毁,连她的床也付之一炬,并将房间重新粉刷一新,表示扫除所有的晦气。
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粉刷得白白亮亮,杨增新正为自己从晦气的噩梦中醒来而欣慰时,他的机要秘书忽然闯进房间,把一封密电递给他,他拆开一看,不由脸色陡变——
原来是他的密探从喀什发来的急电。
电文说喀什王要在南疆宣布独立。
杨增新一瞬间脸色大变,慢慢地沉下脸又陷入沉思:该如何对付这个野心勃勃的喀什王? 该如何设法处决这个心腹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