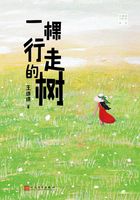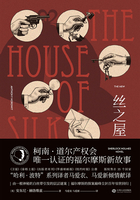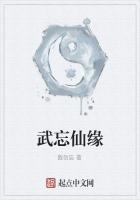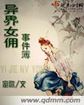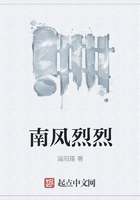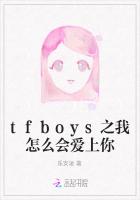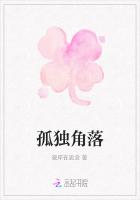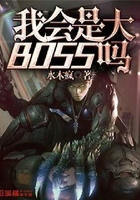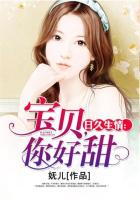清晨,李维丹的屋外嘈杂地响起了一片人声。有人敲着窗子,接着便纷乱地叫喊起来:“李大姐,快开门。”
“李大姐,海英丢失了……”
“海英失踪了。”李维丹急忙打开门,叶华、林班长,还有很多青年人蜂拥而进。周玉珍也在人群里,她是被叶华揪着衣领来的。
“放开手……你,哼!见场长,我都不怕!”周玉珍激怒地推开叶华,气咻咻地冲着李维丹说:“看看你们的团员!……团支部书记,你评评理看……”
“同志们……别嚷,叶华,你快放开手!同志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周玉珍欺侮小海英……”“周玉珍把小海英气跑了……”“林班长,你说吧。”因为找不着小海英,林班长也弄得惶恐起来。他十分懊悔为什么昨天晚上不将她送回场部,但他不认为这是失踪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周玉珍惹起的,海英昨天把事情都告诉他了。他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叶华圆瞪着眼,大声责问:“周玉珍,你干吗要她填那张表?”周玉珍倒是振振有词地反问:“你是她什么人?”
“你管不着!”
“一定得问清楚,否则问题解决不了。”
“同学、同志,怎么样!”
“你能负起她的全部生活费用吗,你能把她养活吗?”
“为什么……”
周玉珍进攻了:“我问你,把她列入供养人员,是我错了吗?让她填张表,不应该吗?”叶华认为问题就在这里,她强硬地质问着:“为什么列入供养人员,为什么!……”
周玉珍早就作好回答这种质问的准备了。她将一本《劳保福利条例》“啪”地往桌子上一放,挑衅地向着所有的人扫视着,气势汹汹地问:
“你们看过劳保福利条例没有?……啊,都没有!……”
“这干劳保福利条例什么事!”
“哼!叶华,我不怕得罪你,你真是不学无术!”
周玉珍翻开这本书的一页,大声地朗读起来:“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病假六个月以上的职工,停发工资,其生活费按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五款补助之……”她把书一合盛气凌人地逼近叶华:“我错了吗?”
叶华理屈了:“那么……”
“那么,既然应该列入供养人员,为什么不应该填表?”
周玉珍的话,使林班长实在听得不耐烦了,他气愤地制止这种毫无意义的争执:“你们吵个屁,搬条例有什么用,现在是人不见啦,得赶快去找。”
周玉珍仍有余怒:“都说我错、我错,什么事情都朝我头上堆……现在,你们该明白了吧!”她悻然地走了。
李维丹朝着周玉珍的身影叹了口气,回头对林班长说:“小林,你忙了一夜,快睡觉去吧。”
“还睡觉,睡得着吗!”
“那么,也好,咱们来研究研究,到什么地方找她呢?”
农场的场部是梧桐窝大草原的中心点,一条中心公路直穿草原南北。沿这条中心公路往南走两公里是拖拉机队,如果她是回场部,那早该回来了;沿中心公路往北走十公里是骑兵连,再走五公里是“八一棉”田,已经给那里打过电话,没有人看见小海英;再从骑兵连往北走,中心公路分开很多支线,通向一系列耕作区和生产连队,一直要走四十公里才到尽头。可是那些地方小海英从来没有去过,她也不可能跑那么远。
应该到哪里找她呢?人们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有些人主张往东找,有些人主张往西找,也有人主张分头到各处找。可是梧桐窝的东南西北是如此辽阔,这样谁都没有把握找到。李维丹的头脑保持着清醒,经过防霜之夜和叶华谈话,她对海英的了解又深一步了。她认为,可以根据海英的思想线索去捉摸一条找寻她的线索:“林班长,一个有悲观情绪的人,多半会朝什么地方走呢?”
这句话,像一盆使人清醒的冷水,使得被大清早发生的事情弄得头脑有点发懵的林班长,一下便明白了说话的意思。他思考了一会儿,说:“李大姐,你这样看还不大全面。”
“那你的意思呢?”
“我认为,海英有悲观情绪,也有……”他想不出恰当的话,只好说:“她还想活得更有意思哪,好像这还是主要的。”
李维丹很同意林班长的说法。“对,对,你说对了。那么,她会朝什么地方走呢?”
“朝有拖拉机的方向走。”有人说。
“不对,会朝医院走。”叶华说。
“也许还会绕到骑兵连。”也有人这样说。
李维丹和林班长都默不作声。瞎估冒猜是没有什么结果的,现在需要动脑子。
又过了一会,李维丹不敢十分肯定地说:“她离开了拖拉机队之后,也许会沿中心公路往南走。”往南再走三公里,就是水库。“她很可能跑到水库了。”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的思想矛盾得很厉害的时候,会不知不觉朝着印象最深刻的地方走的。”
林班长拍着腿,兴奋地说:“我也这么想。还有些补充理由:小海英去年在农场光在水库附近工作,别的地方她很少去过,她不会跑到其他地方的。”
可是有人反驳说:“如果她悲观失望,一时想不开……”
李维丹微笑着说:“放心吧,林班长的话是对的,她想活得更有意义,这是主要的。同志们,我们到水库那边吧。”
叶华忽然脸色煞白了。她恐怖地惊叫起来:“她可千万别跑到水库,那边有狼!”
叶华的话,使人们高兴了一阵的心情猛然灰暗了。昨夜水库那边的狼嗥叫得特别厉害,万一她真的跑到水库,可就糟啦。年轻人一边朝水库的方向走,一边希望别在这个地方发现她的踪迹。
可是,用不了很久就真的在水库附近找到海英的踪迹了。林班长在从前宣传组的废地窝子旁边,拾到了一枝折断了的刻蜡纸的铁笔,他一下就认出这是他昨天晚上给海英的。叶华也在白杨林带里拾到了一张小纸片。哎呀!这不就是周玉珍写的那张“光拿钱不干活”的纸片吗,海英一定来了。
他们找呀、找呀,连嗓子都喊破啦,也没有发现那个一定是在悲伤地踽踽独行的小海英。到了中午,所有地方都跑遍了,就差东边那片大苇湖还没有去。可是除了狼爱钻苇湖以外,就只有猎人有时会到那里,小海英跑去干什么?
苇湖里传来几声枪响,成群野鸭子惊惶地飞起来,满天乱闯;白色的鹭鸶和花斑斑的野雁,咕咕咯咯地在空中鸣叫。但是它们都不肯飞远,因为母禽在苇湖里下了蛋,有些幼雏已经孵化出来了。
叶华伤愁地望着浩浩荡荡的苇湖说:“我们去吗?”去,又该从哪个方向钻进去呢?老场长说过,这片芦苇荡是打游击的好地方,人钻进去便无影无踪了。既然一支游击队都无影无踪,一个人就更不好找啦。
李维丹抱着一线希望地鼓励叶华:“去吧,那里有人打猎,可以问问看见小海英没有。”
苇湖里,芦苇长得两人多高,密密丛丛地挤得连中午的太阳也照不进来。到处散布着鸟粪,白色的、灰色的、黄色的或者是斑斑点点的羽毛;鸟粪像戈壁上的砂砾,铺了很厚很厚的一层;在沼泽边缘的湿土上,印着很多非常大的鸭掌似的水鸟脚印;在狼藉着狐狸足迹的地方,有一团带血的羽毛在发出黯淡的红色……
芦苇荡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阴森森的世界,难怪狼才这样喜欢钻进密密丛丛的苇林里搭窝。只有在那些不知道哪年枯萎了的、杂乱地倒了一大片的干苇丛上,才露出令人欢慰的蓝色的天空。走在这些干枯的苇秆上,就像踩在打麦场的草垛上,响起了一片香甜的窸窣声。那些没有被枪声吓跑的野鸭子,听见这声响都在附近惊惶地飞起来了。不知什么地方响起了小鸭子吱咕吱咕的叫声,李维丹和叶华停步静听,小鸭子又不叫了。这当儿,苇湖是静穆的,连风儿摩擦着芦苇叶锯齿的咝咝声都可以听得见。
突然,叶华惊慌地低声说:“李大姐,你听……”
在苇林深处,响起了芦苇被撞击的啪啪声、急乱的脚步声,还有一只小动物被追赶而慌乱奔走的嚓嚓声,声音越来越近。
“狼……”
“别害怕,叶华,狼只有被打急了才咬人的。”
声音朝她们的方向来了。叶华屏息着呼吸,和李维丹静静地蹲在一堆倒下的芦苇旁边,监视着传来声音的方向。不久,就看见一只还不会飞的、白色的鹭鸶幼雏,从苇丛里钻出来;紧接着——不是狼,是一个人追了上去,往前一扑,扑了个空,小鹭鸶又钻进芦苇丛了……
叶华失声大叫起来:“海英——海英——”
这的确是小海英。她没有听见叶华的叫喊,仍然非常热心地捉小鹭鸶,直到叶华从后面一把抱着她,她才快乐地大叫起来:“哎呀,叶华,快帮我捉……”
我的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找了半天,原来她独个儿跑进阴森森的大苇湖捉长脖子鸟啊!这样奇怪的行动,简直把人弄糊涂了。李维丹经过一阵惊愕,又好气、又好笑,谁说她有什么悲观情绪的?她为那只不会飞的鸟把一切都忘光啦。
海英急忙拽着叶华的手,硬要叶华帮她捉住那只调皮的小鹭鸶。小鹭鸶被追得走投无路,便奋起自卫,用黄色的长嘴朝着海英的眼睛啄去。咦呀!胆大的叶华都吓了一跳,可她张开两臂一下子就把小鹭鸶抱进怀里,哈嘿哈嘿地欢笑着。你瞧她,玩得就这样高兴,连苍白的脸上都闪出绯红的光彩;两条瘦腿不知怎么的变得这样灵活……整个人都变啦,一点都不像那个被病魔折磨得很容易流泪的小海英啦。只有一点没有变,就是她仍然听不见别人说话,所以无论李维丹和叶华怎样问她,她总是催着她们赶快找野鸭窝、拾野鸭蛋、捉小鸭子……
“嗳呀,李大姐、叶华,快来呀!”
她把李维丹拉到一堆倒下的苇丛里,稍微找了一下就找到了一个野鸭子搭的窝,里面有五枚野鸭蛋白灿灿地闪光。“嗳呀,多好……嗳呀,把衣服脱掉,包着……嗳呀,没有绳子,解鞋带吧……”
她满以为用鞋带把小鹭鸶的脖子拴起来,就可以像牵头小羊那样牵着它走哩。想不到小鹭鸶一挣扎,连鞋带也带跑了,一钻进芦苇便再也找不到了。她无限惋惜地叹着气,用衣兜包起野鸭蛋,最后才说出李维丹和叶华急着要知道的事情:
“走吧,老场长在那边捉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