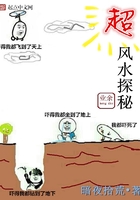鸿城果如村中的孙郎中说过那样繁华非常,宁休骑在白马上,望着四周的景象,这般想着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白马行得极稳,纵使这是宁休第一次乘马也不觉得有过多的颠簸之感。
替宁休牵马的男人便是安远,是那个名震天下的安远,可惜宁休确实不识得他,何谈这几年他轰动人魔两族的赫赫战功。
入城门后,两人一马穿过一片繁华的闹市进而转上一条很是平坦的大道,道上少有行人,宁休从未见过如这般平坦的路,便是连一株杂草都无从在这条道上寻找。
那个男人走在白马前不说半个字,宁休忐忑不安,倒是不知那人也同样是心乱如麻。
城门处的军卫拦下宁休,与他素未蒙面的安远当然没有理由救他,但事实却是如今宁休正乘在那匹与安远一样名震天下的战马之上。
安远识得宁休自怀中掏出的玉佩,心惊之余万不敢让那些军卫伤了他分毫。
“把他交给我处理。”
旌旗立于道旁翻飞,阵阵秋风迎面而过,宁休本就苍白的脸色更是难看,他不止一次回想安远对军官说的这句话,反复再三也不明白此时他的境况。
不过宁休至少认为安远是个好人,仅仅凭他魁梧的背影,以及一步一稳的行姿。
“安将军!”
宁休胡乱地想了好多事,双手倒是一直举在胸前僵硬地握着马缰,再次听到前方有人朝着男人打招呼,才堪堪回过神来。
一路行来不知有多少人向安远抱拳行礼,只是安远从未答话,甚至宁休只见他曾微微地点过几次头,至于其神情如何,宁休坐于马上自然无从得知。
安远朝着前方那个体态有几分臃肿的中年男子点了点头之后,继续前行。
宁休习惯挺直背部,竟是乘马之时他也是这般,好在白马四蹄稳健,极少出现起伏的境况,否则倒是有些苦头让宁休吃去。
每个与安远抱拳行礼之人皆是站于原地,似乎尽是待安远离去后才肯继续前行,刚才那个中年男子也不例外,此刻他正打量着白马上的宁休,虽只有半息的时间却也让得这个少年好不自在。
“你病得很重?”
一道浑厚的声音自前方传来,宁休怔了怔才猜到应该是安远说了话。
“是。”
“气息紊乱,长短不一,是久病缠身?”
“是。”
“你可知道你要寻的是何人?”安远忽然停了下来,而白马竟像是与安远同手同脚般骤然四蹄驻足。
“不知。”
安远忽而觉得身后那个少年有些好笑,连寻的是何人都不知晓,还口口声声称自己前来寻人。
“你可知道那枚玉佩是何来头?”安远转过身,一道犀利的目光随即而来,宁休抬头挺直了背,顺着安远的目光看了回去,并不畏惧。
“不知。”
“玉佩你是从何处得来?”
“咳,咳咳。”
咳过之后,宁休深吸了口气,以求好回答安远的问题:“自幼一直佩戴。”
安远如何问,宁休便如何答,且都是一五一十地答,从未参过半点虚假。
“你父母何在?”
“不知。”
直到白马再次前行起来,安远则又一次陷入了沉寂。
宁休骑在马上,不清楚安远问的问题有何意图,他想起了从未谋面的父母,不禁有些呆滞,自打他记事起一直是独身一人,这些年若不是村中几个老人照顾,他或是早就死了。
“咳咳,咳咳。”
陡然响起的咳嗽声打破了风声与马蹄声难得的平衡,宁休摸着怀中的那枚玉佩,眼眸之中已是恢复了清明。那玉佩入手温润,宁休只觉此刻全身都舒畅了不少,一时忍不住便顺手将其摸了出来。
玉佩于日光的照射下呈明黄色,大致与宁休手掌大小相仿,整体是个龙形的模样,玉龙神情很是威严,双眼极为有神,其上鳞片爪子雕镂得清晰无比,只是整个玉佩的左边显得极为平整,好似用利剑斩断过一般。
安远识得这枚玉佩,并不代表他人也识得这枚玉佩。
如以往一般,宁休此番又拿着玉佩左右看了许久,依然如往年一样毫无收获。
“你带了婚书?”
宁休骑在白马上,握着那块玉佩,想了不止五遍听入耳里的问句,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起初宁休并不认为那封婚书与这玉佩有何联系,甚至于十多日前他才知道有一封婚书的存在。
十二年来宁休因患怪病饱受折磨,这是实情。前些日,村里见多识广的孙郎中建议宁休拿着玉佩来寻人,孙郎中说能赠这枚玉佩之人定有方法治好宁休的恶疾,他离开那个村庄正是为了寻人治病,不料当其离开村庄收拾行装之时竟发现了一封婚书。
婚书是属于宁休的,上面除了有宁休的名字以及他的生辰八字外,还多写了一个女孩的名字:玄漾。
安远知晓婚书的存在着实让宁休吃惊,他不解为何安远只知玉佩竟能说出婚书之事,细想之后到此时他才明悟这玉佩与婚书本就存在必然的联系。
不过宁休只想治病,至于这封婚书,他本就没当过真,而且他甚至不知道成婚意味着什么。
“带了,但……”宁休又想了许久决定实话实说,只是其话只说出一半便被安远打断。
“好,好。”
安远一向浑厚的声音似乎有几分的激动,宁休虽是注意到了安远稍稍停驻的背影,他猜不到安远的心思。
安远动了,白马自然也动了,便在此时,一直平坦的大道忽然变得窄了许多,也是至此起始,道路的两旁对立站着好些精神抖擞的军士。
宁休并不清楚这匹白马的目的地在何处,他试过依靠猜测得出结论,但他最终却是放弃,此后他决定要问安远,是以他开口问道:“请问,现在我们要到何处?”
“找你要寻之人……”安远像是顿了顿,再补充道:“为你治病。”
其实宁休得到回答后想要道谢,但这区区简单的两字竟如同直生生地卡在他的喉间,任凭其如何想吐出也丝毫不见成效。
安远保持着惜字如金的状态,直到一座赤色的城门映入宁休的眼帘。
“要到了。”
这座赤色的城门自然不及鸿城城门那般壮阔,而自城门里却总传出一种让宁休觉得华贵以及威严的错觉,城门其实并不宽也不高,或许只够四匹白马一齐通过。
城门两旁仅仅立了两人,宁休视力极好却不见那二人的样貌,他知道二人定是这守城门的军卫。
白马径直地穿过赤色城门,安远甚至连步伐都未停过分毫。
鸿城这日天高云淡,初秋的景气倒也怡人,偶得少有的一片薄云蔽日,云散之时,宁休眼前的这片天地当真如同镀了几层黄金般辉煌。
骑在马上的宁休将此景收于眼底,震撼于心里。便是连此时钻入宁休耳里的马蹄之声都如那技艺高超的乐师演奏的名曲般,令他心旷神怡。
见惯了山野的宁休,几时见过这样的奇景。白马之上的那个少年挺直背,放目满是宫殿阁楼的这片天地,再度紧了紧手间的马缰。
再是过了不知多久,安远那沉稳有序的步伐变得乱了不少,宁休惊于建筑华美哪有心思看出前面那人步伐的变化,倒是现下路旁不时穿过的成队之人引起了宁休的好奇。
那些人全是埋头而行,皆是尽力地靠着路旁,宁休从未见他们走至过路中,即便是路中无人之时也尽是如此,他们有男有女,甚至包括军士,宁休看了半晌不得其解,只好作罢。
安远终是停下脚步,人与马几乎同时驻足于一长段阶梯之前,阶梯往上通向一座大殿,殿上书三字:军机殿。
“把玉佩与婚书给我,你在这等我。”
宁休望着安远步上阶梯的背影开始担心自己的病情,他自幼起常年咳嗽,且岁数越长状况越是严重,村中的孙郎中只道这是一种罕见的怪病,必须及时治愈,否则定当命不长久,孙郎中说出此话之时倒并未吓住这个少年,宁休不清楚死亡对他有什么影响,但他想治病,想见画上的那个女人一面,他清楚这是他治病的唯一理由,因为他更清楚自己真的是一个害怕麻烦的人。
宁休不是村里的孩子,当他很小的时候便从村中老人那里得知,当年是一个女人将襁褓中的他送到这个村庄,自那时起宁休的身旁便有一幅画,老人说画上之人正是那个女人,而那个女人自称是宁休的娘。
秋日投射下安远离去的背影,渐渐变得狭长进而消失。
宁休收回落在安远身上的目光,跳下马背,松开了缰绳走到白马的正面,垫起脚摸了摸它的头,露出难得的一丝笑意并朝它道了声谢。
那白马竟应时打了个响鼻,低头轻轻地蹭了蹭宁休的脸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