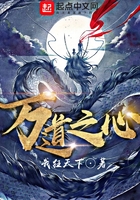谷玎吃惊地看看,原来都是他打的饭费条子,有的签字已是酒后狂草,无体无形,但最后那个竖勾总能看出运笔的遒劲,好像他把全部生命都投入进去,孤注一掷似的。他面对那些条子静默了两分钟,于是凄惨地一笑:“条子都是我打的,我认帐;宁宁的钱也不拿了,以后再说。反正不能让公家欠下你们个人的!”
金虹说:“以后?没有什么以后了,这个店我已经转让出去,过几天我就从北沙走开,再不回来!”
谷玎心里颤抖一下,半是窃喜半是刺痛,翘翘海豹胡子,言不由衷地说:“你这是干什么?咱北沙还是不错的嘛!”
金虹说:“其实你很明白,正是因为,北沙有你这样的人!”
谷玎仿佛突然被人剥光了,用锋利的解剖刀在肚皮上狠狠划了一刀,沮丧地缩起身子,一点一点小下去。他不敢直视金虹的眼睛,那双美丽的眼睛正像乙炔焊枪似的朝他喷火。他想,他也许对不住她,但他也是没有办法,总有一天,他们会理解他的难处,因为他们也会做父亲母亲。
“孩子,你就原谅一个半开化的父亲吧,”他低着头,老相十足可怜兮兮地对她说,“我不能不承认,你是个不错的姑娘,如果在别处,也许我完全能接受你们的爱情;可你要知道,这是在北沙,满大街老亲少友的,你叫我怎么办?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你应该理解我们这个岁数的人!”
金虹冷冷一笑:“算了,我们再讨论这些已经毫无意义。说吧,要我出几个大气球?一切我都是看宁宁的面子!”
谷玎说:“一个,一个就行!”
金虹说:“你打算给我来个什么广告?”
谷玎想了一下,说:“玫瑰酒家,北沙之花,怎么样?”
金虹说:“过奖了。你就写:玫瑰酒家,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谷玎说:“那哪行,那不和酱菜厂的臭豆腐广告弄混了嘛!”
金虹说:“我倒认为挺合适的。就拿你来说吧,要钱的时候把我捧上天,回头就把我贬下地,我成了什么了!”
谷玎羞臊得不行,把一张老脸揉出一波一波紫色的褶子,嘿嘿假笑着,说:“金虹,网开一面,要不然我出不去这个门了!”
幸好有一个人进屋来找水喝,才算给了谷玎得以解脱的机会。坐到汽车上他还想,得罪了金虹,那就又把谭静伤害了一次。的确,他善良的本性里隐藏着某种残酷;由此看来,他这种人不但不能经天纬地,连自我完善也很难做得到。
这种自我批判让他好不难受。
从医院里出来,李甸来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他面色苍白,形容憔悴,但脸上却带着大彻大悟的微笑。身体虚弱,走路摇晃,却给人以坚韧不拔的感觉。他的栅条式病员服在秋风里有点儿凄凉难耐的意味,有时停下脚步,亲切地摸摸哪个孩子的头发,买一点糖果之类给他们。
他凭借着记忆走进小巷。谷家的院子显现出秋天的萧索,石头甬道上落满了莎果树的叶子。莎果已经被摘光了,只有一颗暗红的小果子孑遗在树枝上,随风摇动如铃铎。他还能记起当初偷狗,他们就是用一把大号鱼钩藏在馒头里,那狗刚一吞咽,就被鱼钩勾住,大张着嘴叫不出声来,匍匐如一条鳄鱼,眼睁睁被他们牵着走,它那所有的勇猛机智全都变得一钱不值了。他为自己的胡作非为忏悔了一小会儿,这时便看到了他送来的那只狮子狗,它正蜷缩在阴暗的天空下,半睡半醒地摇着尾巴。他朝它呼唤一声:“贝勒!”它这才躬身起来,慵倦地踱到他面前。隔着板障子,他摸了摸它的皮毛。
谷毛宁带着一包新买的东西从外面回来,看见了李甸来,就让他进屋。
李甸来说:“我就是要来看看它,躺在病床上,我总是想到它!”
谷毛宁说:“你把它抱回去吧,现在你更需要它!”
李甸来说:“不用,你爸妈比我需要!”
谷毛宁沉默了。他打开门锁,贝勒就朝他奔过来。他把它抱在怀里,怜爱地用脸蹭它。
“你做了一件蠢事,”他对李甸来说,“为一个那样的女人,不值得!”
“我不是为她,我是为我自己,我真是太傻了!”
“人总会遇到沟沟坎坎。有一个女人,她非常非常不幸,从小死了父母,只能和姨一起过日子……”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女人是谁。”
“她有一次从外地回来,在火车上被人偷了,三天没吃东西,回到北沙的姨家,姨已经搬出去住了。当时正是严冬,北沙这地方滴水成冰,她站在破房框子里看着满墙白霜,看着没有锅的灶坑和冻出一个大鼓包的水缸,也想到过死,但就在这时候,她发现没有关严的自来水龙头还在向外滴水,一滴又一滴,滴得相当缓慢,然而就是这一线活水,让她鼓起了活下来的勇气,而且变得越来越坚强。跟她比比,作为一个男人,你应该感到惭愧!”
“我只能死这么一次,以后我也会坚强的!”
“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不想回家了,我回家干什么?也许,我就在北沙永远住下去了!”
“也许,咱们是相向而行,我会到你家乡那儿去生活!”
“是么?有意思!为的什么?”
谷毛宁莞尔一笑:“也不为什么。老穆哈默德说过,山不过来,我就到山那边去。--就这么一回事儿!”
李甸来从来没听说过那个陌生的名字,他惊奇地望着面前的年轻人,努力从他身上寻找和谷玎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他咀嚼着他的话,好像明白了一点点,又好像一点儿也不明白。
谷玎又到新加坡宾馆全了一圈。庆典日期屈指可数了,但桑拿浴室还没建好,谢俊放就主张退而求其次,说桑拿不上就暂时不桑拿了吧,能让客人洗上淋浴,也算不错了。谷玎说,那怎么行?我们是一诺千金的,怎么能让这个一千万元的工程功亏一篑!就召集一干人等,下了死命令,又现场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直到确认万无一失,才放心离去。
从山坡上下来,正碰上李甸来在路边闲遛。谷玎就让小孙停车把他拉上。李甸来说:“我随便走走挺好的,不坐车,一个自杀未遂,又不是人民功臣!”谷玎不容分说,伸手就往车上拽,拽到车上还舍不得撒手,说:“咱们不算什么人物,可社会需要你我这种人,咱得好好活着!”
正在街口等红灯,又看见玉秀从新华书店出来,拿着好几本厚书。
谷玎说:“玉秀,买这么多书干啥?”
玉秀平静地说:“买书还能干啥,看呗!”
谷玎接过书看看,原来都是朔黎的作品。
谷玎说:“这个叔叔也是旌旗营的,书里面不少事都是我们当年的亲身经历,多看看对你也许有好处!”
玉秀说:“他没跟你说?他不是我叔叔,他是我爸爸,头几天,他给我来信了!”
谷玎吃了一惊:“真的?这家伙搭错神经了吧!”
玉秀说:“你这是啥意思?难道他不是我爸爸?”
谷玎说:“我要是知道这个,不早就告诉你了嘛!”
玉秀说:“十七八年了,我总算有了爸爸。”
谷玎说:“有这样一个爸爸,你应该感到自豪!”
玉秀说:“自豪,当然自豪。全北沙的孩子,还谁能有一个作家爸爸,就凭这个,我能不自豪么?”
谷玎说:“玉秀,谷叔叔祝贺你。到时候你爸爸来,我说什么也在新加坡宾馆给你开一个房间,让你们父女俩好好团聚团聚。再说,这也算得上庆典的一个花絮!”
玉秀说:“行,我一定给爸爸准备好见面礼!”
车开着,小孙就说:“十个文人九个骚,剩下一个是酒包。怎么样,还不是朔黎拉拉下的种子?这种人总是像公鸡似的,踩了蛋扑楞扑楞翅膀就走,却把孩子扔在山旮旯,遭了这么些年的罪!”
谷玎喝斥他一句:“你懂个鸡巴?你这种人太现实,身上没有一丁点儿艺术细胞!”
小孙就一脸羞愧,望着他嘿嘿地笑。
忽然看见一群人围起个大圈子,像看江湖艺人卖大力丸似的。谷玎说:“今天警察咋这少,满大街看不到一个大盖帽?狗起群似的聚堆,这也太有碍观瞻了!”就下了车前去整饬,刚吆喝了两声,那嘴就张成一个椭圆的孔洞,再也合不拢了。原来人们围观的正是睽违已久的秦赖巴,只见他身穿一套肮脏的西服,领带松松垮垮的如一根吃剩的油条,细脖伶仃的坐在一只垃圾桶上,不住地打着哈欠,一根根很有韧性的黏涎联结着两片嘴唇,琴弦般晶亮有光。他的眼睛眯得极细,黑眼仁散漫地盯住一个地方不动,俨然一尊风雨剥蚀的石像。他老婆站在他身旁,咧着大嘴哭着,并用那颗蓬乱的头去撞路边的小树,那树簌簌抖动,枯萎了的叶子一片一片向下飘落。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坐在他的脚下,可怜巴巴地向他仰望,那树叶就落在他们干焦的头发上。
谷玎说:“这是怎么啦?病了还是让人偷了?”
秦赖巴媳妇发出一阵凄厉的嚎啕,有如消防车疾驰而过,上前拉住谷玎,把鼻涕眼泪蹭得他满身都是。
“表哥呀,这日子是没法过了,你得给我做主啊。这狗东西他把好几万块钱全败霍了,他挂马子,他吸白面……”
谷玎身上都凉了,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他上前扯住他那根领带,这才发现,那身行头全是名牌,西服是皮尔卡丹,领带是金利来。秦赖巴的嘴里发出一种臭鞋垫的气味,眼睛盯住他,仿佛不认识似的,抬头寻找了一下阳光,突然打了个响亮的喷嚏,唾沫喷了谷玎一脸。
人们哈哈大笑。小孙说:“这下好了,这下你省得洗淋浴了!”
秦赖巴终于睁开眼睛,好半天才对上焦距,认出谷玎来,呀一声,就握住他的手摇撼起来:“表哥,是你呀。我刚才一闭眼睛,忽忽悠悠的就到尼加拉瓜了,那一片海,那一片光腚的女人……”
众人都笑。谷玎感觉到了那生命的孱弱,如同一个容器里的水正在缓慢地流去。他看着那根细瘦的脖子,恨不能一下子将他扼死。
谷玎疑惑地问:“你知道尼加拉瓜在什么地方?你怎么知道那地方有海有光腚女人?”
秦赖巴说:“表哥,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我说了算,我让它在哪它就在哪,我让它啥样就啥样!--表哥,我忘不了你的恩情,虽说是闹个牙干口臭,可还是给你带东西回来了。”说着就从衣兜里摸出一只镀金打火机,炫耀地向众人展示一下,啪地一声揿着,然后就眯起眼睛看那淡绿色的火苗。
谷玎的鼻子有点儿酸了。他说:“你咋这么不争气,本来这一下日子就好过了,可想不到你弄成了这样!”
秦赖巴说:“可不是咋的,连我也没想到。我要是不听那个南蛮子的话就好了,我本来也是抽着玩的……表哥,我先使使行不行?使完了再给你,我俭朴一点儿,今后我用火柴!”
秦赖巴从衣兜里摸出一个三发烟盒,取出里面的锡纸,裁成两片,一片折成V字型,一片卷成喇叭筒,那动作相当娴熟,在人看来,简直就是变魔术。然后他又拿出一个青霉素药瓶,打开胶盖,往锡纸上小心而吝惜地倒了一点儿白面,均匀摊开,将纸喇叭衔在嘴上,重又揿着打火机,往锡箔底下一燎,便腾起一股虚淡的烟雾。那一瞬间他的眼睛奇亮无比,只听咝地一声,深深吸了一口进去,急忙又往复摆头,如新式电扇,那吸法极其贪婪。如是者三,那锡纸板上的白面就化为乌有。他这才抽抽鼻子,心满意足地把打火机递过来。
“表哥,我这一辈子,神仙皇帝的滋味也尝过,死也值了!”他说。
谷玎背过手去不接。他说:“他胆子也太大了,吸毒是犯法的,难道你不知道?你这条贱命搭上不算,把全家也毁了!”
秦赖巴如同刚刚充了电,精气神立马提上来,脸上的表情竟变得鲜鲜活活的。他说:“表哥,你根本不知道,这也是一种境界,这境界绝不是当了省长县长所能体会的。怎么跟你说呢?你想得到而又得不到的,在这里面全能得到。比如说我吧,那些个歌星啦影星啦,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大奶子的外国娘们啦,都被我日过了,你行么?连花旗银行波音公司中东油田都是我的,只要我愿意,随手就把台湾解放了!”
众人都惊异地咋嘴啧舌,面露神往之色。
谷玎说:“我真后悔,当初就不该拉扯你!”
秦赖巴说:“表哥,你不试试?有福同享,实践出真知,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说着就把那一套劳什子捧到他面前,很有竭诚奉献的意思。
谷玎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鼻子说:“你还敢在大街上做毒品广告,发展壮大组织?就凭你私吞公款和吸毒这两条,枪毙都够了!”
秦赖巴一听,扑通就给他跪下了:“表哥,你太好了,你咋这么理解人呢?钱我花了,别说这辈子,就是下辈子也还不上。剩下这点白面也快抽完了,不枪毙我还留着我干什么?我这就跟你们走,毙了炼巴炼巴,也不用起坟,装在臭豆腐坛子里,往烈士纪念碑旁边一埋就行!”
说着话,秦赖巴自己就来到吉普车前,奋勇地向上攀爬。
小孙说:“癞蛤蟆钻裤裆里了。咱把这家伙拉哪去?”
谷玎说:“公安局,有三十年巴篱子够他蹲的!”
秦赖巴慌了,忙说:“表哥,你咋说话不算话呢?该枪毙就枪毙,可别让我零遭罪了!”
汽车开走了,看热闹的人群也已散尽,秦赖巴老婆还在原地哭泣。李甸来看看那两个孩子,心中老大不忍,就凑上前去劝说。秦赖巴老婆看看阴上来的天说,他叔,行行好,帮我把孩子送家去吧,我这体格弄不动他!李甸来见那个小的睡着了,就把他抱起来,擦擦脸上的污垢,竟是细细嫩嫩的一张小脸,向他努着红润的嘴唇。他用手逗弄了一下,那孩子就把他的指头嗍住,一下一下嘬起来。他忽然高兴了,朝人大声喊道:“他吃我的指头,这小东西他吃我的指头!”索性就抱着他走进商店,卖了一大堆奶粉和糕点。秦赖巴老婆满脸感激,一时竟有几分羞涩,直劲道谢说:“他叔,花这冤枉钱干什么?其实管我一顿红烧肉,什么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