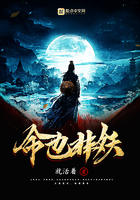原来正是张茂则请高太后过来的。太后坐在榻边,心疼地说:“皇儿,这几日朝上的事我都听说了,是不是心里不痛快呀?”神宗颇感委屈地说:“母后,都是皇儿不好。”高太后说:“在娘的眼里,我儿都好;在母后的眼里,皇儿尚须努力。”
神宗颇为动情地说:“母亲,这些日子儿臣一直在想,朕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皇帝。过去,朕只是想当一个好皇帝,使朕的子民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使朕的国家不受外族欺负。所以,朕冲破一切阻力实行变法。朕励精图治,殚精竭虑,无一日睡过一场安稳觉,可……可赵抃竟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骂我……骂我是昏君!”
高太后和蔼地问:“是不是感到委屈?”“委屈得几乎呕出血来。”神宗点头说道,“可赵老爱卿是不说假话的。朕真是个昏君吗?朕昏在何处?没有人告诉朕。是用人出了差错吗?朕深知,吕惠卿、王珪、邓绾、李定等人的毛病,可朕是在用其长避其短呀!变法图强没有人拥护,如何进行?还有,驭臣之术,历来是清浊并用的,否则,皇权就会旁落他人之手。朕究竟错在何处呢?”
高太后微微笑道:“孩子,天下谁都可以叫屈,唯独皇帝不能。因为天下都在你的股掌之中啊。赵抃骂殿、范镇打殿虽然伤了你的帝王之尊,但也事出有因啊!你可知道我们家的江山是怎么来的吗?”神宗答道:“母后,朕知道,应该感谢这些老臣。但作为皇帝,我不允许他们以此来挟持我,左右我,不能因此干扰朝政。”高太后摇了摇头,说:“你说得不错,不过这‘挟持’二字恐怕是他人的蛊惑之言。韩琦、欧阳修、司马光、范镇、赵抃,都为你的父皇接过这江山立下了不世之功,但他们没有一个向我们索取什么。他们敢于直言,都是为了你的江山社稷,他们为此不怕丢官丢命。这样无私事君的忠臣,不正是你成就伟业要依赖的人吗?现在韩琦、欧阳修都先后去世了,范镇、赵抃也已暮年,每失去一个,都是失去国之柱石啊!”
神宗若有所悟,但又接着说:“不过,皇儿未料他们竟然冒死保苏轼。”高太后意味深长地说:“那是他们在为你保护国之重臣。孩子,苏轼的才干远在王安石之上,早在变法之初,苏轼就提出徐立徐行之策,并为你献上三策。如今看来,都被他言中了,难道你还怀疑苏轼的才德吗?”神宗回忆起此事,不免为之一惊。高太后接着说:“自古忠臣,多有逆耳之言,且以媚上为耻。唐太宗胸阔如海,才得以纳百川之流,从而有了贞观之治,也由此成就了他的大自尊。”
神宗恍然大悟。高太后笑道:“孩子,你明白就好。朝堂之上,诗案之事,百官放言,只需察言观色,即可辨忠奸。苏轼的案子,还须仔细斟酌啊!亲贤臣,远小人,你要切记,否则大宋危矣!”神宗说:“多谢母后指教,孩儿谨记。”
送走母后,神宗独坐御榻,沉思良久。他召来一名内侍,秘密吩咐如此这般……
入夜了。月光如水,缓缓泻进御史台监狱苏轼的囚牢中。苏轼正枕肱酣睡。突然一个黑影窜了进来,拣了与苏轼相对的墙下倒头便睡。苏轼翻了个身,以为又关进来一个犯人,未予理睬,仍自睡去,不久鼾声如雷。那人躺在一边,捂耳挠头,被鼾声惊得一宿不得安眠,辗转反侧到天亮。
那人便是神宗派来的内侍。他天明后即刻回宫禀告神宗:“陛下,奴才昨夜奉旨探监,睡于苏轼一侧。不料,苏轼整夜鼾声如雷,搞得奴才一夜未睡。”神宗大笑道:“这就是了,说明苏轼胸中并无亏心之事。大凡喜欢诽谤之人,若身陷囹圄必有怨恨之言,且不能入睡。”这时他已有了赦免苏轼之心。
寒冬终于过去了!
圣谕下达了:责授苏轼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自八月十八日被逮入御史台监狱以来,苏轼被关押了将近百余日。牢狱中艰苦恶劣的环境,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虚弱憔悴而略显衰老了。但他倔强倨傲的脾气却不曾受一点摧折,放达诙谐的性格仍显露在炯炯有神的目光里。
他扑打着满身的尘土草屑,乞丐般地走出监狱大门,感受那久违的阳光和春风的气息,一切都像历经劫难后的重生一样富有生机!显然,由于久处黑暗,他一时不习惯外面刺眼的光亮,但很快就享受着身心不受羁管约束的畅快。诗人本真的性情又开始恢复,溢于言表了。无限的诗情已在心中开始酝酿!
范镇、赵抃、苏迈已在监狱门外等候,其身后停着一辆马车。
“父亲!”看见苏轼出来,苏迈马上迎上前去。
“子瞻!”范、赵二老也步履蹒跚地走去,一把拉住苏轼的手。“二位老爷子,我们这不是在做梦吧?”苏轼说罢,已是涕泪横流,二老也都老泪涟涟。范镇说:“过去是恶梦,现在是喜梦。”又看了看苏轼说,“头发都灰白了啊。”苏轼笑道:“老爷子,白了好,头发白了就老成了。”
赵抃感慨地说:“子瞻哪,我们这可真是两世为人哟。”苏轼愕然不解。范镇解释道:“他为了救你,把圣上都骂了,结果差点被斩。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他这瘦猴子就到阎王爷那里称臣了。”苏轼连忙施礼道:“哎呀,二位老人家,这个人情债太大了,我可还不起啊!”赵抃笑道:“哪里哪里,不光为救你,也是尽人臣之本分。哪里有人情债哟!”
范镇故作嗔怪:“脾气还是不改,只顾打趣了。还不快见见儿子。”“父亲!”苏迈扑到苏轼怀里大哭起来。苏轼也哽咽道:“好孩子,别哭了,为父对不起你们了。”
赵抃从旁劝慰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范镇也笑道:“对咯,大磨难造就大贤臣。走吧,上车再说。”
苏轼也拭泪而笑,自我解嘲道:“看看,我在乌台几个月,连澡也洗不了,养了一身虱子。我还是骑马为好,免得同乘一车,让乌台的虱子也咬了二位大人。”范镇笑说:“你身上的虱子,怕是也比李定有学问!”苏迈不由得破涕为笑。
赵抃说:“这次‘乌台诗案’,景仁兄、司马光、黄庭坚各罚铜二十斤;张方平三十斤;驸马王晋卿被削去一切官职;子由被贬筠州酒监;王巩被贬为宾州酒监。”范镇接过话头说:“你嘛,被贬黄州,做什么团练副使,不得签书任何公文。黄州安置,与软禁差不多。总之,不管老屁股嫩屁股,该挨的板子挨了,不该挨的板子也挨了。”
苏轼不禁叹道:“以诗获罪,古来未有;千古奇冤,归于一哭。”
范镇打趣道:“看来子瞻这回是只哭不歌了!”赵抃说:“子瞻怕不是这样的人。”又回头问苏轼还作诗否。苏轼笑道:“不作诗怎么对得起李定他们呢?现在就有两首。”范镇忙催着念给大家听听。
苏轼随口吟道: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连翩鹊啅人。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捻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范镇拍手笑道:“好个‘试捻诗笔已如神’,子瞻的骨头还是硬啊!”
苏轼接着说:“还有第二首。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苏迈大惊:“父亲,最后一句可又得罪人了!”苏轼佯装大惊:“又闯祸了?”赵抃说:“如今天下忌讳说‘少年’二字啊!”三人会心相视,哈哈大笑。
苏轼听苏迈说王巩被贬往宾州,不日开封府差役就要催着上路了,急忙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叫上苏迈一起前去探望。苏迈劝道:“父亲刚出狱,身体虚弱,先歇息一两日吧。”苏轼坚决地说:“定国受我连累,远贬千里之外,如此恩德,难以为报啊!”苏迈见拗不过,急忙搀着苏轼出去。
到了王巩府中,只见家人正在收拾物什,准备启程。王巩在房间内对众夫人说:“我求求你们,不要跟我到贬所。远去宾州,一路千山万水且不说,我干的是酒监,说白了就是卖盐卖酒的。你们三人跟着去,吃不了那个苦啊!”他那三位夫人倒是十分坦然,英英叠着衣物道:“你能受得,我们怎么就受不得?‘乌台诗案’被贬的官员,都是一家一家地走,我们怎么能分开啊!”盼盼正在整理书籍笔墨,接过话茬说:“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俚闾卑巷且如此,何况我等是知书达礼之人。”卿卿正装箱子,跟着说:“就是。你以为我等是图你富贵来了?恩爱大于天。”直说得那王巩七尺男儿也忍不住掉泪。
苏轼听罢三位夫人的高论,拄着拐杖踱步进来,笑道:“怎么,这就开始打点行装?”王巩急忙迎上前去,又惊又喜,抓着苏轼的手说:“子瞻兄,我们正要去看你呢,想不到你先来了。”三位夫人也停了手里的活计,纷纷围拢来。苏轼潸然泪下,说道:“定国,我的好兄弟,愚兄身陷囹圄,很多亲友都避之唯恐不及,而贤弟与几位夫人却仗义援手,大有古君子之风,请接受愚兄一拜。”言毕,苏轼一躬到地。
王巩连忙扶着说:“子瞻兄,折杀小弟也。你我本是兄弟,小弟岂能做负义之人。”苏轼又转身向三位夫人施礼,吓得三位佳丽连忙还礼。苏轼解嘲道:“愚兄是个穷骨头,连累你等远谪千里荒僻之地,让愚兄如何受得了啊!”英英哭道:“大人千万不要这样说,只要你平平安安出来了就好。这一百多日以来,姐妹们与定国无日不以泪水洗面,现在好了,该高兴才是。”盼盼拭泪道:“大人到黄州后,万事要想开些,不要忘记鸿雁传书,我等及时互通消息。”卿卿道:“大人受苦了,我等终于见到了你出狱的这一天,过一个磨难一重天。我嘱咐他们设宴为你压惊。”
苏轼本不忍看王巩一家离散,心中不免难过,待听见这三位夫人情深义重,好言劝慰,又心头一暖,含笑答道:“多谢多谢。贤妹们,愚兄害得你们颠沛流离,这京城的故相府也不能住下去了。”盼盼坦然笑道:“看你说的,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不禁大加称赞道:“好啊,‘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夫人真是有菩萨的大悲悯、大智慧!”众人都含泪而笑。
苏轼又听说驸马都尉王诜也被贬筠州,特地前去问候。一进门,王诜就上下打量着苏轼,也不施礼,歪着头问:“是人还是鬼?”苏轼笑道:“入狱前是人,入狱后是鬼,如今出狱了,非人非鬼。”王诜反问:“莫非成了仙佛?”苏轼解嘲道:“是啊。不过,这次我应当感谢李定他们,让我多活了一百多年。”王诜不解。苏轼接着说:“大牢之中,度日如年,一百多日,不恰好一百多年嘛。古人说磨难长见识,不无道理,一日一年,自然见识就多了。”王诜笑道:“有理有理。应该把王珪那个老杂毛和李定一伙投进去,叫他们也长长见识。”苏轼摆摆手,说:“此言差矣。读书还请先生呢,长大见识的好处怎能轻易送给他们呢?他们只有死了以后才有资格入地狱。”两人都哈哈大笑。
说到这,王诜叹了口气:“唉,是我害了你,要是不给你出诗集,不给王珪那个老杂毛,焉有‘乌台诗案’?”苏轼笑道:“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他们早就在收集我的诗文了。只是,你的官职都没了。”王诜说:“无官一身轻,只要叫我画画就行。只是我天资有限,怎么卖力也不能望你项背啊!哪像你,随手一写一画便成大家!”苏轼平和地说:“你倒羡慕起我来了。大家怎样,小家又如何?昨日,定国的夫人盼盼告诉我,‘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你我连一个小女子都不如啊!”王诜也叹服不已。
由于差遣日期紧迫,不敢迟滞,次日苏轼就要启程离京。二人絮絮谈到深夜,苏轼便起身告辞。王诜说要去送行,苏轼婉谢:“不必了,免得又有人从中再生事端。在京诸人受我牵累的,都已一一拜望分别了。还请晋卿兄多多珍重。”说罢,二人洒泪而别。
元丰三年正月初一,正是新年。苏轼告别了京中诸友,独与苏迈骑驴挑担,冒着寒风,缓缓向南往黄州而去。
出都门便是近郊,只见官道绵延,隐没在一片寒林之外。荒村中农舍倾颓,一派萧索的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