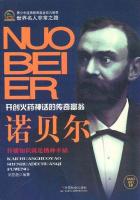这时,神宗慌忙进来问安。太皇太后让神宗起身,看着他问:“哀家听说,苏轼下狱了?”神宗点了点头,太皇太后接着说:“哀家曾记,嘉祐二年,殿试完毕,仁宗帝喜形于色,说‘朕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二人,苏轼、苏辙兄弟是也’。恍如昨日。如今这位太平宰相没坐在相位之上,反倒坐在监牢之中。唉,必是小人中伤。咳,咳,咳……”太皇太后一阵咳嗽,神宗忙上前捶背。太皇太后缓口气说:“哀家恐愈之无望了。你勿再冤枉无辜,神灵不容啊!”言毕,老泪纵横而下。
神宗哽咽着说:“孙儿谨遵皇祖母教诲,定赦天下死罪,以求上苍,保佑皇祖母。”太皇太后摇头说:“不必赦天下凶犯,唯放一苏轼足矣!”神宗惊愕不已,但很快恢复平静,低声说:“请太皇太后放心便是。”
却说苏迈得知范镇要来京城,欢喜异常,忙去驿馆接他老人家。王巩三位夫人照例给苏轼做好饭菜,装在食盒内,请一个管家送到梁成家中,再由梁成拿进牢房给苏轼。苏轼揭开食盒,看到里面烧了一条鱼,大吃一惊,不禁呆坐在床边一言不发。
梁成还以为是今天的菜不合口味,便解释道:“苏大人,苏公子今日好像去接范大人了,是王大人家管家送来的饭。大人要是觉得不合口味,我这就另给您换一份饭菜来。”苏轼有些颓然地说:“不用了,梁成兄弟。你把它吃了吧,这么些日子多谢你的照应。”梁成憨厚地笑道:“苏大人说哪儿的话。”
苏轼问道:“你实话告诉我,外面是否听到了什么消息?御史台的判决是不是定下了?”梁成不解地说:“没有什么消息啊?大人吉人天相,不会有事的。大人,你不必想得太多,历朝历代,哪有因为写几首诗就掉脑袋的?圣上虽受小人蒙蔽,但毕竟……不会这么做的。”原来,苏轼和苏迈约好,如果朝廷定了他死罪,就在送饭时送一条鱼。苏迈去接范镇,竟忘了嘱咐厨子不要做鱼。英英、盼盼、卿卿三姊妹听说苏迈外出,忙到厨房照看厨子为苏轼准备饭菜,见厨子做的都是清淡菜肴,商议着应该给苏轼改善一下,便命厨子做了一条鱼。
苏轼望着碗里的这条鱼,不禁凄然神伤,拿起桌上要他写供词的纸笔,慨然成诗:“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和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苏轼因诗获罪的消息同样传到了洛阳。在司马光的独乐园内,前夜的大雪已铺满了整个庭院。仆人吕直清早起来,正欲拿着扫帚扫除积雪,却见地上早已留下了一串串脚印。司马光正站在小园花圃边上,对着一树老梅沉默不语,良久,又不住地徘徊叹息。吕直小心翼翼地问:“先生,今年的雪来得可早啊。”司马光仿佛没有听见,绕到墙角一丛翠竹前,仰首不语。吕直不敢再问什么,悄然走开。那竹枝虽被大雪压得弯了腰,却显得更加苍健了。
当年司马光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便自求隐退于洛阳,蜗居于独乐园内,潜心撰写《资治通鉴》。但他并非全然忘却朝政,而是时时刻刻关心着朝廷的政令举措,思考着大宋社稷的未来。他得知苏轼因作诗而下狱,愤懑不已,但又无法营救,还被新党小人指斥为朋党,愈觉忧闷,所以才独自踏雪徘徊。他素来钦佩苏轼的人品才干,以学问道德相交,引以为君子同道,尽管在变法的意见上并不能达成一致,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私人情谊。苏轼是当世贤才,却一直沉抑州官,不被重用,这回又因诗得罪,系于囹圄,受尽狱吏呵骂鞭棰之辱,岂非我朝百年文治之耻?朝中奸邪用事,嫉贤妒能,蒙蔽圣听,迫害忠良,只怕天下有识之士都要畏祸缄口,致国事日非了。想到这里,司马光全然忘记了冬晨的寒冷,茫然立在雪地里一动不动。
这时,范祖禹从读书堂走了出来。范祖禹是范镇的孙子,一直追随司马光著书。他忧心忡忡地说:“恩公,‘乌台诗案’至今未结,不知圣意如何?”司马光这才回过神来,叹道:“是啊,祖禹,凭你祖父的脾气,欲做之事无有不成。可这次上了奏章也没有救下苏子瞻!”范祖禹说:“看来我大宋的清明文治,要被这‘乌台诗案’玷污了。”
司马光点点头,满脸沉郁之色:“老夫历来主张‘责君严’,现在的台谏不责君只责臣,哪里是什么忠君?分明是奸臣当道,弄权误国!”范祖禹说:“他们置圣上于不仁不义之地,我真担心苏公的处境啊!”司马光背手踱步,仰天长叹:“我又何尝不是呢?他们就是要把持不同政见的人彻底除尽。王安石只是拗,但他毕竟是君子。这些人就不同了,他们是小人,是恶人,是大奸大恶!”他转身接着说:“我给圣上写了一份奏劄,今天你把它送给朝廷。”范祖禹领命而去。
开封皇城内。众大臣正聚集殿外,等待上朝。正谈说之际,李定窜到人群中,扬扬得意地大声嚷道:“苏轼真天才也。二十二年前写的诗,竟倒背如流,一字不差。”众人都鄙夷其为人,故意不去理会。李定自觉没趣,怏怏闪到一边,见王安礼、章惇面沉似水,目光逼视自己,心中愧惧,只得像丧家狗一样躲开,转身向王珪作揖,满脸堆笑。王诜怒目直视王珪,见他扬扬不睬,正欲上前怒骂一气,忽听得内侍高喊“时辰到”,才不得不收敛盛怒,整理衣冠,随众官列队步入崇政殿。
神宗临朝坐定,李定立刻闪出奏道:“陛下,经过四十五天的审问,苏轼诗案已经问清。苏轼对诽谤朝廷,影射陛下,攻击良制美度供认不讳,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按律当处极刑!”群臣窃窃私语,一阵骚动。王诜拂袖大骂,章惇气结无语,王珪却恭敬低首,不赞一词。
李定见神宗并不回话,愈加趾高气扬:“此案涉及人员众多,其中包括司马光、范镇、张方平、苏辙、李常、孙觉、刘攽、黄庭坚、王巩、王诜、秦观等二十二人。驸马王诜,素与苏轼来往密切,互相唱酬,互赠礼物。案卷中已经详记,酒食茶果,笔墨纸砚,弓箭裙带已经列出。上述之人,与苏轼勾结一起,狼狈为奸,视新法美度为眼中钉、肉中刺,全然目无朝纲,蔑视人主,怀不臣之心,已经久矣。若不严办,我主所行之尧舜大业,定毁于此等人之手。”奏毕,伏地不起。
神宗一边听着李定启奏,一边御览案宗,脸色沉郁,一语不发。李定以额贴地,屁股撅起,不时抬头看看神宗,见神宗不语,又俯首长跪。
张璪乘势出班奏道:“陛下,从苏轼与诸大臣的交往信件中,更能看出苏轼的怨毒之心。”舒掸也跟着说:“陛下,微臣审查了苏轼与范镇等人的信件,这些人冤枉圣上,对新法怀恨在心。若不严惩,则国无宁日啊。”直说得声泪俱下。见朝堂上气氛肃然,愈加斗胆哭奏道:“伏望陛下处苏轼极刑,褫夺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孙觉、苏辙、刘攽、王巩、王诜等人的官职,永不叙用!”众臣大惊,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有王珪袖手旁立,恭敬自若,但嘴角却闪现出人们不易察觉的冷笑。
神宗愤愤地将奏章扔到御案上。朝堂上霎时安静下来。
此时,范镇正在怡心宫内拜见高太后。范镇这次回京,显然是为苏轼而来,但他并未急着面见神宗,而是先来与高太后叙旧寒暄。高太后见了这位三朝老臣也十分高兴,让他与自己对面而坐,问道:“范镇啊,你这一去就是八年,身子骨还结实吧?”范镇于座上拱手笑道:“托太后的福,还好。老臣今日见到太后康健,格外高兴,此乃朝廷之福、天下之福啊。太后啊,老臣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高太后知他快人快语,忙问何事。范镇说:“老臣已是黄土埋到脖子上的人了,脱了今日鞋和袜,不知明日能否穿。但老臣处江湖之远不忘吾君,此次进京面圣,不为别的,就为这‘乌台诗案’而来。”
太后早已猜到他定为苏轼而来。关于苏轼入狱,她也早有耳闻,屡次对神宗好言相劝,不得妄杀读书人,坏了祖宗家法,何况苏轼又是先帝仁宗亲点的儿孙宰相呢?只是神宗一意变法,为奸邪小人所蒙蔽,连她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她深知范镇忠直可嘉,便问道:“不知卿家对‘乌台诗案’有何高见?”
范镇直言道:“《诗经》乃孔子删定,不乏刺政之言,圣人称为美刺。故汉以降,无有以诗定罪者。今日以诗问罪子瞻,圣上开了文字狱之先河。由此,我大宋开明之政蒙了灰尘,皇上圣明的美誉也有毁损。另外,苏轼之诗,问世已经有年,传播甚广,台谏未必不知,何以在今日旧事重提,以罪相加呢?对变法持有异议者都有大难临头之感,以后谁还敢对朝政进献忠言?老臣恐怕从此之后,我大宋清议之美政亦不复存,上下只有阿谀献媚之言了。如此一言之堂,若朝政有失,直臣则不敢言;若奸臣当道,忠臣则不敢出。如此,大宋江山,何以久乎?”
高太后点头称是:“这也正是哀家日夜忧心的啊!本宫当力劝皇帝,保苏轼无虞!”范镇立即离座下拜:“多谢太后。太后啊,老臣垂暮之年,退而进言,除忠君为民之外,还因仁宗帝临终有言,托臣翼护旧臣、忠臣!”并从袖中取出一支金牌令箭,呈递给太后。太后为之一惊,诚惶诚恐地接过,再三查看后确信无疑地说:“不错。是先帝神器。太皇太后有言,若出乱臣贼子,无须担心,自有持神器之人挺身力挽狂澜,所指即是范公了。”范镇点点头。太后将令箭交还范镇,说:“神器不可轻易示人,望范公收好。”范镇连忙说:“太后应直呼老臣之名,不可以范公称之!”太后说:“你手持先帝神器,自当与一般朝臣不同。”范镇坚执固请:“朝廷有法度,不可乱了。”高太后只好应允。
范镇感激太后深明大义,备受鼓舞,朗声说道:“太后,李定等人若置苏轼于死地,老臣就不得不大闹金殿,请太后恩准。”高太后大惊,忙说:“此乃国家大事,你如此信任老身,哀家又怎能违背先圣之意呢?只是哀家不能干政,你应大胆行事,不要负了先帝之托,这也是对当今皇帝的爱护。”范镇高兴地说:“若如此,真乃大宋之福也!老臣有礼了。”说罢,便要跪拜。高太后忙起身相扶:“哎呀,快起来,不可不可,你怀揣神器呢!”
这时一个宫女神色慌张地跑进来:“太后,不好啦,太皇太后薨了!”
高太后大惊失色:“你说什么?”
崇政殿内,内侍忽然哭着跑进朝堂,跪于地上启奏道:“陛下,太皇太后薨了!”
满朝哗然。
神宗惊闻噩耗,瘫软在龙椅之上,当着大臣的面痛哭起来:“皇祖母啊……”张茂则一面抹着眼角的眼泪,一面上前来劝慰神宗节哀。众臣“呼啦”一声都跪在地上,哀泣之声遍满朝堂。神宗哭道:“难道真如皇祖母所说,冤枉无辜,神灵不容……”又指着舒掸大声喝道,“你,给我出去!”
舒掸抱头鼠窜,悻悻退下,王珪、李定都吓得不敢出声,兀自装出一片哀戚的神色。神宗已无心绪上朝,下旨道:“搁置诗案,办好国丧!”
张茂则大声宣旨时,王珪暗暗松了口气。他本来盘算着唆使李定等人将苏轼定个死罪,不想触怒天威,早已吓得汗如雨下。但如今正值国丧,诗案搁置,神宗定无精力来穷究此事,自己也正好免受皇上责罚。他又盘算着借此机会将苏轼远远发配了事,待神宗日后再问起,便是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了。想到此,王珪又心下暗喜,但还是满面哀戚地随众臣退下。
御史台监狱内,梁成慌慌张张地跑进苏轼的监牢中来,气喘吁吁地说:“大人恐怕是要在这牢中多待些时日了。”苏轼忙问为何。梁成接着说:“太皇太后归天了,诗案搁置起来,在办国丧呢。”苏轼将信将疑,待追问梁成后方知实情,不禁捶胸顿足,放声大哭。他想起嘉祐二年进士登第后太皇太后曾在宫中接见过他,勉励他忠君报国,那时他意气风发,如今身陷囹圄,壮志未酬而斯人已逝,不禁悲从中来。梁成忙好言宽慰,苏轼收泪说道:“梁成啊,太皇太后是有史以来鲜有的好太后哇。”梁成也感泣不已。
这时狱卒送饭进来,提着一只大桶,往苏轼的碗里舀上一勺,便欲出去。梁成看那碗中,全是些残羹剩饭,混着些脏兮兮的菜汤,一股馊臭味儿,实在令人作呕。梁成看不过去,一把拉住狱卒说:“苏大人自有家人送饭,送这些猪狗食来做什么?”狱卒不屑地挣开他说:“梁成,你少管闲事。上方有令,以后不准苏大人吃家人送的饭。”说完扬长而去。梁成仍愤愤骂道:“王八蛋!苏大人,这个不能吃,我回家给您偷偷带点吃的来。回头我会告诉苏公子,让他以后不用送饭了。”
苏轼双手擎起饭碗,稍微闻了一下,说:“别连累了你。别人能吃,我也能吃。”说完就要吞一口,梁成赶忙制止说:“哎呀,大人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残汤剩饭不说,什么脏东西他们都往里扔,里面有吐的痰,有沙子,有鸡屎。蔡确当御史中丞的时候,就用这个法子审了一批官。结果,大家宁愿认罪,不愿再待在这个大牢之中。”苏轼为之一惊:“竟有这等事?”梁成说:“想不到吧。蔡确为了往上爬,整了不少人,用诬告把对手整进来,再用这法子把人整出去?所以,案子没有破不了的。圣上呢,认为他是干练之臣。最后,他上去了,别人喊冤叫屈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苏轼倚在墙上不再言语,陷入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