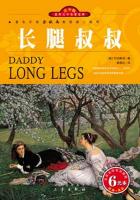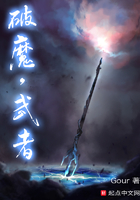“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家吧。”她说。我也没多推辞,反正一个办公室。她猛地一起动离合,我下意识地抱紧了她腰。
“李涵穹!”刚到家属院门口,一个低粗惊吓的声音喊我。蓦然间,我酒醒了,我知道这声音是谁,我太熟悉这声音了,这是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声音。她领着芠修在外面散步。我让小王骑车向前走,下了车和她说话,她不说,我们默默地回到家。
“没有别的意思,路上碰见了,办公室小王正好把我捎回来。”我解释着。
“呜呜呜呜,明明我看见你抱着那个骚狐狸!”她大哭着。
“车跑得那么快,我又喝了酒,我摔下来怎么办?我本来和她也没有什么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知道我不该这样做。
“喂,五叔!”我听见她在屋里打电话,“李涵穹在外面有女人,我和芠修看见那女的骑着摩托车带着她,李涵穹在后面抱着她。你也不管一管?他别想离开我,别想和我离婚,就是砸断他腿我养着,我也不离,我也不能让孩子没有爸爸。”
“真有这事?等着我找涵穹,这混蛋!”五叔在那边说。
“喂,表哥,李涵穹在外面和女人乱搞,让我逮着了,我看见那女的骑着摩托车带着她,李涵穹在后面抱着她。等着我找他爷爷讲理。”她在给我二姑家大表兄张涛打电话。
“喂,表姐,李涵穹在外面和女人鬼混,我和芠修看见那女的骑着摩托车带着她,李涵穹在后面抱着她。呜呜呜,你们要管一管?”她给远在天津我最要好的表姐说。
“……”
“他妈的!你有完没完,就这么点事情,你还想让江泽民、布什知道啊?”我一脚把门踹开。
1998年的秋天如女人的身体生理变化那样有规律地按时来到,白浪河边依依杨柳在瑟瑟秋风中,无力地摇晃着孱弱的肢体,片片淡黄色的柳叶如扁舟无数羽毛翩翩悠悠而下,落在河面上,撒下一片秋天的凄凉,铺下一层无奈的飘零。
一场秋雨一场寒,医院的花园里一片绿肥红瘦,带着无限凋意。“芠修,快点,我上班要晚了。”早上,我给芠修穿上外套,骑上当年表兄为父亲住院方便送我的“大金鹿”自行车,带着芠修穿越大街小巷,急急地向医院赶去。
“爸爸,我妈还在家里呆多久,她怎么不上班,你每天都这么紧张?”芠修坐在我后面问我。
“你妈不是说她有病吗?别管那么多,好好在幼儿园玩,画好画。”我说。
“老爸,停下,停下,先买画笔,没画笔了。”芠修在后面叫着。
她又接近20天没上班了,秋寒使她得了一场感冒,几天后她一直喊头疼,到神经内科做了脑电图,稍微有点异常,医生说考虑脑炎,先观察,不着急。可她非要住院,医生无奈,开了住院单,这一住就是半个月,出院后在家里休息。
“涵穹,小刘还不来上班啊?这20多天了,我们考核怎么办?她奖金怎么发?说实话,要不是看你在院办的面子上,这奖金早就该扣了,你说,她来人民医院三天两头歇病假,上了几天班啊?档案室这么轻松的活,她还这样,幸亏不是临床科室。”我正在忙着筹备医院伽马刀开业,她的主任赵同心给我打电话。
“赵主任,实在不好意思,我也是拿她没办法。你放心,我让她尽快上班。哎,赵主任,晚上潍坊档案局王局长请客,你们是同行,你也参加吧,前两天我去沂山,带回了当地的一些野生蘑菇,顺便给你尝尝。”我说。
“行啊,晚上我参加,正好我也要找王局长有事情。如果小刘没好利索的话,你让她在家里休息好,别留下病根。”赵主任说。
“谢谢!赵主任,谢谢!我回去好好做她工作,让她上班。她老这样,我也不好意思。”我说。
“今天,赵主任找我了,你差不多还是快去上班吧,反正坐在那里也是喝茶水,没多少事情。不然,我在办公室,这脸上哪放?”晚饭后,我蹲在阳台地板上,拿着一把剪子修剪着杂乱的茉莉花树。
“我也想去上班啊,这没法去上班急死了。可这腰疼就是没办法,也还是头疼。哎,我问你,你看这里,是不是肝啊?我怎么也感觉不舒服?下边还痒,我去医院化验,说是阴道炎。”她腰上缠着个大护带,趿拉着拖鞋,手扶着门框,像深秋公园里一个踯躅郁行的老人,金黄色的银杏落叶在身边忽悠悠飘零着,像是翻阅着沉重的岁月,厚厚的落叶使她本来就不利索的腿脚更加不便。树叶里横着一条大树根,一个踉跄,差点绊倒,她急急地用手扶着一棵杨树。树林深处,我和芠修舒展着柔软的身体像松鼠一样在树丛里蹦来蹦去,时而练个倒立,时而在一根横枝上作引体向上……
看着她这老态龙钟的样子,我心头一阵悲哀。
“我说你是不是有抑郁症啊?你整天哪来的这些病,这里是病那里是病,我看你是心理有毛病,你头发梢是不是感觉也疼啊?你整天把药当饭吃,我看从你身上割块肉都可以当药吃,你阴道炎该我什么事?难道我还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带给了你病?你也不想一想,你整天吃这么多药,不引起体内菌群失调吗?”她这一说,我火又上来了,“不仅是你,孩子得个感冒,你不分轻重,滥用抗生素,哪个药好你用哪个。结果孩子身体更差,好好的孩子我看都得让你毒死。”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你胡说八道!我何时对孩子这样?孩子感冒不都是我管吗?你管了几次?”她反问。
“我管了几次?我是没你那么上心,可孩子不就是个感冒吗?你我小时候感冒吃过药吗?孩子感冒不厉害,拖拖就好了,哪有你每次那样对孩子的。恨不得用药把孩子包起来,你这是对孩子好吗?天底下哪有这种畸形的母爱?”这不知咋的,又扯到孩子身上来了,我更火。
“得了,得了,李涵穹,我不和你吵了,两口子就那么回事,不就是因为有一个孩子?”她“嘭”一声把门关上了。
“你听着,你再不上班,医院扣你奖金我可不管。要不是看我面子,早就该扣你奖金了。”我说着,拿起朋友给我的两块树皮画顾自欣赏着。
1998年10月30日,我正在值班,无聊地浏览着各种报纸。我并不关心报纸的那些新闻,那些东西发生在身边但对我来说很遥远,真正引起我兴趣的是那些乡土风情文学板块,同时还为芠修收集各类绘画和刊头设计。办公室报纸多的是,书记、院长、副书记、副院长每个人办公室报纸订了六七份,领导忙得没时间看,那么多报纸倒像是给我订的,静静地躺在那里等着我去欣赏。每次原封不动地从报刊架上撤下来后,我先过滤,无用的当垃圾卖掉,有价值的我就收藏下来,阴雨连绵闲情逸致的时候再分门别类剪裁。《齐鲁晚报》的“青未了”,《潍坊晚报》的“潍河两岸”“石笏园”“人在红尘”,《潍坊日报》“周末版”等都是我特别关注的主要版面。这些版面多是红尘男女、月下低语、情感倾诉、文学述评、乡土风情、凄婉怀旧、往事情怀,而这些则是我最喜欢嚼之如甘饴,让人回味似水流年,恰似清冽醇香的甘醴。眼前的一版“青未了”是“一声叹息”,故事的主人公“我”讲述的是“我”和老公婚后老是吵架,双方几次下定决心离婚,但在女儿的哭声里,屡次恨恨地收起无聊的杀手锏。几年冷战陌生的生活,已是形同路人,女儿成了他们生命中唯一的支撑。“我”清雅高洁,盼望浪漫永恒的爱情,觉得他俗不可耐;他庸俗世道,觉的“我”清高刻薄。他在仕途上不断进步,并且在外面有了女人。在不停的吵架摔东西,互相厮打中,双方无法忍受仇敌般的关系,再次提出离婚,但他因为提拔顾及名声又悔改。文章的最后写道:“在外人眼里,他们还算是恩爱夫妻,夏天晚上一起出来散步,双休日也带着孩子到婆婆那里去。工作稳定,衣食无忧,心情不好也不坏,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失望。‘我’常想,到了老年后,或许像许多人一样,互相搀扶着,感动年轻人的那种白头偕老,但偶尔孤床失眠的夜晚,‘我’想着他正和那个女人颠鸾倒凤,会突然难过地哭起来。哭‘我’干尸般的爱情,哭‘我’无法说出的苦楚,哭‘我’永远也无法实现的对于爱情的梦想,哭‘我’这一生是如此的遗憾:没有遇到我心仪的那一半。”
“李老师,你好!今天的报纸来了。”我正低头顾自欣赏,收发室的王如英进来了。
“好,谢谢,放桌上吧!”我头稍微一抬,礼貌性地打招呼。眼睛不经意地扫向《潍坊日报》第一版。赫然印着一条新闻:市委组织部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充实乡镇。大意是,为充实乡镇干部,提高乡镇干部的整体素质和管理水平,市委组织部决定近期在全市各单位选拔一批副科以上、年龄40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的年轻干部带着工作关系和组织关系下派到12个县市(区)乡镇担任乡党委书记、乡镇长或党政副职。
对于这样的新闻,我真感不起兴趣来,组织部组织这样的事情多了,也不知这次有没有真事,况且是副科以上。我来人民医院,虽然是硕士学历,但就是一名普通职工,想去也不够条件。
“李老师,这是卫生局的几份文件,你签收一下。”王如英说。
我签完,拿过来翻看着,无非是关于加强医德医风,提高医务人员整体素质的一些文件,还有几份关于全市卫生系统赴九江抗洪的表彰决定,最后一份是卫生局转发市委组织部选拔年轻干部下乡镇的文件。我根据每位院领导的分工,分好文件,把组织部这份文件在文件阅办单上写下:请张院长阅办。拿起那嘀里嘟噜一大串钥匙,打开每个院领导房间,把文件放到他们办公桌上。
第二天早上,大老板张院长来了。“张院长,您好!桌上有几份文件,请您批示。”我跑着小步把他办公室打开。“这一份组织部的文件要求我们下周四前把要下去的人员报到卫生局人事科。”我顺手打开空调并擦了一把他的椅子。
“这份文件明天开院周会你让王院长传达。哎,你也可以申请下去啊,趁着年轻多锻炼锻炼,研究生毕业也相当于副科啊。”张院长说。
“好,谢谢张院长。我考虑考虑。”我说。
没想到张院长会这样支持我,能有这样的机会,我无须考虑了。从他办公室出来,我一阵欣喜。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在仕途上闯一闯,以后或许能从乡政府慢慢地进入县政府、市政府,做一名受人羡慕的国家公务员。有这样的机会,我可以摆脱在院办尴尬的位置。那专科毕业混了八年才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的梁水视我如眼中钉、肉中刺,整天拉着个故乡“龠龠”那样小的麻雀疤疤脸,恨不得让我立刻从他眼前消失,就怕我顶了他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可以摆脱这种每天在一起云不起水不惊的死泥潭一般的生活,我无须看到她每天像个老人一样躺在床上,无须看她像故乡的老槐树那样给我古董一样的感觉,无须看她像个老人那样慢腾腾地踽踽而行,无须看她幽幽的眼神使我胆寒心惊。或许分开一段时间,回来能缓解一下冷漠的关系。我很怀念研究生学习阶段,那时不经常在一起,回来还是蛮亲热的。
11月3日,我毫不犹豫地提着自己发表的文章和证明材料去市委组织部报了名。
1998年12月25日,昌潍大地一片清冷,麻雀寒枝跳跃叽叽喳喳,街上行人“咯吱咯吱”踩着残余的积雪,缩着脖子匆匆行走。潍坊农校培训处礼堂里,一片暖意然然,兴奋激昂。市委组织部部长都卜义,坐在主席台上,披着厚厚的风衣,带着金边眼镜,翻着一双死鱼眼,喉咙里面像长了一个癌瘤,嘴像多日找不到可吻的对象,只好紧紧地亲着话筒,慢条斯理地好不容易从喉咙吐出来再从牙缝里挤出来:
“你们是市委组织部经过层层选拔,认真考虑筛选的优秀下乡青年,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厚望,脚踏实地,认真工作,以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听着这虽慢条斯理但铿锵有力地撕裂出来的伟大动员,每个人心里有多激动啊!为了增加轰动效应,还专门安排潍坊电视台、《潍坊日报》进行现场采访和报道,在场的有几个人还专门接受了潍坊电视台的采访。
“下面,由市委组织部刘云山宣布下派人员的下派单位和职务。”主持会议的干部科科长鞠文元说。
“王增利,诸城昌城镇党委书记;
张光勇,安丘王家庄子镇镇长;
李莉,潍城区大虞河街办副主任;
李涵穹,高密市松堡镇党委副书记……”
这一去,没想到开始了我的流浪之旅。我由一开始的激动、满腔热情变成了彻底的悲哀和满腹凄凉。我指望通过此行改变我与她的关系,没想到逆向而行越走越遥远,越走越陌生,以致最后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硝烟弥漫的离婚大战;指望通过此行实现自己事业的梦想,没想到自己确实演绎不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官场现行记。我蓦地想到了爷爷的大流亡,那是在无奈之下遭受的饥寒交迫的流离之苦;而今我是在善意的谎言下,为了逃避婚姻的现实而饱受的精神饥寒之苦。我没想到,我又走上了与爷爷流亡相似的道路。
这天是1998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