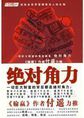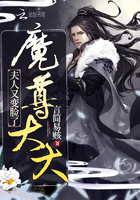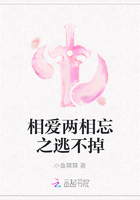一
长恨此身非我有。
我不知道,我的家乡,是否能似上海一般能容忍俞天白的《大上海沉没》一样,容忍我这部《十三行遗嘱系列·赝城》及其姐妹篇们。
我知道这很难,很难。
却也暗暗希望,我只是多虑了。
连《客家魂》三部曲那样洋溢着激情、疾呼着“高举骨头”、弘扬人间正气的呕心沥血之作,都不为人所接受。变着法子诋毁它、贬抑它,说其僭越了“民族魂”。其实,我只说了一句心里话——在《后记》中所写:“毕竟,这是我的故乡,我不希望它在经济繁荣的幌子下,掩饰着那么多封建专制、愚昧迷信、野蛮落后的负面。”
我只能说,我讲了,我拯救了我的灵魂。
这一部作品,我也同样只能说同一句话。
二
但它毕竟与《客家魂》是完全不同的作品。
《客家魂》说到底,是弘扬了一种正气,讴歌了我们民族的理性精神,是奋发向上之作,尽管其间有无数的血污、白骨与泪水!而《赝城》呢,似乎是一种绝望,一池死水,一次徒劳的挣扎,或者说,黑色的幽默、辛辣的讽喻!它一改我过去小说的套路。唯有相同之处,便是沉重。
本来,我想极力写得调侃一些、轻佻一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到了最后,我却仍坠入到那千年挥之不去,更无法逃遁的沉重之中!否则,我无法面对我的历史良知。我知道,这一来,我很可能要失去我那曾印数达到四五百万册作品所拥有的读者群,他们会骂,谭元亨这小子怎么啦,一下子变得颓废了、玩世不恭了,由理性堕入了肉欲,由诗化而沉没于世俗。当然,更会有人破口大骂,你南下回来,这里有什么对不起你这位浪子了,忘恩负义,居然对我们大放厥词,往我们脸上抹黑。没准要来个“驱逐出境”!
我不想为自己辩护,也不需要。
三
本来,90年代初,我便想把它写出来。
那是我出国讲学——讲的是中国文化史观——之前,我与一位老师,曾日夜守在年逾古稀的当年曾被姚文元点名道姓骂过的著名教授陈则光的病榻前,他曾给我写过一封手书,让我上威斯康星大学找周策纵,说他一定会对我的讲学内容感兴趣的。后来,我给周策纵打了电话,周听说陈则光病重,很是吃惊,并说陈是一位学问很高深的学者,可惜了。电话中我没敢说,住院时,这么一位大教授却只能住在普通病房,连一位处级干部都不如,一再找医院交涉,医院称,教授无法套级别上高干病房,只能这么办。而陈先生的学生,有的已是省级领导了。我能说么?一说,岂不又给家乡抹黑,给国家抹黑么?我甚至没敢上威斯康星,怕周老问长问短,把什么都问了出来。只在马里兰大学匆匆作了个讲演,便飞到了巴黎。当然,如今已有政策了,连我也都住上了高级病房,可陈则光当时却没能住上,不久,我刚从海外归来之际,他便猝然离开了人世。病榻前发生的一切,不仅仅有要上高级病房一事,还有很多,很多,如不因为出国,我当时都想写下来,写一部《大师之死》,死在一个几十人的、污秽不堪的病房中。但我终于未能写下,归国后的遭遇,各种指控、处分等等,让我疲于奔命——这个,人们亦已在《闯荡全球的无效护照》中看到了。
而这部《赝城》初衷也是写大师之死,但最后,我还是不忍写这么一段经历,我怕我的心脏承受不了。我已经九死一生了,不想把这“一生”也换成死,从而噤口。当日海外归来,未能成文的处分是“一年之内不予晋升教授”,而结果则是三年不给我申报,直到我拿到政府特殊津贴后,一年才报上去的。而陈先生三年前给我写的评审意见也成了一页废纸。在海外的周策纵是学贯中西、德高望重的大学者,其在哈佛大学出版的《五四运动史》是当代的经典名著,一生著述近百种,著作目录仅至1989年便达64页,他得到过福特、卡内基、古根汉等基金,并获得过美国科学院等众多学术奖,近日,国内出版了他与季羡林、杜维明、庞朴、任继愈等人的丛书《学苑英华》,他的一部叫《弃园文粹》。可他仍尊称陈则光先生为学兄,说陈先生造诣很高……然而,陈先生却是那样死了。
夫复何言?
记得当年反右斗争中,右派有过这么一句名言,这便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在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这话说得非常客气,却同样遭到非常不客气的对待。如今,这现象已大有改观了,至少,没谁标榜自己为“无产阶级”或自贬为“小资产阶级”了!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千古皆然。
四
《客家魂》占去了我太多的挚爱,尽管那激昂的格调,始终是我内心冲动的外化,却也消蚀了我太长的生命,它整整写了十年。在第一部问世后四年,其赝品也出来了,竟堂而皇之地称之为“开先河”之作,自然是靠金钱而买来的——有时,评论家迫于物质生活的困窘,也不得不出卖一点良知,我又能说什么呢?
正当《赝城》竣笔之际,人文社的老编审刘炜来到了广州,说起79、80年她在人文社编发的几部湖南来的长篇,其中我那部《一个年代的末叶》在艺术上较为圆熟、思想上更要深刻得多的,深为秦兆阳所赞赏,当时即可发排了的。然而,另外两部虽不那么成器,让编辑费了不少心血,却获了全国最高奖,而我那部却被扣上“整个作品的思想体系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下子给尘封了近20年。也许,历史并无什么公正可言,历史从来是趋炎附势的,为“胜利者”所写。但我聊以自慰的是,这20年我并未停笔,写下了2000万字,艺术上日臻成熟,思想也没有止步。而那两位,到了顶峰也就再没有出色的作品了,固然一个早夭,一个早到了外边当寓公去了。
不久前,我将那部长篇更名为《圣城的罪恶》,重新交给了出版社。那是写的70年代末,一个年代的末叶,“圣城”正在由天上回到了人间,那是一段历史过程的必然。
那么,这部《赝城》呢?它更该是一个世纪的末叶了。从20世纪到21世纪,“赝城”能回复到真城,返朴归真么?
赝城也是一段历史过程的必然。
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五
永远对现实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恐怕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通病”,而我大概也是无可救药了。
20年,有大踏步的高歌猛进,也有踌躇的原地踏步——但愿是“退一步,进两步”的前奏,人们总是抱有这种善良的期待。世纪初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竟成了谶语,物质生活进化了,精神生活却未见得同步。《赝城》中亦是如此,许副市长的振振有词与小女子张慧仪的自信,无非就是一种“家国同构”——在这点上,我们究竟前进了多少呢?20年后能否得以问世的《圣城的罪恶》,其批判的锋芒仍是那么锋利,不曾过时,这不是我的幸运,而是大的不幸!
“圣城”本应早就消逝了!
而“圣城”未去,“赝城”又来了,中国人又怎么啦?
中国人的时间太不值钱了!
中国的精神史也太苍白了!
“把真品变成赝品,这是最典型的东方思维方式。”这是一位著名的国际文物保护专家在参观了我国一个著名的古墓博物馆时所说的。
这不是政治,仅仅是文化。
六
以上这些,都是这本书之外的话了,该说说这本书了。
在这之前,如果包括儿童长篇小说在内,我已经出版与发表了超过20部的长篇小说了,但我并不标榜它这是第二十几部。但至少,前边有十来部,如今仍在再版,有的一印再印,未曾与时俱逝。人们常常喜欢指责谁谁谁写得太多了,但近日,巴金老人却不这么认为,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比起国外的作家来说,中国作家不是写得太多而是写得太少了。人家绝对不会有吃“皇粮”的作家。至少,我敢说,我的每一部长篇,都是倾注了我的全部心血的,绝不是游戏之作,应景之作,只举几部书名便可知了,如一再重版的知青《女性三部曲》,《潘汉年》及其《潘氏三兄弟》系列纪实长篇、《客家魂》的三部曲,还有我真正的长篇处女作《圣城》及这部《赝城》,没有哪一部,在写作中我不曾流过泪,在写作后不曾大病一场,乃至住进医院。而这一部,我更是换了一种笔法,寻找新的表现方式,也就是说,不再重复已有的自我,力图有新的突破,甚至不惜失去我曾有过的读者。
“长恨此身非我有”——这是中国文人几千年的慨叹。但愿今天能少一点这样的慨叹!
我绝不后悔写下这样一部作品,在人类重重苦难中作为苟延残喘的文学,毕竟是相对于物质压迫之下的精神之花,总有它开放的理由!
我将开始我又一轮的精神行程——当然,不应再是一种循环!
谨将此书,奉献于我的恩师陈则光先生的灵前!
这是已迟到了两千个日夜的祭奠。
谭元亨
1998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