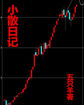郝卫宁
我爱死梅花了,但长这么大,竟没见过梅花。
我之爱梅大概是在十岁左右的时候。其实,我生长在一个没有梅树的城市,根本没见过梅花,而且,确切地说,除了喇叭花和月季花,其他的花我都见得少。那个时候,国家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政治时期,“花可熟观,鸟可倾听,山川云物之胜可以纵游”的“资产阶级”情调为广大的“无产阶级”所不屑,而且就连人们的服饰都少有花样鲜艳的颜色。我虽然正值花蕾的年龄,却偏偏“不爱红妆爱武装”,不想着含苞欲放,老想着舞刀弄枪。当然就想不到那见都没见过的梅花。忽然有一天,听到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读了毛主席的一首词《卜算子?咏梅》。呀!我所敬爱的毛主席原来如此地喜爱梅花啊!梅花能够“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真是高洁之品、人间奇绝呢。于是,一半是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敬意,一半是存着对遥远的既不可望又不可及的“丛中笑”的好奇,梅花,走进了我的心里。
这一走进,竟是二十多年。
因为爱梅,做过很多“可笑”的事。
在我十二岁那年的春节前,跟母亲去商场买布料做新年的衣服。这之前,每年的新衣服我是从不选花布的。而这次,我选中了一种白底印有淡粉色花的布料,因为那花儿看起来非常像我想象中的梅花。这件“梅花”衣服成了我最喜欢的,一直穿到小得不能再穿了,我就把衣服上的领子拆了下来,歪歪扭扭地在上面缝上了摁扣,又把其他衣服的领子上也缝上摁扣,这样,穿每件衣服时我就可以把那“梅花”领子摁在上面翻出来,我觉得真是又好看又与众不同啊!同学们说我真臭美!母亲说这像什么呀,领子和领子不一样大,长短不齐的。我心里想,臭美有什么!不一样大有什么!不一样齐有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犹有花枝俏”的味道吗?直到现在,我的这个著名的“梅花”领子的故事依然是母亲的笑谈。
我一位同学的父亲是个画家。曾有一阵子,我天天缠着她的父亲要学画梅花。人家说这里没有梅花,你没见过,不好画的。我说,龙你见过吗,不照样画!屈原你见过吗,不照样画!于是,人家就不好再说什么,只好捺着性子,抽着空教我画梅。他教我的是宋朝杨无咎的墨梅画法,他说杨无咎一生坎坷,终生寻梅、观梅、画梅,他的墨梅在线条上更有书法的笔意和梅的风骨。画家的话我似懂非懂,我画的梅也多是“有墨无梅”。画家说梅花傲霜斗雪,高洁雅淡,你心中要有梅,才能画好。我说我们这个城市没有梅,观察不到,心中怎么能有梅!他就沉默了。有时候,他会在他画得比较满意的画儿上写一两句古代赞梅的诗,比如“一树寒梅白玉条”“尚余孤瘦雪霜姿”“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然后,指着画儿说,画梅的枝干要像写隶篆,在顿挫中见笔力;画梅梢和花朵要像写行草,在曲直中见韵致。
那是一些淡淡的、清幽的日子。画家潇洒泼墨,笔下的梅花从蓓蕾、小蕊、大蕊到欲开、大开、烂漫、欲谢、就实,各种形态鲜鲜活活,冲淡了外面世事的喧闹。后来,我的“墨梅”一直没画好,这个同学已经举家南迁了。很长时间以后,同学还记得画梅的事,来信安慰我说没见过梅花,当然就画不好了。还说有梅花的南方哪儿都好,就是梅雨季节很烦人,东西都是潮湿的。看了她的信,我记住了四个字,梅雨季节!我想象得出雪中梅,却想象不出雨中梅,“和风和雨点苔纹,漠漠残香静里闻”,那该是多有韵味的季节啊!后来,我对人宣称,我最爱画的是“墨梅”,最喜欢的季节是“梅雨季节”。同学们笑我,梅雨与梅有关系吗?瞎联系让人笑掉大牙啊。又说,不知道你的人还以为这是一个多有品味的人,知道你的人知道你画的“墨梅”是有“墨”无“梅”,而且连与梅没有任何关系的“梅雨季节”都从来没有“享受”过。我不管,谁爱笑就笑去,反正都有个“梅”字不是。
我真傻,少不更事,太把“丛中笑”的梅花当回事了。街坊阿姨一天告诉父亲说,她女儿出阁,商店有处理的被面,但她没买,便宜倒是便宜,而且上头印满了梅花,可是啊,怎么看怎么都让人想起七个字:“冻死苍蝇未足奇”!梅花吉祥,我也不敢买啊!及至我登台扮演李铁梅,哭诉“听奶奶讲红灯”,好像梅花附了身,而父亲快要被“冻死”、梅花自个笑出一场“悬崖百丈冰”的时候,我像是一铁锤砸下来脑袋给打蒙了。
看不见闻不到爱不起恨不得的梅啊。
当我结婚生子时,父亲已经沧海桑田,却气定神闲地对我说,要是生个女儿,就起名“雪梅”吧。
阳光斜射进来,洒在父亲的脸上,也洒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味道。窗外的雪融化着,滴滴答答,时缓时急,敲在心上。
生的是儿子,与梅无缘。
丈夫的表姐梅英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一所大学教授中文。一天打电话来说她的美国学生在上课时问到了她名字的中文含义,她说是梅的婴儿——她在闪念之间把“梅英”改作了“梅婴”。她让我帮她找些有关梅花的中国古诗词之类,她说她忽然意识到也许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介绍中国文化的突破口。我答应了她。我很想再走近梅。
我狂翻了所有有关梅花的书籍。
在自然界存在的大约25万种花朵中,梅花最为中国人所喜爱。因为她产自中国,耐寒、耐旱、耐瘠薄,冬季开花。李笠翁在他的《闲情偶寄》中称“花之最先者梅”,“千红万紫,终让梅花为魁”。刘海粟放声大呼:“我爱梅花,不爱昙花!”前人留下的诗词歌赋、音律古画,有赞叹梅花不畏严寒的坚强性格的;有以梅花的高洁雅淡、清丽超逸、潇洒绝尘自喻的;有借素朴淡雅的梅花表达自己轻视功名利禄的;还有一波三折、让人听之荡气回肠的古曲《梅花三弄》;有行云流水、活而不乱的拳术“梅花桩”……当朔风凛冽、冰雪皑皑之际,唯独梅花昂然枝头对于生命充满希望和自信,教人精神为之一振。梅花珍惜早的消息、保持晚的气节,永远俏丽、永远欢笑,正是这种冷绝群芳的特性,使她成为审美的极致、人格的象征。
我告诉梅英,“梅文化”中的人文色彩和“仙”风“道”骨,深深震撼了我,一句话说完:“人间奇绝,只有梅花枝上雪”!用梅花雪化成的水沏茶,也堪称一绝。《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怡红院劫遇母蝗虫”中说妙玉用梅花雪水沏的上等茶,非常珍稀,“宝玉细细吃了,果觉轻淳无比,赏赞不绝。”而那不俗的黛玉竟没能品出梅花雪水,以为是“旧年蠲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清淳,如何吃得!”
好生了得!
书海“寻梅”,又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遗憾没见到真正的梅花。寻梅不见梅,心里非常难过。
后来,一次出差到坝上,听人说附近有一片干枝梅林。我喜爱的、我想念的、几乎“寻”遍了所有描绘她的笔墨丹青并支撑我度过艰难成长岁月的梅花,竟会在如此不经意间出现在我面前,我又惊又喜,几乎是狂奔着到了干枝梅林。我发现她很矮,只有膝盖高,枝干很细;花儿只有黄豆大小,味道却很浓,说不上是一种香还是其他什么味儿。看管“梅林”的人说干枝梅可以随便采。我问他怎样采。他说整棵地拔出来就行,一棵五元钱。我说拔出来会不会死掉?他说不会,枝干了而花儿不死不掉,要不干吗叫她干枝梅呢。尽管我很怀疑这夏末秋初开花的干枝梅与心中那迎风傲雪的“岁寒之友”之间的关联,也很怀疑这五元一棵带有了某些“商品”色彩的干枝梅与心中那高洁淡雅的“君子之花”之间的异同,但她毕竟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接触到的最接近梅花的“梅”呀!我采了一大棵,捧了十多个小时回到家。为她找了一个漂亮的花篮,放在客厅最醒目的位置。然后,不顾家人的牢骚任由她那称不上是香味儿的味儿好几个月地弥漫着整间屋子,任由她枝干花枯后一点一点扑扑落落地掉下,迟迟不肯把她扔掉。后来,一位朋友说那根本就不是梅花,也不是正宗的干枝梅。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真梅到底在哪儿?我问自己。古往今来,骚人墨客以梅言志,咏梅、画梅、唱梅、赞梅,梅的风骨、气节和韵味远远超出了她的本身。我想,或许见梅者未必识梅,或许识梅者未必见梅。画家的梅花,“梅婴”的梅花,带给我许许多多有“梅”陪伴的日子,使我孤寂中有了希望;身本洁来还洁去,叫我浮躁中有了恬淡。难道这就是“心中有梅”的含义?梅花本无形,寻梅之于我,恐怕是今生一世的精神之旅了。
(选自2007年第1期《文化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