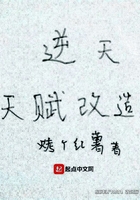金秋的阳光穿过斑驳的树叶,在他那张俊朗的脸上摇曳着、闪烁着,他双手拿着琴谱,但此刻眼睛却微闭着,和刚才的我一样,正在享受阳光,正在温暖的阳光中小憩。
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绕到他的背后,左手按住和弦,右手在琴弦上拨下去,哗啦啦,吉他一阵乱响,惊醒了麦迪。
他失神地看着我,我立即向他展现出一个灿烂的调皮的微笑。他皱着眉头,像在半梦半醒之间,伸出拿琴谱的右手,在我面前晃了晃,像看不见,又像不敢相信。我心里的酸涩突然要涌上来,我连忙向右看,向上看,拼命地要把眼泪忍回去。
这场姐弟恋,我只能在他面前扮一个性感妩媚、风情万种的小姐姐。
终于,麦迪拉住我的手,要我在他身边坐下来。我看着他,问了我想问的所有问题。
其实,故事很简单。
我病倒的第二天晚上,麦迪也病倒了,急性阑尾炎,他连我的医药费都拿不出来,还能找我要钱?黑桃告诉了小苏,小苏的爸爸妈妈当晚赶过来,支付了所有医药费……
“你们……在一起了?”我偏着头,要多妩媚有多妩媚地问他——我只是想掩饰自己心里的痛,那一副衣服演奏出的恩爱图,再一次地在我的脑海里放映。
“是的。”我看不出麦迪是轻松还是沉重,他低着头回答我,尔后又看着我的眼睛问,“你会瞧不起我吗?”
想了好久,我终于说出“没有”两个字。
“我只是觉得……你卖得太便宜了,为什么不卖给我?”
麦迪并没有生气,只是淡然一笑:“我觉得这个你,比和我在一起的那个你,真实得多。”
“你爱哪个?”他话音未落,我就扬起眉毛问。
“我还能爱你吗?”他看着我的眼睛。
“你是说……?”我有点不明白,“正在失恋期……不过,我要重新考虑一下。”
麦迪抿了一下嘴唇,仿佛咬了一下牙齿,伸过双臂来,紧紧地把我抱住。
“那……小苏呢?”我不得不问这个我不想问的问题。
当我问完这句,睁开眼,就看到小苏站在麦迪背后不远处的阳光下,瞪着眼睛看着我们。我愣在那里,麦迪察觉出异样,转过身来。
小苏手里的琴谱无力地垂下来,她看着我们,眼里的心痛无以言表。
“小苏……”麦迪站起来,想朝她走过去。
“不!”小苏歇斯底里地大叫一声,扔下琴谱就跑。
这个小广场四周都是马路,而且车行速度不慢。“小苏,你听我说……”麦迪连忙追过去,想把她拉住,可小苏白色的风衣一眨眼就卷入到车流中了,听见汽车叫嚣着刹车的声音,我尖叫着闭上了眼睛……我害怕看见那残忍恐怖的一幕……
“你妈的!找死啊!”一声粗壮的汉骂告诉我并没有出什么事。
我缓缓睁开眼睛。
“对不起!对不起!”麦迪拉着小苏,一边道歉一边把她往路边拉,小苏一边挣扎,一边用粉拳在麦迪背上一阵乱打。麦迪把两只拳头捉住,腾出一只手来揽着她的腰,把她往路边推。
我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我会去找你的,你等着我!”麦迪的这句话大概是对我说的。我睁开眼睛,看着他拥着小苏消失在拥挤的人潮里。
大武汉人真多,一个人湮没在人潮里,就像冒了一个泡泡,很快消失了,连影都没有一个。
他会来找我吗?
三十一、那盆仙人球
给桑家榆买的烟灰缸,给我自己派上了用场,每天咖啡馆打烊后,我就斜靠在窗前的沙发上抽烟,有时候点一支蜡烛,有时候忘了点。窗外的苹果树结了几个细小的果子,我本想留着等桑家榆来了一起去摘,可是等着等着,他一直没来,被上学路过的淘气小孩摘走了。
听说抽烟会让人衰老,听说酗酒会让人衰老,听说伤心会让人衰老,为什么痛楚的女人就要老得很快?为什么老天爷要把什么都留给幸福的女人?她们已经得到了幸福,还有什么必要留住青春的容颜?
我斜躺在沙发上,左手捏着那枚银色的打火机,右手像桑家榆一样弹着烟灰,袅袅烟火向上飘,燎着我的手。短短几天,我的手指就被熏得焦黄,放在鼻前嗅一嗅,有几分他的味道。
我不上网,也不开手机,我想,就这样算了吧,就这样让世界把我遗弃了吧。
可是,可是,我还有一盆仙人球在他那里。我想把那盆仙人球拿回来。
那盆仙人球有怎样的故事?
那盆仙人球是我们的孩子。
是的,是我们的孩子。
大四那年的那个樱花之夜,有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我的身体里发芽了,这是一件多么美好、多么幸福的事情。我带着惊喜和甜蜜去回味那份交融,体会身体里每一分小小的变化。这是一种真正的融合。
我怀着战栗的心情要去把他结束。尽管结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然而为了桑家榆,我不得不这么做。如果是为了他而牺牲,于我,那也是一种幸福。
我一个人去的校外的小医院,一个人躺在洁白的病床上,冰冷的器械伸进去……我好疼好疼,那时我就知道,原来爱一个人要这么疼,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就要这么疼。
剧痛一阵阵袭来,连让我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我好想把自己的身体摈弃,旁边的小护士可怜我,来抓住我的手。我抓住生还的机会似的,抓住她同样冰凉的小手。我好痛好痛,指甲深深地掐到她的皮肤深处,她咬着没有血色的嘴唇一声不吭……
最后胚胎取出来了,那个可怜的小生命只有半个鸡蛋那么大,我向医生苦苦哀求,将那个小生命的碎片带走了。
那个小护士帮我找来医用塑料袋,我一层一层地把他包裹着,一直焐在手心里,我想用我同样冰凉的手掌温暖着他。然而他和我身体里的血液一样,彻底变凉了,再也回不去了。
我害怕失去他,害怕他会消失,害怕他失去我会害怕。
等我的身体恢复一点力气的时候,我买来一盆仙人球,听说仙人球嗜血,而且生命力很强,我把他埋在了花盆里。
我想,这样他就不会消失,不会离开我了。
等我的身体渐渐能够正常活动的时候,我把那盆仙人球送给了桑家榆,我央求他无论如何不要抛弃它,他答应了,而且,他也做到了。
难道现在他却要抛弃我吗?
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那只穿着黑色丝袜和红色皮鞋的性感的腿。
我问自己:如果他回来找你,向你解释了一切,而且那解释是真的,不牵强不附会,真实可信,你打算就这样下去吗?你确定自己能忍受这种日子?
这问话,我已分不清是自己还是丁霁心的。我知道这种日子是和大多数人所不同的,并被大多数人所反对的,因此我要受大多数人无需受的苦,受大多数人不能忍受的痛。
一种被啃噬一样的疼痛将我拉回现实,手指间夹着的香烟烫到了食指。我一松手,烟蒂掉到了地板上,我连忙坐起来踩灭了它。
门外车灯一闪,一个瘦削的男人从车上下来,推开了咖啡馆的门。
我曾说过,这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是良善之人,因为他们都有一颗人心。
是的,是桑家榆来了。
三十二、芳香之旅
是的,桑家榆来找我了。
这世界上有多少事情我们能知道真相?因此,我再一次地选择了缄默,我没有去问他,没有去问他那双黑丝袜、那双红皮鞋。除了他亲口承认那之间的关系,我又能相信什么巧合、什么解释呢?所以,不如不问。
咖啡馆的夜晚静谧而温柔,一如他的亲吻和爱抚。他手指上的淡淡烟草味道,一如既往,那是迷情剂。
“你想去我的家乡看看吗?”他斜躺在苹果树下的沙发上,吐了一口香烟,问我,“——我长大的地方?”
幸福似乎来得有点突然,我睁大了眼睛看着他。
“我的生活周围,那是一道道密实的藩篱,我没有办法把你带进来,你愿意去我长大的地方看看吗?”他总能听到我心里的声音。
“我……愿意。”我咬紧嘴唇,蹙着眉头,不让不争气的眼泪流出来。
星期六的早上,他开车带我去了他的家乡,我们先经贺胜桥至咸宁,然后继续南行。尽管同属湖北境内,但风物已有些不同。道路两旁零星有些黑瓦白墙的房子,门楣上都用黑漆大字写着些:颍川次第、山阴次第什么的。我好奇地打量这一切,想象着小小的桑家榆背一捆柴行走在山路上——我多想认识那时候的他!
接近正午时分,我们到达一座大山脚下,那是一个翠竹满山的地方,高大的毛竹把山岭装饰得青翠欲滴,一阵山风拂过,竹尖点点头,弯下腰,发出悦耳的沙沙声。只是山下的房屋更见矮小破旧。黑色的屋脊中间被压弯下去,两头微微翘起,正厅只在大门两侧上方开了很小的窗户,可以望见黑漆漆的厅堂。门口歪歪斜斜铺着石阶,青石板已经被踩得乌黑发亮,看上去都不像人能住的房子,可大门却洞开着。
桑家榆见我瞪着眼睛好奇地看着窗外,一边停车,一边说:
“这就是我的家乡,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他把车停在池塘边的竹林里,牵着我往山坡上走,山坡上只有一户人家,门锁着,看上去已经很久很久没住人了。
走到门前站定,他掏出钥匙来,“咔”的一声,很轻松地就将门打开了。推开吱呀叫唤着的木门,里面竟然干净得像刚刚打扫过的。我再次睁大眼睛看着他。他不看我,自顾自地说:
“邀请你来之前我叫人打扫了的。”
我握着他的手用了用力,他感觉到了,偏过头来,看着我,然后轻轻把我抱了起来,放到神龛前的八仙桌上坐定。
“你知不知道?小屁孩是不能坐桌子的啊?”
我知道他在使坏,说:“我知道,你放我下来啊。”
他却偏偏不让。我拗不过他,只得看着他。
他盯着我的眼睛说:
“没拜过堂的媳妇,那就坐坐桌子吧。”
我眼里有泪要滑落,扭过身去看神龛,上面香炉和蜡烛都有,我回过头来,伏在他的肩头,不禁要哭出来。
“好了,”桑家榆却把我抱下来,“小屁孩桌子坐够了没有?怕不怕大人打?”
待我将眼泪忍了回去,他又问:“主妇大人,我们现在吃什么啊?”
我这才破涕为笑,伸手将他打了一下:“我初来乍到,什么也不熟悉,你叫我怎么办啊?”
“唉,看来还是要我出马了……”桑家榆少有地开起玩笑来。
不一会儿,果然有一个当地人打扮的妇女送了一竹篮吃的过来,揭开来看,有两大碗青菜,两大碗米饭,还有一小罐鸡汤。
桑家榆把竹篮提到门外的竹林边。他家老屋门前有一片很大的空地,他告诉我这以前是做稻场的,上面可以给稻谷脱粒,还可以晒东西,以前的花生、红薯干什么的,都要在上面晾晒。
空地四周都是毛竹,毛竹生得密密匝匝的,钻进林子几步就看不见人了。桑家榆在前面带路,钻进竹林后向高处走,他绕到他家的后门,这个小土坡上除了有高大的竹子,在竹林的下面还一丛一丛地生着茂密的野菊花,此刻正星星点点地开得灿烂。
桑家榆把盖篮子的布揭开,铺在一片野菊花旁,把篮子里的饭菜一碗一碗地拿出来。然后脱下自己的外套,让我坐在上面。
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天,他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讲他小时候怎样爬树、怎样摸鱼、怎样当孩子王……他问我鸡汤好喝吗?他告诉我,他家里没人了,只有一个嫁得很远的姐姐……
当太阳爬过房顶的时候,他摘了一束野菊花递到我鼻子底下。
“香吗?”他问。
“香。”
“很多人不习惯这种香味……有点苦……”他站起身子,走过来,松软的杂草在他脚下发出轻轻的呻吟,“只有我们这种山村长大的孩子才喜欢。”
我想说:我知道你无所傍依,我知道你的每一步都是自己艰辛地走出来的……可是我什么都没有说,我明白他明白,那么就失去了用言语表达的必要。
他坐到我背后,环住我的腰,把我的头别过来,一下一下温柔地吻我……
我们在野菊花丛中睡了整整一个下午,醒来时我的头发上、皮肤上满是野菊花的香味。
傍晚时分,我们步行很久去小镇上喝酒,直喝到两个人都要大醉,然后又去小镇旁的湖边赏月。看月亮从云层中涌现出来,升到正中天。桑家榆突然诗兴大发,接二连三地背起诗来,我坐在草地上仰头看着他。接连背了几首长诗,他还不尽兴,要去街上找毛笔宣纸来写字。
我跟着他疯闹,一家家的去敲小店的门,小镇上没有找到卖生宣的店子,他看到前面有一处灯火通明的地方,我们又继续向前走。一路上,他都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我真希望这条路永远没有尽头,他陪着我走到黎明、走到天光四亮、走到一个花香满径的地方,我们彼此只拥有对方,除了对方,什么都没有。
等我们疯跑过去,那里竟然是一个蔬菜批发市场,一眼望不到头的瘦街上,全是菜农和绿油油的青菜。农民们披星戴月推着一车车的蔬菜赶到这里,在路边将一筐筐的菜码好,等待着买家,他们忙碌着,仿佛此时不是午夜,而是叶上初阳的早晨。
莴苣削得整整齐齐,码得很高,小白菜在直径一米的大铁丝筐里菜帮子朝外围成一个圆,像一个大菠萝。菠菜、茼蒿、芹菜都水灵灵的,碧绿的叶子在灯光下闪动着诱人的色泽。
“买点菜吧?”我们俩异口同声地问对方,说完,因为这不约而同,都会心地大笑了。
才花了五块钱,就把我们一天要吃的菜买够了,桑家榆付了钱,从我手里拿过菜提着,然后依然腾出一只手把我牵着。
柴米油盐酱醋茶,原来一粥一饭也可以这么诗意——是因为他、因为爱才如此,还是因为稀有才如此?
红烛过半,夜已深沉,我从他温暖的怀抱中挣脱,在他家厅堂的八仙桌上,借着红烛的微光,给他写下了我平生的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情书。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旅程,可惜一切就要结束了,我还是不得不离开他。
纵使去过他的老家,“见”过他的父母,纵使给他做过一日三餐粥饭,我还是不得不离开他——还有什么日子能比这个更亲密、更美好的?
我们都有一颗自由奔放的心灵,可世界总有高高在上的规则。规则给我们划定了一个安全的区域,我在区域之外。我太爱,太痛,所以只能放下。
亲爱的他不知道我作出这个决定需要多大的勇气,我爱他,就已用尽我最大的力量。离开,更是用尽了所有力气。
还有多少未完的故事?还有多少未了的心愿?亲爱的,这一粥一饭的恩情,你何时还我?
我们曾相约着明年七月去庐山消夏,相约着冬天去海南度假,相约着要在天边种一棵菩提,然后看它慢慢长大,相约着去看西夏的老宅子、昆仑的落日……我们曾相约着给我一个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他的生日……我们曾相约着……有那么多的约定,都没有来得及实现。
我知道,即使我给他时间,我继续等待,也等不来这一切,等来的除了他的愧疚、我的怨怼,还有什么?有太多无能为力、有太多身不由己……有太多的不可预知……他给了我一个关机的四十八小时,已经够了。
他驱车离开的时候,路过我们赏月的小镇,我看见一支绿色的邮筒立在路边,我松开他牵着的手,将那封信投入了邮筒。
他问我:
“寄的什么?”
“一封情书。”我回答,“给我最爱的人。希望他小心查收。”
他淡淡地一笑。
这朵微笑烙在了我的心底。
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