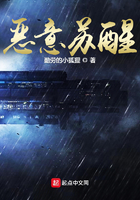可良宝看到齿棣的表情不一样了,他的脖子和左右手各动了一下,仿佛肌肉酸了,他吞了口唾沫,伸出舌头来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嘴唇蠕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而又说不出来。他看着丝雨,在丝雨的脸上搜寻着。可丝雨茫然不解,她见这个凶狠的伯伯盯着自己看,又害怕又紧张,把头低下去,可又不由自主地要仰起来,仰着满脸泪痕的头,向齿棣央求道:“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杀我妈妈!”
齿棣的嘴唇又动了一下,小眼睛里闪出点点亮光,野蛮的目光在一瞬间消失,他仿佛害怕了,在懦弱地寻找退路。
“快叫——”一个念头闪过良宝的脑海。
“不!不行!”尹三大叫一声,打断了良宝的话,她的脸痛苦地扭曲着,声音马上又变成低低的哀求,“丝雨会记事了……”显然,良宝那一刹那的念头,尹三懂了。不,不能,不能让丝雨叫他爸爸,不能让丝雨知道,她有一个这样的爸爸。
丝雨含着眼泪的眼睛看看良宝,又看看尹三,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只听到良宝让他喊,喊什么她不知道,难道是宝伯伯说我求这位伯伯的时候没有喊他吗?就像妈妈平时教导的,要喊人,嘴巴要甜。想到这里,丝雨怯怯地喊了一声:“伯伯!”
齿棣再也憋不住了,喉咙里一声怪叫,小眼睛一闭,咧开嘴大哭起来,随之,他捏刀的右手也垂了下来。良宝连忙把头向左边一偏,示意尹三闪开,与此同时,他两步绕到齿棣背后,飞起一脚猛向他后背踢去,齿棣一个趔趄,打翻了门口的摊子,扑倒在泥地里。
这一声巨响,才挤进了人们被各种吆喝和讨价还价声塞住了的耳膜,这才在喧闹的菜场中产生了一点反应。人们手上还拿着自己挑选的东西,奇怪地扭过头来,看到尹三的摊子泼了,红枣花生莲子滚了一地的,一个男人扑在地上,双手捶地,嚎啕大哭。
十四
有人报警了,警察又把齿棣带走了。他们没想到,这个顽固的家伙不听教训,不回家过春节,又跑来捣乱。
这回,他不像上次那样强硬了,他喊着嚷着求尹三救救他,他保证再也不来闹了,他还说,他一直以为她把女儿丢了,现在……就不会再来闹了……尹三扭过头去不看他,一把紧紧地抱着丝雨,丝雨的小脸挨着她的脸,冰凉冰凉,一脸泪痕。
两个孩子都吓傻了,完全不做声。尹三一手抱着丝雨,一手牵着宝儿,跟着良宝去医院缝针。针缝完了,要输液。输液观察室里就他们三个人,吊在天花板下的电视专为他们播放着,没有人看,声音却出奇的清晰。
吊瓶里的盐水一滴一滴的顺着输液管往下滴,这沉默让尹三的心吃紧。
“你,打算怎么办?”良宝在暖气充足的输液室里昏昏欲睡,他强打起精神,问尹三。
能怎么办?还能打算怎么办?我只能祈求老天爷发发慈悲,可怜可怜我,让齿棣回去,让我们娘俩能把这日子往下过过去。不敢想,不敢想以后。尹三看了一眼丝雨,孩子眼泪还未干,睡着了,可睡得又不踏实,不时在梦中哼哼。
“这孩子,大概是吓着了。”尹三答非所问,“先把年过过去了,再说吧。”
又过了两天,傍晚时分,尹三正准备收摊,齿棣又来了。他的案子不好定性,警察们又把他放了,劝他好好回去过年,可他不听。他提着半挂香蕉,四个苹果,找到尹三,说是给丝雨买的。
他央求尹三跟他一起回去,他说:“你跟我一起回去吧,我保证再也不打你了。为了买你,家里已经把积蓄用光了,还借了不少钱……你这一跑,庄稼也荒了……鸡鸭也没人喂了,羊也死得只剩两只了……”
良宝扬了扬拳头,把齿棣打发走了。
晚上,躺在杂货铺后面的床上,尹三翻来覆去睡不着,思绪不由自主地又回到了那莽莽群山之中的小村庄……
被捆着,被麻袋装着,不知过了几天几夜,汽车、拖拉机、牛车,不知翻了多少个山头,等尹三重见光明的时候,已是在一个大山脚下。她还被捆着,嘴巴被塞着,跪在地上,扭头朝四周一望,只看见四面高山上露出的一角天空……那山真高,真大,怕是跑几天几夜也跑不出来。
过几天,他们以为她已经被打怕了,让她下地劳动……地在半山腰,可半山腰依然看不出自己身在何方,除了山,还是山。
穿布衣,有绣花图样的布衣,过廊桥,可以遮风挡雨有墙有瓦的廊桥,住的是吊脚楼,紫树建的三层木楼……人家唱山歌,尹三唱不得,一听,就眼泪直流……就算是青山绿水,那也不是自己的家啊!何况,自己的家乡在千山万水之外。更何况,晚上睡在身边的,还有齿棣啊。
他,也有过好的时候。刚成婚,她身上的淤青褪了,下地干活,他也温和地教过她。第一次呕吐,他以为她有了孩子,就会安心跟他过日子,他也面带喜色,把好吃的留给她。
那次他用冲担把她的小腿杀得发炎了,她昏迷着,他采草药给她敷伤口,一整晚一整晚地不合眼,一睁眼,看到的第一张脸是他糊满眵目糊的双眼。后来她生丝雨,不能下床,他给她端洗脚水,婆婆骂:畜牲不能惯!他低着头,不理她,还是一盆盆的清水端进来,一盆盆的脏水端出去……
他求她回去,他说他会对丝雨好的,不会再逼着她生儿子的……村子里修了水库,庄稼好种了……要跟他回去吗?尹三想。生了女儿要生儿子,多半也是婆婆的意思,他是个孝子,自然会听他妈的。他打她,虽然打得厉害,可也是自己性子烈,多少像她这样的女人,被活活打死了。关键是,他才是丝雨的爹,真正的爹,有血缘关系的亲爹……
不,不行!千辛万苦逃了出来,吃了多少苦头?好不容易回到爹娘身边,好不容易带着丝雨逃出了那一座座的大山,怎能再回去?尹三连忙翻了个身,掐断了自己的念头。再咬咬牙吧,再苦些,再累些,总有熬出头的那一天。自己若是再回去了,就怕没勇气和力气再跑出来了。
十五
但可怕的是,齿棣不走了。他找了家十块钱一晚的旅社,住下来不走了,每天在三街菜场附近转悠。丝雨的梦魇还没有醒,每天迷迷瞪瞪的,尹三真怕他再吓着了孩子。
一个下午,尹见尹舞来接尹三和丝雨回白鹭冲。
“丝雨,回外婆家过年,好不好?”尹舞给丝雨买了新衣服新鞋子,又逗她,孩子脸上才有了点血色。
“过年?好!”丝雨笑了。其实长到这么大,她还没有过过一个像样的春节。尹三心里涌起了涩涩的酸楚。
尹见说:“姐,这世上的钱,总是赚不尽的。”尹三笑了笑,点了点头,让尹见帮着把摊子收了。回白鹭冲过年,对尹三来说,也是一件大事。
见尹三在收摊子,良宝脱了蓝大褂,又在上面郑重其事地揩了把手,走过来,看着尹三和弟弟,说:“尹三,你等一等,我有话跟你说。”
尹三抱着搁东西的门板,站着,看着他。他又低了头,踌躇着不能开口。尹见见状,低了头要走开。良宝又一把拽住他,说:“尹见在这里也好。”可他还是半天开不了口。尹舞见了,就抱了丝雨去后面,只听良宝低了声音在说,“尹三……我一直想说,可不知如何开口……”
尹三轻轻地把门板放在了角落里。
“可这再要是不说,这就拖到明年了。我知道,我大你很多……我还……”
菜场所有的喧嚣在这一刻安静下来,在良宝身边挤来挤去的买菜人也不复存在,尹三的头一下大了,身子似乎又轻了,似乎一片羽毛落到了手掌心,又像挑着的千斤重担被另一个肩膀担了过去。
原来自己,已经这么累了。
可尹三走神了。愣住了。
这沉默,在尹三的小铺子里回旋,在三街菜场回旋,在欲雪的昏黄的天空回旋。
良宝还站着,看着尹三,等待着答案。
下雪了,洁白的雪花从灰暗的天空飞旋而下,一朵一朵,密集而飞快。这将是一场畅快的大雪。尹三的眼神由下而上,盯着飞舞的雪花出了神。
尹见打破了沉默,他替尹三回答了:“良宝哥,这么大的事,让我姐考虑一下吧。”
十六
“下雪了!下雪了!”所有的小孩子都在嚷,丝雨也在嚷。
尹见背着丝雨在前面走,尹舞和尹三在后面跟着。尹舞挽着尹三的胳膊,把头靠在尹三肩上,跟尹三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可尹三却没听她的,她看见了齿棣。
在斜对面的公汽站台,齿棣背着一个大蛇皮袋,正盯着一个小孩手中的牛奶瓶。他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已经冻得瑟瑟发抖,背上背着的大概是他捡到的饮料瓶,袋子湿了,把他的衣服也打湿了一大块,可他全然不觉,只顾全神贯注地盯着小孩手中的瓶子。齿棣胡子拉渣,浑身上下又脏兮兮的,把小孩吓着了,小孩的妈妈瞪了他一眼,把孩子换到了另一边,他被挡在了身后。——他刚来到城市,他并不知道,那种饮料瓶是不能卖钱的。
尹三看了一眼,连忙把头低下去了,她生怕齿棣发现了他们,那将又是一场劫难。可她心里,是难过的。这隐隐地难过,不知从何而来,却大大地搅乱了她的心。
尹舞却说:“三姐,你看!”
尹三小心翼翼地抬起头,顺着尹舞的手指,看见了行道两旁的法国梧桐树。
那树也小心翼翼地生长得好艰难,五六个枝桠都被锯断了,只剩下碗口大个疤,寥落的枝叶在寒风中颤抖着,有一片被吹落了,蜷缩着跌到尹三的脚下。
原来冬天,才能看见一棵树的真实生存状况。
“我读到大学后,才明白有些人的人生,是被规划好的。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上哪所幼儿园,读哪所小学,几年后报考什么中学,进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大学还没读,工作就定下来了。而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就像山里的山泉,没有计划,我们就冒了出来,汩汩往外流,遇到石块,我们就绕道,哪里地势低,哪里容易,我们就往哪里流,要么流进小溪,要么无声无息地干涸……
“又像这城里的行道树……一棵树,长得好好的,遮住了门面,要锯掉一截。缠住了电线,要锯掉一截。就是长得太茂盛,到了冬天,园林部门也要锯掉一截——也许不是一截,而是整个杪子……”
尹舞微笑着看了一眼担心的尹三,又接着缓缓说道:“可是,姐,你看,这棵树,不还是长得好好的么?就算锯掉它所有的枝桠,那又怎么样呢?到了春天,它不还是会抽出细嫩的枝桠,在阳光雨露下努力地长得强大?你看,这直直地向上长的枝桠,不是一直长到了五楼,长得好好的么?”
“三姐,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地、向着有阳光的地方生长……”
尹三的耳边回响起良宝的话,良宝说:我会跟齿棣谈谈的……若是你还想在这里生活……若不是……我会对你和丝雨好的……
良宝会对丝雨好的吗?我想,会的,会的,一定会的。我相信。
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