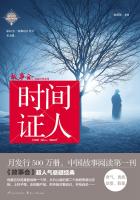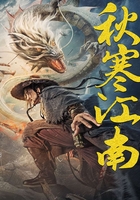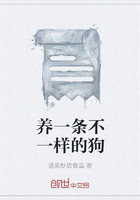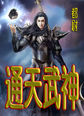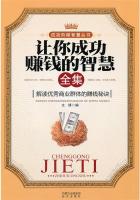四十万、四十一万、四十二万、四十三万……
两个人杠上了。
四十五万、四十六万、四十七万……
终于,在一个没有任何预兆的价格面前,年轻人停止了叫价。他明白,在自己这样的年纪,还有更重要的事去等着他做,花大把的钞票去买一幅画,的确是太过于奢侈。
光头拍卖师微笑着问他:“这位年轻的先生,您不再加价了么?您打算把这幅艺术品拱手让给这位老先生么?您不觉得就这样放弃、与自己喜爱的艺术品失之交臂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吗?您坚持了这么久,也许再坚持一下,再只加一次价,这件启老这幅花鸟小品就是您的呢!也许就只加一次价!”
那位彪悍的拍卖师的话音量不高,却充满了亲切的诱惑,他看着年轻人,年轻人犹豫着,他的双手捏成拳头,放在脸侧,他似乎在努力控制,在努力控制自己的右手,不让它不听命令随随便便伸到空中乱喊。
“五十五万!”可他最终还是没经受住蛊惑,他把右手伸到空中,高声喊道。
“好!这位先生有魄力!有豪气!”拍卖师也高兴得提高了音量,他的头皮也跟着脸膛一样发出喜悦的红光,“五十五万第一次!五十五万第二次!”
可一个声音打断了他:“五十五万五千!”还是那位老者,他再次沉着地举了举牌子。
“可是先生……”拍卖师突然面露难色,突然又像想到了什么似的,话锋一转,说,“这位先生真会幽默,十万以上,每叫价一次增加一万元。”
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哄笑。
“调节一下紧张的气氛……”拍卖师也笑了笑。
老人却没有笑,好像不认为这是什么好笑的事情,他喝了口茶,然后说:“五十八万!”
“五十八万一次!五十八万两次!五十八万三次!好,成交!恭喜您,这位老先生!启功老师的传世之作《墨竹》就收归您的囊中了!恭喜恭喜!”拍卖师这回不看年轻人了,他只把热切的目光投送给那位老人,他那温热的目光像一缕阳光,罩在每一位高价买主的身上,让人暂时相信他是来自肺腑深处的祝贺和友善。可老人依旧面不改色,抿了一口茶,向随即走到他面前的林晓白微微一笑。
事后好长时间,林晓白一直在想:这个老人怎么能够这么样地沉着冷静呢?他简直太冷静了,似乎胜券在握,难道他决定无论花多少钱都要把这幅画拍到吗?无所谓价钱?既然这么冷静,何必又花这么大的价钱来买一幅画呢。不过,她又转念一想,也许是她不了解有钱人吧,五十几万,也就一部好车而已,可能对他来说,是个小case啦。
不过,她还是小小地耍了个心眼,在问号码的时候,她故意用方言问他:“老先生,您朗个的牌牌是几多?”
以她的经验看来,在人放松的时候,听到方言就会不由自主的用方言回答。果然,老人用方言回答她:“96号。”老人说完后,不经意地皱了皱眉头,又用普通话纠正了一次,仿佛小孩写错作业,用橡皮擦擦掉一样。
幸亏她爸妈教会了她浅川话啊,不然新疆方言,老人可不一定听得懂。
不过,他用的是四川方言。
十
徐长清彻底断了念想,整个浅川城,似乎没人认识那位四川老者,他就像一尊云雾里的神龙,来无影,去无踪,不留一点儿痕迹。
他真是四川人吗?林晓白也弄不明白。但他刻意掩饰自己的四川人身份,这一点是肯定的。他为什么要掩饰呢?也许越是想掩饰,越是说明这个情况真实——说不定还是重要线索呢。可,也有可能他是故意误导。误导?可为什么要误导呢?林晓白越想越不明白。
这个神秘的老者,好长时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主要对象,人们把他在拍卖会上的种种表现都传得神乎其神,他喝茶、他举牌,就是连他整一整帽子,摸一摸他已经所剩无几的头发的动作,都有人模仿。“五十五万五千!”这句话被学得最多,那声音、那语气、那举止,都被学得惟妙惟肖,不过,模仿者似乎把音调提高了八度——当然,那是模仿的兴奋和舞台效果的需要。
而那幅《墨竹》,自然也经过无数次的渲染变得神乎其神,看过的人说那竹叶是活的,风从哪里来,竹叶就往哪里倒……徐长清听到这些的时候,是一个下午,他去新华书店买墨汁,听坐在书店门口卖对联的老者说的。他问:“你看到了?”
老人毫不客气地就回答:“那我还真看到了!我那个外甥就在文化宫工作……”老人以为他是来抬杠的。
徐长清不想跟他争论,也许他真看到了,只可惜宣传部组织几个书画家送对联下乡了,以为展览总要有几天的,哪知道就那样失之交臂了,如果知道只有一天,他就是违拗区长的命令,他也是要去的。而这懊恼,让他更加地怏怏不乐。
他走在腊月的大街上,只感叹这一年怎么就这么快就过完了呢,他似乎还停留在临摹完《墨竹》的那一刻,那时候,那胸中的那股真气啊,那是荡胸生层云,那是豪气冲云天,那是一水护田将绿绕,那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那胸中的那种畅快,那全身心的那种舒畅,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当时他只是想:原来我徐长清一辈子舞文弄墨,还可以临出这等好东西来啊!
只可惜,真迹没见着,自己的画也不知所踪。他知道,他若这时候去找鲁人凤,他一定有许多理由推脱。早知道见不到真迹,真该把自己画的那幅留下来,就是拍张照片也好,至少能留个念想啊。
徐长清走在寒风凛冽的街上,一手提着墨汁和宣纸,一手拿着帽子,心中无限惆怅,任凭寒风呼啸,全然忘了自己为什么要把帽子拿在手上。
春拍后的第四天,腊月十二的,晚饭过后,徐长清就开始腹痛了,起初以为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半夜反反复复起来上厕所,可又拉不出什么来,一阵一阵地绞痛,痛得冷汗淋漓,连喘气都不利索。
夏绢知坚持打了120。可去医院一查,不发烧,不腹痛,肠道菌群也正常,吊了瓶盐水,徐长清就沉沉地睡去了。可夏绢知却睡不着,在病房外抽抽搭搭地哭。林晓白劝慰不住,打电话叫来了刘中亮,刘中亮看着心酸,知道表姐担心姐夫的病情,也担心自己的将来。又说了许多宽慰的话。少不得常常跑医院里看看。
在医院住了两天,眼看要过年了,徐长清还是痛,却仍然查不出什么来,医生只说是神经性腹痛,要他把精神放松。
“把精神放松?怎么个放松法?”徐长清喃喃自语。
“就是叫你想开,看开些。”同病房的病友说。
难道我还看不开吗?难道我还有什么没有放下的?徐长清在心里反问。
过了两天,徐长清坚持出了院。刚一回家,看见院子里的苦楝树,枯叶所剩无几,几乎数得清,可树上挂的苦楝子还在,在寒风中嗑嗑抖动着。他突然心头一热,几乎要流下泪来,想回自己的老家看看。
夏绢知看着刘中亮,刘中亮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一行人什么准备都没有,就回了徐长清的老家清衣河。
当天,徐长清就请几个本家的侄子,帮忙把屋瓦修葺一番,好在春节他们都回家了,而砖瓦,各家门口都堆着有。当天晚上,他们就住下了。夏绢知从小在城市长大,一天也没在清衣河住过,更何况棉絮被褥都是借的别人的,那个别扭自然不消说,可是知道徐长清病着,心里又不痛快,一万个不愿意,也只得将就着他。
过了两天,他自己煎了两碗苦楝树的水喝了,那奇怪的腹痛竟然就好了。
夏绢知高兴地给刘中亮打电话,刘中亮在电话里哦了一声,就挂了电话,他知道徐长清就是好了,可他少了精气神,他也不长久的。他现在不写字不画画,只跟人闲聊,那还是徐长清吗?
表姐一家的离开,对于刘中亮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夏绢知还不知道,段部长高升了,任组织部部长,他带走了郑新锋,却没有带走一直自以为得他欢心的刘中亮。
去组织部和宣传部,对于一个司机来说,有多大区别?可刘中亮就是转不过这口气,他是哪点做得不好,让人嫌弃了?他拿了那把步枪出来,也不管什么春节不春节,白天黑夜地打狗,直打得整个浅川城的狗见了他就狂吠。
十一
和刘中亮同病相怜的还有司机小卢。
小卢苦着一张脸,满大街开着城管的市容巡逻车。浅川城的人们爱腌腊鱼腊肉,天一晴就往树上、电线杆上乱挂,加上临近年关,摆摊设点的越发多了,小卢开着城管巡逻车就是专门监督这个的。他借调去宣传部半年多,还是回来了。他跟郑新锋沾点儿亲带点儿故,一直想调过去,可惜借调去用了半年,还是回来了,这回来的滋味更不好受,他很是郁闷。他开车满大街转着,把他的烦闷带到了浅川城的各个角落。
“拐子,我跟你不一样,我是被人一脚踢开了,而你呢,哪里开车不都一样!有什么好烦的?”刘中亮跳上了小卢的巡逻车,没精打采地安慰他。
“怎么一样!我先动了那心,我又、我又……花了钱的……再说了,你们那儿毕竟油水厚些,我有老婆孩子的人,不比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小卢一肚子怨气,看来他为这事损失了不少。
刘中亮不吭声了,哪知他还接着唠叨:“你不知道,这拿了钱不替人办事,多气人哪!真他妈缺德!还是亲戚里道的!”
“可我呢?我还不是被人一脚踢开了!”刘中亮想想这几年的辛苦,他家的大姨子、小妹子,谁没用他的车,上班、逛街、吃酒、打牌,他又送又接,风里来雨里去,就是他的老家,每年十五、清明、中秋、春节,他一年跑多少趟……有几年去北京看外孙,都是他开车去的,那冰天雪地的,幸亏他车技好,才没翻下山……他心里的确像是有一团火,湿热湿热的,郁结在那里,发不出,又泄不下,令人浑身长毛般的不舒服。但他不想跟小卢多说,像个女人。
小卢知道他心里也不好受,歪着嘴巴开导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