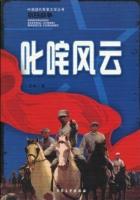1975年春节之前,鲁长顺担任煤矿保卫科长不久,参加了矿党委召开的一次保密规格较高的会议,内容是:省委领导要来慰问矿工,矿党委决定由政治部牵头搞好接待,一再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要求做到不出任何事故,尤其不能出政治事故。至于领导前来的具体时间,为保证领导安全暂时保密,另行通知。
这种会议虽然严肃,但是大家对待这种事都习以为常了。一散会,大家就迅速行动了起来,政治部拿出了一个早年用过的家庭出身好、政治上可靠、平时表现好的数百人的名单;后勤部门立即根据名单配发了崭新的工作服、长筒胶鞋、安全帽……唯有鲁长顺不知道怎么办,经过请示才知道:他和部下冒充矿工,混迹于矿工中,随时准备擒拿敢于捣乱的反革命分子。在领导到来之前,他要天天组织这些准备接受慰问的人进行演练,反复给他们讲解注意事项。
鲁长顺虽然觉得有点可笑,但是依然办得很认真,每天组织这些人进行队列训练,反复讲解领导到来后大家应该怎样做。
腊月二十八上午,鲁长顺接到了领导要来和大家共进午餐的通知,要他率队在食堂门口等候。他在11时30分就把队伍带到了食堂门口,再次给他们讲述了注意事项后,站到队里和他们一起列队等待领导到来,并不断观看队伍,看到一个个小伙子精神饱满地迎风肃立的状态,心里非常高兴。然而,他这种心情很快就消失了,领导们迟迟不到,在寒风中等候的矿工个个冻得瑟瑟发抖了,抱怨声也随之悄然而起。他理解工人们的心情,尽力劝说大家肃静,安抚大家耐心等待,下午2时,又接到了新指示:“取消共进午餐,队伍拉到煤矿办公楼前广场等候慰问。”
接到新通知,队伍的骚动声得到了缓解,大家猜测到领导就要来了,忍饥挨饿遭受寒风侵袭的折磨就要结束了,顺从地由鲁长顺带到了广场,不料又等候了一个多小时。
下午3时许,一长溜轿车、吉普车开进了煤矿办公区,一大群省、市、县领导在矿领导陪同下昂首挺胸地走了过来。
鲁长顺朗声喊了句:“立正!”
矿工们闻声,立即闭住了发牢骚的嘴巴,数百人肃立在寒风里,等候领导慰问,整个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了。
领导们走到了矿工队伍前,一个省领导威严地喊道:“同志们好!”
“领导好!”矿工们按照事先安排好的齐声吼道,震惊了整个矿区。
“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
省领导满意地点点头,走向了事先竖起的麦克风前开始讲话,其他领导退后几步,列队站在他身后几步处和矿工们肃立听讲。
这时候,站在前排的鲁长顺发现这些领导们个个红光满面地哈着热气,隐隐嗅到了一股酒臭味儿,猜测他们之所以晚到,肯定是在县里吃喝过了,心里生出了一些怨气:“真他娘的操蛋!这究竟是谁慰问谁呢?矿工们不吃不喝地等了你们将近四个钟头,就不是人啦?”
这个领导却没有鲁长顺的感受,看到数百名矿工如此恭敬,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演讲:“同志们,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现在的国际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领导按照当时的套路,先讲国际形势,再讲国内形势,接下来讲当地形势,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没了。
早已习惯听这种讲话的矿工,饥肠辘辘,冻得浑身颤抖了,可是知道这是政治任务,谁也强忍着倾听,会场上还只有领导一个声音。
领导很得意,继续着自己的演讲,不料在讲到全省形势时,听到了一声低声嘟囔:“也是大好!年年都是这一套,连块水果糖也不给。算‘牛子’慰问呀。”
一曲乐章里蹦出了一个不和谐音符,尽管音调不高,然而却让主演听见了。
领导张着讲演的嘴合不上了,怒目扫视会场。
矿工们低下了头,屏声静气地看着地面。
矿领导惊恐地在省领导身后转起了圈子。
一场政治事故发生了……
省领导毕竟见多识广,很快恢复了常态,干咳两声,接着讲演了下去。
会后,省领导愤然离场,看一眼矿领导伸出告别的手,理也不理地背转两手,登车走了。
矿领导们转身喝问:“是谁捣乱了?”
鲁长顺和矿工们低头不语,尽管都知道是齐小兵惹的祸,可是谁也不愿意揭发他,都觉得他说的没错。
“是齐小兵!”一个矿领导对书记说,“他站在第二排,没有错的。”
“查他!这时在公开场合喊反动口号,是扰乱革命秩序,是污蔑革命的大好形势,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家伙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矿党委书记愤恨地扔下一堆“帽子”,转身走了。
鲁长顺却忙活了起来,组织人审讯齐小兵,发动人批斗齐小兵,派人外调齐小兵,折腾了几个月得出了一个结论:齐小兵家庭出身三代都是贫农,其父亲是县里落实政策“解放”的水利局局长,本人两年前中学毕业后被招工到矿上的,平日里劳动卖力,政治上没有反动表现。
鲁长顺本以为这一结论可以挽救一下这个敢说实话的年轻人,矿党委还是给了齐小兵一个“开除留用”的处分。
这一事件深深地刺痛了鲁长顺,他觉得这是形式主义害死人的一个典型范例,把齐小兵的名字刻到了心头,决心找机会将他保下来。命运似乎在和他开玩笑似的一直不给他这个机会,不久他就被调到了云县担任公安局长,失去了为齐小兵说好话的权利。
他担任县局局长后,还记着齐小兵的教训,从内心里反对这种形式主义的慰问,遇到这种事就想法躲,不是到下边办案,就是检查消防、治安……他没有想到这种躲避竟然给自己带来了许多好处,除了赢得干警们夸赞外,还赢得了领导好评。几年后,几个省、市领导前往云县慰问,听说他正在抓一个大案而没有参加后,一位省领导说:“这个局长有几年没有参加慰问,都在忙着工作,实在难得呀。我到别的县,看到的都是围着我转,竭力讨好我,目的无非是要给我一个好印象,想得到提拔嘛。我看这些人不能提,这个人应该提,县里的同志们觉得怎样?”“我们接连推荐几年了,都因为他学历只是初中而被退回来了。”县委书记如实说。省委领导立即耷拉着脸说:“乱弹琴嘛!现在一讲干部知识化,干部们都搞什么电大、夜大学历,有的还弄上了博士、硕士,谁知道他们怎么弄来的?买的还是真学了?真学从哪儿来时间?还有时间工作?我看这种埋头苦干的人要比整天搞学历的人有水平。这样的干部,你们市委要不要?不要的话,我们省里要。”市委领导急忙点头答应说“要”,并让县委尽快整理材料上报,经过严格考察破例提拔鲁长顺当了市局副局长。
鲁长顺升任市局副局长后,还是找借口回避陪同领导慰问,有一年竟然到交管局上岗指挥交通了。省领导慰问的车队经过他指挥的路口时,一位省领导看到他站在马路中央的指挥台上有板有眼地打着指挥手势指挥后说:“这才是值得慰问的人呢。前年他在检查节前消防,去年他在带队巡逻,检查治安,今年,唉,这样的干部怎么得不到提拔呢?”“学历太低,没有办法呀。”市委书记感叹道,“听说提拔他当这个副局长时,当时的市委领导就和省委组织部磨了半天嘴皮子。”“扯淡!”省委领导作色道,“你们觉得够不够提拔的格儿?拿学历压人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如果他只是除了学历不够。你们就走程序向省里推荐。”
鲁长顺再次得到了提拔,当上了省公安厅副厅长。一路走来,看起来很顺,其实已过二十多年了,如不是学历作怪,也许早到这一位置了。他升至副厅长时已成了公安厅领导班子中年纪最大的人,可是凭借着丰富经验和埋头苦干的精神,依然赢得了整个领导班子成员的爱戴和赞扬,而最先领略到他水平的人就是茅箭兵。
一次,茅箭兵接到检察院汇报:“一个身为市委副书记的犯罪嫌疑人被检查院逮捕后,在看守所翻案了,否定了已经交待的全部贪污、受贿事实,检察院决定从现住的看守所提出,另找地方关押。”
正在茅箭兵办公室等待汇报工作的鲁长顺闻听此话,“嘿嘿”笑了。
“你笑什么?”茅箭兵不解地问。
“不高明!”鲁长顺笑着说,“翻案意味着原先的证据链条断裂,这不是小事。犯罪嫌疑人敢于这样做,肯定是和看守所内的干警勾结上了,并通过‘内鬼’和外面串供了,换到别的看守所,他依旧王八咬死嘴,检察院还得重新取证。其实最好的办法是还让他住在原来的看守所里,让‘内鬼’现形,让他们自己再把翻过的案翻过来。”
“对呀!”茅箭兵连连点头说,接着拿起电话把这一意见通知了检察长,最后嘱咐说:“让他还住在原来的看守所里,你们要做的是调取看守所干警和犯罪嫌疑人家属的通话记录,监控他们的通话,找出‘内鬼’来,让他们自己再把案子翻过来。”
这一招果然灵验,检察院当天就查到了一个看守所干警和犯罪嫌疑人老婆的通话记录,两天后就把他们再次通话的录音拿到了。面对录音,“内鬼”低头承认了接受犯罪嫌疑人贿赂并为之通风报信的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不得不交待了自己趁看病输液之际买通这一干警的罪行。
茅箭兵从此彻底服了鲁长顺,每遇难题必向他请教,每次都能得到一个相对简易的快捷方案。因此,他今天提议提拔鲁长顺到正厅级,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潜藏在内心许久的一个想法。
说了一段闲话,返回头来再说鲁长顺对待下基层慰问。
鲁长顺当上副厅长以后,想再回避下基层慰问就比较难了,只好遵从党组分工下去慰问干警。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年形势变了,再下去不用空着手了,每次都能带上后勤部门准备好的礼物去见基层干警。不过,他还牢记着省领导慰问煤矿职工的往事,下去之前绝不通知,下去时轻车简从绝不带无用之人。
今年下基层,他被党组分到绿县去慰问一线干警。接到任务后,他因为在那里的煤矿工作过,家乡也是那里的,对那个县的情况比较了解,首先就想到了黑山关交警站。
黑山关位于两省交界处的国道关口上,不仅距省城远,就是离县城也有百余公里。这个关卡设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的任务主要是防止本省物资外流,人员也归工商部门派遣管理。改革开放之后,原有的职能日渐减弱,车辆却日益增多,急需交警疏导交通,处理违章和事故, 公安部门就从工商部门手中接管了这个关卡。因为地处边缘,所以不要说省、市领导前往,就连县局领导也很少光顾,其生活状况之差是可想而知的。鲁长顺选择此处无疑是正确的。
定下黑山关之后,鲁长顺嘱咐了后勤部门负责人几句,第二天一早就带上党组领导指派的后勤、宣传等有关部门人员驱车直奔黑山关,路过县城才打电话通知县局局长已经到达,请他与有关人员到黑山关汇合。
鲁长顺一行两部越野车和一辆轿车驰向黑山关,一路上还算顺利,只是车到关口不远处才发现有些堵车。他在心里念叨着“路窄、干警忙”,让司机把车开向路旁的一条小路,说:“应该在这个山坳里。”
“不像!”司机说,“这道坑坑洼洼的能把人颠晕、颠散骨头架子。”
“别说了,向前看嘛!”
“哟!还真是这个地方!”司机说着,把车开到一排窑洞前停下了。
这是一排依山修建的用石块圈起的窑洞,石块蒙着厚厚的黑色粉末,已使人难以分清石块的本色了;各个窑洞的窗户很小,但是都有一个伸向洞外冒着黑烟的烟筒;窑洞外面堆放着一堆小山似的煤炭;若不是一个窑洞口上挂着一个写有“黑山关交警队”的木牌和一辆警车,谁也不敢想象这里就是一个代表国家执法的机关。
鲁长顺下车后,站在远处,望着窑洞,连连感叹:“真苦!真苦!”
“是啊!这时候,我都不能在煤火屋中呆了,人家还在这里住着、办公,太不容易了。”司机感慨地说。
随同前来的政治部副主任问鲁长顺:“鲁厅,怎么不见一个人呢?”
“没看见堵车啊?”鲁长顺阴沉着脸说,“人家都在疏通道路呢。走,咱们看看去!”
“好!”大家一致响应喊。
“你们就别去了!”鲁长顺手指机关后勤的负责人说,“把我嘱咐你弄的东西搬出来,做几个可口的热菜,今天中午,咱们好好地和他们喝几杯。对啦,买酒花了多少钱?”
“没多少钱,算了,由我处理……”
“你怎么搞得?”鲁长顺有些生气地打断他的话说,“是你来慰问,还是我来慰问?为什么不买好酒?”
“鲁厅,别发火。买的是千把块钱一箱的酒,差不多了。”
“是差不多!”鲁长顺从衣兜里掏出一沓子百元面额的钞票,递向后勤部门的同志说,“拿住!这是两千块钱,连下酒菜的钱也有了。记住,按照党组决定办事,额外部分谁的官大谁掏钱。党组决定光让我们送米、面、油,喝酒是我的心意。你如想替我当副厅长,你就掏钱。”
“好,好!”后勤部门的人急忙接过钱来,又退给他几百元,并拿出了一张发票说:“这是剩下的钱和买东西的发票,你看看吧。”
“看‘牛子’哩,走啦!”鲁长顺说完,接过钱装入衣兜,接过发票撕毁扔到脚下,带着大家走向一条斜插向国道的小路。
他们沿着小路只走了十分钟左右,便来到了国道边卡处,惊异地发现这里的道路已和刚才完全不一样了:堵塞已被疏通,车辆来往如梭,非常壮观。六个交警分别站立在路中央岗楼旁,对着左右通行的车辆行着注目礼。
“鲁厅!”一辆警车停在了他们面前,县局局长叫着从车里出来说,“要不要上岗体验体验?”
“不行啦!老了,不敢和他们比了。”鲁长顺说着,看看公路上没车,急忙越过公路,来到岗楼前与一个个交警敬礼、握手,问候。
干警们在县局局长介绍下,一个个激动地给鲁长顺还礼、握手,说一些感谢的话。
鲁长顺走到最后一个干警身边的时候,不由自主地眼圈红了。他看到了一个满脸油黑,胡茬花白、制服已分不清什么颜色的老干警,想到了这种环境,激动地握着他的手问:“老同志,在这儿干多久了?”
“二十多年啦,自从被发配到这儿就没离开过!”
“嫂子和孩子们住哪儿?”
“住城里!”
听到这里,鲁长顺转脸问县局局长:“这么艰苦的岗位,怎么让人家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过去曾给他调过岗位,他执意不去呀!”“多好的同志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人家越是这样,我们当领导的越应当给安排好生活!”
“是,我们一定按厅长指示办!”
“什么指示?我只是建议。”
“建议就是指示!”
“不能执行这个指示!”交警突然插话说,“厅长有私心,是利用职权照顾老熟人。”
县局局长呆了。
鲁长顺也愣了,思考半天后才问:“咱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鲁科长,我是齐小兵呀!”
“齐小兵?”鲁长顺眨眨眼,从面前一脸沧桑的交警脸上找到了当年齐小兵的一些特征,激动地抱住了他,流着眼泪说,“小兵兄弟,你可让我找见了!对不起,让你吃苦了!为什么不找我?你可知道我多么想见你?”
“谈不上苦!”齐小兵脱离开鲁长顺的两个手臂说,“哪种年代,是我自作自受,我从来没有怪过你,还知道你为我说了不少好话哩。后来,我的问题平反了,我爹给县交通局说了说,就把我安排到了交通管理股,后来就转成警察了。我想找你表示感谢,又怕人说高攀领导,就想凭着自己的本事干。就是这么一回事,你不怪怨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