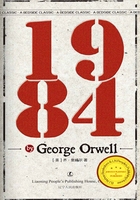“他让考布拉给我送了一封信,但是我们现在必须非常小心,因为我的父母在监视我。他们说,我和别人偷偷相恋让家族蒙羞,会给别人留下话柄。他们吩咐管家搜查进门的每一个仆人,以防他们为我传递信件。”
“他给你写了什么?”
“即便我老了病了,即便我头发灰白,走路一瘸一拐,他也会永远爱我。”
“我很难过,”我说,“我知道你有多爱他。”
娜希德咂了咂舌头。“你怎么知道?你从来没有爱过。”她几乎是生气地说。
我承认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在和费雷东度过快乐的一夜之后,我的感觉开始改变了。我思索着这是不是可以叫作爱。
“亲爱的娜希德,”我说,“在来的路上,我还十分肯定你要告诉我,你和伊斯坎达尔订婚了,你就要实现自己最大的心愿了,所以,我很高兴地哼着歌。”
“我也这么以为。”她回答。
我想了一会儿:“如果伊斯坎达尔很出色的话,你父母是否有可能改变主意?”
“不可能。”她阴郁地说。就当我以为她不会再哭的时候,她弯下腰,就像被困的动物一样呻吟着。自从父亲去世后,我就没有听过这样的恸哭,她的声音让我的心都碎了。
我尽力安慰她:“娜希德,我的心肝,你还有希望。让我们向主祈祷,他一定会垂怜于你和伊斯坎达尔的。”
“你不明白。”娜希德回答,接着又低声哭起来。一个仆人敲了敲门,说为我们送来了咖啡。我跳起来,从她手中接过盘子,不让她进来,以防让她看到娜希德满脸的泪痕。
“没关系,”她说,“他们都知道我订婚的事了。”
我很迷惑:“什么意思?”
娜希德的眼泪流得更厉害了,就像春天的大雨一样:“如果我放弃了伊斯坎达尔,我的父母也许什么都不会做,但是我流着泪告诉他们我永远都忘不了他。因此,他们替我和另一个男人订了婚约。月圆的时候,我就要结婚了。”
这个消息比上一个还残忍。娜希德的父母如此宠爱她,怎么会在她还在为初恋哀悼的时候,就把她扔给另一个男人呢?我为她感到非常非常难过。我再次搂着娜希德,把头靠着她的头。
“那你要嫁给谁?”我问,希望是个能让她幸福的好人家。
“母亲拜访了赫玛,她说她知道有一个合适的人,”娜希德痛苦地说,“当然,我从来都没见过他。”
“那你知道关于他的任何事吗?”
她的父母一定为她挑了一个百里挑一的人,因为娜希德不仅有貌,而且有财。也许他是个和她门当户对的人,而且会为她揭开那些我已经学会享受的夜间之乐。
“只知道他是一个富有的马商的儿子。”
我盯着娜希德。我知道我必须说些什么,但是我却说不出话来。我开始咳嗽起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我弯着腰,低着头,寻找着空气。
“天啊!”娜希德说,“你还好吗?”
但这个打击似乎无法终止。我一直咳着,直到流出泪水,但仍然说不出话来。
“你看起来很痛苦。”我擦着眼泪时,娜希德对我说。
“如果你知道得多一些就好了。”我回答。我强迫自己保持缄默,因为我常常太冲动。一定有成百上千个富有的马商吧?至少有几十个吧?
大多数都有儿子吧?一定会是其他人的。
“他叫什么?”我突然问,十分紧张。
“我不知道这对你有什么意义,”娜希德回答说,“因为这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他叫费雷东。”
我又咳了起来,仿佛我就要失去自己的生命支柱。当然,我可以告诉他关于他未婚夫的一切:解下头巾的头发是怎样的,听到卡曼奇的声音时他是怎样狂喜地闭上眼睛的,他兴奋时身上散发的味道是怎样的。现在我甚至知道要怎样取悦他,但是只有她才有权成为他的正室妻子。一股妒忌的热流窜遍我的全身。想到他也许会更喜欢她时,我开始咳得喷溅起来。我希望她没有猜疑我为何会如此。
娜希德被我如此突然的举动感动了:“我最亲爱的朋友,我很抱歉我的困境让你如此不安。请不要让我的坏运气黯淡了你的生命线。”
我赶忙想要如何为自己解释。“我只是希望你幸福,”我说,“你告诉我的一切把我的心都撕碎了。”
她忍不住流出泪来,而我的眼睛也被湿气笼罩着。但是娜希德的眼泪掺杂着对友情的感激,而我的眼泪则隐匿着一个内疚的秘密。
最后一次宣礼声响起了,告诉我应该回家了。我离开悲痛的娜希德,揣着自己的忧伤慢慢地走回家。我独自走在街道上,终于可以不用隐藏自己悲伤的真正原因了。难怪费雷东这么多周都不理睬我,他一定在忙着和娜希德的父母讨论婚约,安排结婚的细节。
那我们的夜间之乐又该如何?每天晚上,他让我竭尽所能地满足他,直到公鸡报晓,带走我的所有,仿佛这是他的权利。我的鲜血沸腾起来,我在四花园里走得越来越快,直到撞上一个拄着拐杖的驼背的老婆婆,然后向她道歉。
我听到灌木丛里传来一阵猫叫声。也许它正在寻找它的另一半,就像我一样。我从来都不要求什么,只求嫁给一个好男人。为什么我只是一个情人,而已经拥有一切的娜希德却能成为他永久的妻子呢?为什么伊斯法罕有这么多男人,她要嫁的偏偏是费雷东呢?
我到家的时候,厨子听到了我的脚步声,于是在厨房里叫着我。“你迟到了,”她抱怨道,“快来帮忙洗莳萝。”
“别烦我!”我大叫。厨子惊讶得掉了手上的刀。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管这样犟的孩子的。”她对母亲说。我不理睬她,冲过院子回到我们的小房间。费雷东怎么可以不告诉我他已经定下了婚约呢?虽然他不知道娜希德是我的朋友,但是他对我隐瞒了这么重大的事情,说明我在他眼中是多么渺小。
第二天,费雷东又召见我了。我到他家时,拒绝让海耶德和阿齐兹为我洗澡、熏香、洗头发。我的地位已经恢复了,她们又开始害怕我了。她们对我又是乞求又是恳求,直到我冲她们大喊让她们离开,她们才战战兢兢地走了。我坐在和费雷东嬉戏打闹的小房间等候他,身上仍然穿着外出服。我非常生气,甚至觉得周围的空气也越来越热,我的脸也热辣辣的。
当费雷东到的时候,他注意到了我这异常的装束,但什么都没说。他脱去鞋和头巾,吩咐仆人们离开。接着,他坐在我身边,牵着我的手。“听着,灵魂。”他说话了,仿佛接下来要向我解释什么。这是他第一次叫我“我的灵魂”。
我打断了他的话。“你不想再要我了。”我说。
“我为什么不要你?尤其是经过了昨晚之后。”他笑着要推开我的膝盖,但是我紧紧着拢着双腿。
“但是你要结婚了。”
“我必须结婚,”他说,“别担心,什么都不会改变的。”他的回答只意味着一件事。
“你的意思是,你要享齐人之福?”
“当然。”
“你不知道这会造成什么样的麻烦。”
“为什么?”
“娜希德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的确看起来十分惊讶:“在伊斯法罕所有的女人里——”
“而她不知道我和你的临时婚姻。”
“为什么不知道?”
“我的家人告诉我要保守秘密。”
费雷东耸了耸肩。“你的家人考虑的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他说,“但是人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难道这不会影响你的社会地位吗?”
“男人可以随自己所愿地结婚。”他回答。
我看着他那件昂贵的印着猎鹰图案的蓝色天鹅绒长袍,那一刻,他仿佛拥有全世界,而我却一无所有。
“不管怎样,别人怎么想有什么关系?”他说,“相处和睦的妻子们不仅可以互相照顾孩子,还可以在女性问题上相互帮忙。”
“我连你真正的妻子都不是!”
“这也没有关系。”
我沉默了,因为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嫁给费雷东这样的有钱男人可以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我等待着,希望他能恳求我嫁给他,但他没有这么做。
费雷东搂着我,但我没有顺从他。“这是我父亲的意思。”他说,他的呼吸让我的耳朵变得温热,“他总是想和伊斯法罕某个有地位的家庭结成姻亲。这可以帮助他争取一个政府职位。”
他叹了口气:“但是不要觉得我不要你了。如果我真的不要你了,我会让你离开,就像秋天的树抖落叶子一样。”
我没有回答。如果娜希德不像阳光一样灿烂夺目,他永远都不可能向她的家人提亲。
“她很漂亮。”我几乎有些生气地说。
“我是这么听说的,”他回答,“过两天我就会亲眼见到她了。”
费雷东开始用他柔软的手抚摸我的脸颊:“我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但从我见到你,而你命令我不许看你的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你了。大多数的女人都会假装礼貌,然后慢慢走开;你让我见识了你的泼辣。我喜欢你黑色的头发和棕色的皮肤,它们就像两块华美的深色地毯。你太小了,所以我觉得你不会是戈斯塔罕的女儿。所以,那个小男仆回来时,我给了他钱让他告诉我你是谁。当我雇佣戈斯塔罕为我做地毯的时候,我要求他在地毯上织一些护身符,因为我想让这设计图上有你的痕迹。当我看到还在编织的地毯上那些闪闪发亮的宝石时,我便决定要拥有你。”
他的话让我的心第一次快乐地飞翔。“我一直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我。”我说。
费雷东叹了口气。“我的生活里处处都是一些为了赢得更多的钱而赞颂我的人。我的第一个妻子在去世之前,也是为了得到她想要的东西才悉心照料我。你并没有这么做,而我喜欢这一点。”
这让我十分惊讶,因为我用我的身体尽我所能地取悦他。但的确,我并没有对他说任何甜言蜜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