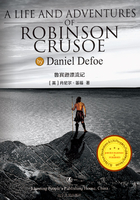在人们的心目中,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是以其小说、杂文、散文为主要创作标志的。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编选这本“鲁迅随笔选”呢?究竟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算作鲁迅的随笔呢?它和鲁迅的杂文、散文又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所谓随笔,英文名称essay,在英文中,散文、小品文、随笔、短论,都叫essay。这一文学概念在“五四”时期得到新文学界许多代表人物的大力弘扬,特别是周作人。中国文论中自然也有与essay相应的概念,中国文学史中自然也有可划为essay的创作,比如最早的《容斋随笔》。那么为什么五四先驱们却偏要引入这么一个“洋概念”来做中国的文章呢?
原因就在于他们希望通过引进的文学概念来打破传统中国文化中以“载道”为正统的文学观,解放个性,追求心灵与情感的自由抒写。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往往充满着悖论。旧的“载道”文学被打破了,新的“载道”文学又发展起来。这其中的原因不是简单几句话能说清楚的,即便是鲁迅也不能不自觉地投身于新的“载道”文学——鲁迅称之为“遵命文学”的创作当中。鲁迅的小说、杂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的“遵命文学”;这些创作曾发挥过推动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然而鲁迅本人对于这样的“遵命文学”却总是怀着隐忧,担心普遍的对于“遵命文学”的追求可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比方说他从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教人吃西瓜时不要忘记我们的国家也像这西瓜一样面临着被割碎的危险,他不禁讽刺道:“但倘使我一面这样想,一面吃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倘若用西瓜作比讲过国耻讲义,却立刻又会高高兴兴的把这西瓜吃下,成为血肉的营养的人,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鲁迅始终对文学的“目的性”抱有警惕,反对从生活中提炼出所谓的“精华”作为人生惟一的价值和意义。他为生活中的平凡和琐碎辩护,认为那些“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的人不过是“盲人摸象”,而且。“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归根到底,这种隐忧的实质就是担心本来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之目的而必须的所遵之命、所载之道,反过来却形成对人的新的压抑。
正是因为鲁迅能够超越具体时代与具体任务,始终不忘“人的全面解放”这一所有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根本目标,才使得他的作品和思想具备了超越时代的普遍性。鲁迅不属于这样一类作家和思想家:在某个特定时代,由于他们最好地切合了时代的要求而享有盛誉,但时过境迁,他们已很少被人提起。
从文学概念上来讲,鲁迅的随笔、杂文、散文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但是从“五四”时期引入随笔这一概念背后的考量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鲁迅的“遵命”色彩浓厚的杂文名篇之外,还有许多很好的文章,直到今天仍然能够让人看了以后会心一笑或者掩卷长思。这些文章取材随意而微末,如国骂“他妈的”,如一般读书人耻谈的“发薪”,如随处可见的世相“揩油”,如“宣传与做成”、“以脚报国”、“吃教”等对某些神圣事物的有意的“曲解”甚至是“恶搞”。和“鲁迅杂文”所包含的特定意味相比,“鲁迅随笔”显得更轻松,更洒脱,更幽默,更随意,自然也更为生活化。如这样一段开头:“夜里睡不着,又计画着明天吃辣子鸡,又怕和前回吃过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样,愈加睡不着了。坐起来点灯看《语丝》,不幸就看见了徐志摩先生的神秘谈……”我以为那第一句话简直是妙不可言,真正是在寻常与随意中深入到生活与人性的骨髓里去了。类似的文字还有很多,再如《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对于萧伯纳来访这件许多人笔下的“文化交流盛事”颇为调侃,鲁迅实在是无法发现一个名人来访就怎样造就了伟大的意义,只能是老老实实记流水账,老老实实承认“我对于萧,什么都没有问;萧对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但同时鲁迅却如孩子般的耍了个花招——他非常自然地以自己这老实人的老实衬托出许多自以为聪明者的可笑:“第二天的新闻,却比萧的话还要出色得远。在同一的时候,同一的地方,听着同一的话,写了出来的记事,却是各不相同的”。
至于“鲁迅随笔”与“鲁迅散文”的区分,也需要在这里简单说说。钱理群先生曾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其所作《鲁迅散文全编·序》中对“鲁迅散文”做了如下定义:“我们可以说,鲁迅的小说与杂文是偏于‘为别人’写的,他的散文则是偏于‘为自己’写的,也就是说,他要借散文这样一种更具个人性的文体,来相对真实与深入地来展现其个人存在。”
“鲁迅随笔”自然也带有更多的个人色彩,但其与“鲁迅散文”的区别则在于它跳脱出个人抒怀与公共叙事之间的对立与差异,重在表现鲁迅作为一个生命体所显现出来的舒展自如的生命姿态。“鲁迅随笔”中的鲁迅形象似乎更外向、更阳光、更活泼一些,或品评世事,或自得自嘲,或“忽然想到”,或道上一段“娘儿们也不行”的道理,历史社会时政内心世界无所不包,自由地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打破了内心世界和外在社会的界限。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鲁迅随笔”仍然有着自己的特质,绝不可庸俗化为“心灵鸡汤”之类的玩意,和坊间流行的“周作人随笔”、“林语堂随笔”等轻松文字相比,更具对生活的穿透力,始终保持着直面真实的精神,从来没有无关痛痒之语。在《“寻开心”》一文中,鲁迅针对有人提议教育部应“设法标榜岳武穆、文天祥、方孝孺等有气节之名臣勇将”,“随笔”到:“或者查查岳武穆们的事实,看究竟是怎样的结果,‘复兴民族’了没有,那你一定会被捉弄得发昏”:但鲁迅并未就此止笔,止于这点小幽默和小智慧;他接着“随”下去,点出了这“发昏”的根源乃是没有认识到中国许多事情的实质乃是“玩玩笑笑,寻开心”,而认真的人一较真自然不免发昏。如果说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随笔好比两个绅士之间的随兴闲聊,那鲁迅的随笔就是在这绅士般的闲聊时,其中一人已于不知不觉中将另一人的衣裳剥得精光,令对方大窘——相比之下,谁更“随”?也正因为此,直到今天,如果我们善于联系现实,就会发现鲁迅的随笔仍然保持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比方说如今许多行业机关都好搞宣誓活动,如今年年初看到的一条新闻——“‘自然微笑迎客,给人以优秀服务形象;岗位礼仪规范,给人以优美服务文化;行业技能精湛,给人以优质服务享受;文明双语接待,给人以优良服务沟通;窗口诚信环境,给人以优等服务互动……’昨天,随着淮海路窗口行业广大员工的声声誓言,淮海路窗口行业‘迎新年阳光、迎奥运、迎世博总动员’主题活动拉开序幕。”看看鲁迅关于这类宣誓的随笔吧:“现在是盗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赌咒也摩登,变成宣誓了。”而巴鲁迅早已料到自己这样乱说话可能激起的反应,自己就先说了——“说出来么,那就是刻毒”。
基于以上对鲁迅随笔的认识,我们编选了这本鲁迅随笔集。所选作品,不包括《野草》和《朝花夕拾》中的篇目,也不包括鲁迅上世纪30年代写下的大量文艺论战名篇,内容上以社会、思想、文化、生活见闻方面的随笔为主,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偏向于“准风月谈”的那一类文字。这些作品基本上按照发表时间的顺序排列。其中1918—1919的“新青年”时期、1924—1925的“语丝”时期、1933—1934的“申报·自由谈”时期可以说是鲁迅随笔创作的三个高峰期。
希望通过这本选集,使读者看到一个更亲切、更活泼,而又不失智慧和泼辣的鲁迅,能够在轻松一笑中对我们品评当下生活世事不无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