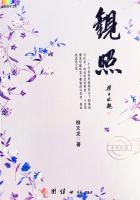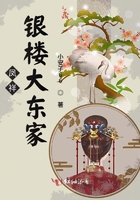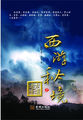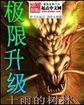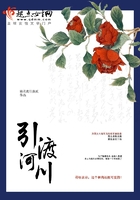小说进展得很顺利,暑假结束了,我的小说也写完了。一开学,我就在《千帆》小报上进行了连载,这一连载再一次引起轩然大波。这是一部描写年轻人寻找梦想的小说,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缩影。同学们看了,感动得一塌糊涂,纷纷表示说出了压抑在他们心里的愿望,展现出了那种敢想敢做、敢爱敢恨的年轻本色。这以后,我的信件更多了,他们都说“你竟然能写长篇小说,这在我们学校是从来没有遇见过的”。
这件事情很快传到了班主任那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先是把我夸奖了一番,然后就是一番“但是”。其实,我早就料到班主任想要对我说些什么。我也不否认,考大学对我来说也很重要,现在正处于关键时期,但我认为考大学与我的写作并不矛盾。但我没有与班主任理论,这是徒劳的,对错都是为了爱,班主任的出发点是好意,希望我能考上名牌大学,所以当着他的面我答应他暂且把写作搁在一边,事实上,私下里,我依然我行我素。
有时候,人是需要疯狂一点。
长篇小说的完成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大学,我的梦想终于实现
现在想来,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当你说它不可能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具备了可能性,只是潜伏在地下等待某一天的爆发。我以前认为出书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在出版前的一个月我仍然这样认为,然而,不可能却变成了可能,还变成了现实——我的长篇小说《爱在忧伤的日子》出版了,就在大三那一年。
与初中高中不同的是,我一进入大学,系里的同学们就以“才子”称呼我,虽然我觉得很别扭,但也无法封住他们嘴。我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多少多少的文章,尤其是在高二就写出了长篇小说被他们传得神乎其神,他们惊讶地说,没有想到这样的人就在他们的身边。如果现在回想起来估计他们一定要笑话自己当年的少见多怪了,因为这样的人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稀罕。
我学的是出版专业,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机遇。在我对“出版”这两个字有了较深的领悟之后,在同学们的鼓励下我开始有了把我在高中写的长篇小说《年轻本色》投给出版社的念头。我记得那是大一的下学期,我不知天高地厚,直接打电话给作家出版社的总编室,要来了地址。然后抱着我的手写稿找到出版社,敲开总编室的门,说明了来意,一个女编辑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就把我支开了,说总编室不受理自由来稿,要我去别的编辑室。我忐忑不安地敲开了另外一个编辑室的门,还好,这一次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他叫我把稿件放下,一个月后给我消息。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一个月后我的稿件被退了回来。但我至今仍然感激那位老编辑,他不仅实现了一个月给消息的诺言,还给我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回信。在无法满足我出版愿望的这一点上,他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他说像郁秀这样的作品他们接了太多,只可惜我不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之后,鼓励我不要放弃,就像我的小说题目一样,年轻本色,就是要敢想敢闯,不怕失败。
我真的很感激作家出版社的那位老编辑,因为他的那封信我坚持了下来。在现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年代,那样敬业的编辑实在太少了。后来,我又找了几家出版社,都没有消息。也许是我的稿件在质量上还没有达到要求吧,再找下去也是浪费时间,于是我放弃了。由于这部小说我原本就没有打算要出版,所以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失望。
虽然放弃了投稿,但我并没有放弃写作。大一的暑假我又开始了创作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就是后来正式出版的《爱在忧伤的日子》,原名是《我的荒谬今生》,为什么改成这个我想大家的心里都清楚。
这是一本融进了我很多思考的小说,关于青春,关于忧伤,关于残酷,关于爱,关于死亡,关于荒谬。那个暑假,我在湖南永州经历了一场我有生以来从未碰到过的酷暑,在那段酷暑里,三年来积压在我内心深处的东西开始蠢蠢欲动,终于,一发不可收拾赤裸于世。于是就有了这本《我的荒谬今生》实验体的小说,一本把鲜血、死亡涂抹在雪白的墙壁上的小说。一个懵懂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带有叛逆性格的血性青年,以少年忧伤的目光图解成人世界的现实和悲哀,那个偏僻而充满诱惑力的藕香村,遥远而似乎近在眼前。藕香村的那些男男女女,那些风俗尘世,那些观念思想,整个的被“我”
少年忧伤的目光解构和重建了。玉珠奶奶和爷爷违背人伦的真爱,少年与少年之间的血案,涛哥与几个女孩的情感纠葛以及与“我”似是而非的兄弟情谊,执著追求与无奈拒绝的矛盾,一次又一次的死亡,残忍的、温情的、荒谬的、正常的、偶然的、必然的,一切的一切都充满了悲伤、悲哀、悲壮的色彩。我企图用重复叙事和极端体验来叩开人性之门。
作家社的张老师说,我不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所以,这一次我想做一回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小说写完后,我投给了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个朋友介绍的一个年轻的编辑。三个月没有回音,我打电话过去问说他已经辞职了。我只好自认倒霉,又给了北京的一家出版社,一个月后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的小说文本确实很独特,尤其是对加缪的荒谬主义哲学有些思考,可惜的是我以前没有出过书,他们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替我的小说做实验。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言下之意,怕我的小说没有人看,卖不出去。挂了电话之后,我开始感到迷茫,一个鼓励我创新,一个又说没有市场,真是左右为难。《我的荒谬今生》和《年轻本色》一样被几家出版社拒绝之后,又被我束之高阁了。不得不承认,有那么一刻,我感到很绝望。
虽然投稿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可是,我的表达欲望反而越来越强烈。大三刚开始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一个大三学子的自白》。文章发在网上,迅速流行,网友们说,那是一篇血泪之作。后来这篇文章被评为2004年度大学校园里最为热门的帖子,再后来《大学生》杂志选发了这篇文章,接着《青春》也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我把杂志寄给我高中最好的同学,她看了,用短信回了两个字:想哭。随后又说,写一篇小说吧,就关于这方面的。
我答应了我的同学。小说历时四个半月,艰苦而幸福。我发给我的同学,他们说,真实得让人落泪。是的,很真实,炽烈而真实的情感。我写的时候,眼泪经常大滴大滴地掉下来,我的稿纸现在还有泪水的痕迹。小说在网上连载后,很多网友给我留言,他们说我的风格很像郭敬明,很像,很像,简直就是他的翻版。甚至有人问我是不是郭敬明的兄弟。对每一个读者的评价我都很感激,我想说的是我不是郭敬明,我没有他那么有才华,那么的幸运。我也从来没有模仿他的想法,我已经过了模仿的年代。但我仍然很喜欢他的小说,他是一个用感情写作的人,我喜欢有感情的作品。同样我也是一个用感情写作的人,天生是这样的,这可能与我的经历有关。我只是把最真的事,最真的情写出来。所以,那么多的读者喜欢我的小说,不是因为我的写作天分有多么的高,而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部小说当中寻找到自己的影子,我只不过是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
机遇总是青睐那些时刻准备的人,这一次,出奇的顺利,我把稿件发给现代出版社,第二天他们就给了我回复,说愿意出版我的小说。我记得当时我的手颤抖得很厉害,握笔都握不住了,有窒息的感觉。两个月后书出版了,我再一度成为大学里的焦点人物,我们系专门在图书馆给我做了宣传和作品讨论会。那一阵子,我的手机,我的电子邮箱,还有QQ等等到处都有读者的留言,还有的读者深夜打电话给我,一说就是几个小时。这样的喜悦来得太快,我有点承受不住,我记得拿到书那一天,我在扉页上写了这么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接下来的日子似乎好运不断,《爱在忧伤的日子》卖得很好,第一个月就登上了北京图书大厦的畅销书排行榜,出版方也加印了。在这本书的带动下,我的另外一本小说《我的荒谬今生》也被华龄出版社相中了。只是发生了点小分歧,编辑认为我的书名不好,想改为《爱在忧伤的日子2》,因为本书的风格和《爱在忧伤的日子》很相似,改了以后市场会更好。我和编辑理论,但他们根本就不听我的,说如果不改的话就出不了。最后,我想起这本书的坎坷命运,我不得不妥协。这是我感到最为悲哀的一件事情,不仅仅为自己悲哀,为出版社也为和我有着类似经历的作者悲哀。对于一个不知名的作者来说,他永远处于弱势地位,为了获得在文学上的话语权,只得一次又一次向出版社妥协。不是我们懦弱,而是现实太残酷,我们无法改变环境,只好改变自己。我们这样屈辱地活着,就是为了以后能真实地表达自己,创作是一件很自由的事情,我们希望有一天不再看出版社的脸色写作。可事实上,有这一天的人太少。
在大四的时候,出版社安排我去了一趟贵州,在贵州的高校和同学们交流,顺便做现场签售。我记得有一位大一的学生问我,在大学期间就出版了这么多书,我的写作的动力是什么,是对文学的追求还是为了名和利?假如在面包和写作面前要我选择一样,我会如何选择。大一的学生确实很单纯,这个问题有点幼稚,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我不是一个纯粹理想主义者。我写作的动力是表达的欲望,但我不排斥因为写作而带来的名和利,如果要我在面包和写作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我会选择面包,然后继续写作。那位同学听了我的回答似乎很失望,我从他的眼神当中可以看出来,他把事物看得太完美,他把写作看得太神圣。当然我丝毫没有看轻他的念头,他有他的想法,我有我的选择。
还有一位同学这样问我:“在这个文学还不如一只苹果的年代,作家成了一个落寞的群体,风光不再,更有甚者,有人将作家跟落魄潦倒划了等号,我想知道对于你的未来是如何看待的。会继续在文学这条道路走下去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首先否定了他的看法。我说:“你过于偏激了。如果真正有志于创作事业的人并不会因为收入的低而放弃。而且作家从来就不是一个落寞的群体,你看越来越多的人企图通过网络而一举成名。创作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回报也是对等的。在中国没有落魄潦倒的作家,如果他真是一个作家的话。作家这个职业是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自由是最大的驱动力,财富也并不会比一般人少,你说的那些应该是极少数。”
至于我的未来,我只能这样回答他,未来太遥远,我无法把握,我只是把现在的每一件事情尽力做好。这件事情就是写作。
是的,这是我惟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