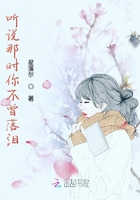“……正是幽人叹幽独,东邻携酒来茅屋~怜予病窜伶仃愁,自言新酿秋泉曲~”
一大清早,南河头一带的镇民都听到了船上一个男子的歌声,唱的词儿没人能懂,却又凄凄惨惨的,扰得人恨不得从窗口扔个擀面棍子下去。
“三哥好雅兴。”一个青年长身玉立,站在岸上,看着船上翘脚躺着的男人,呵呵一笑,嗖的一声就跳上了小船,而船身连晃都没晃一下。
“秋彦还好吧?”男人坐起身子,随手撑了一把船橹,小船就离了岸,摇摇晃晃地顺着和缓的水流淌起来。不过这小渠不宽,就算在水中央摇船,凭张明远的轻身功夫,要跳回岸上也不难。
“你倒是记挂他。”
“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久些。”刘仙伶盘腿坐在船上,随着船身的摇晃而左右摇晃着,似乎还没从昨日的酒意中醒转过来。引得张明远迷惑不解,昨日的酒又不是什么烈酒,而这落拓渔人似乎也没喝多少。
“你这人,唉!”张明远一时语塞,又想起昨日的惊险,不禁叹气,“秋彦他刚回来就出这种事情,真是欺我江湖无人吗!”
“呵!”刘三儿发出一声轻笑,对张少爷的话不置一语。
“要是放在过去,有桃庵花客那些前辈们执掌镇子,哪里容得下宵小妄为?!”
“桃庵花客?”刘三儿饶有兴致地眯起了眼睛。
“刘三哥也听过的吧?就算是外乡人,只要是混过江湖的,都该听过桃庵花客的名号。那时候反清复明的志士可不止有洪门三合会那帮子人。”张明远是张家外室生的庶子,这几年才被找回来当少爷,身上还带着挺重的江湖气。
张家是本地望族,本来和莫家的势力一文一武不相上下,可是在清初那会儿,江浙的文人遭到打击,便逐渐没落了,倒是莫家仗着跟道上的朋友有些交情,祖传了一套“凌寒掌”威力甚大,在镇上长立不倒。所以近年来,张家督促这族中子弟习武,某种意义上倒也重拾了正统儒家的六艺之学,不光是在诗文上下功夫了。
也就一瞬间工夫,刘仙伶就兴趣缺缺地重新躺下,瞌睡朦胧地拿脚摇着橹,把船摇出了南河头,也不知道是要往哪边去。
“听过,风二爷、江南剑侠傅白鹤,当年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呵呵。”
“对啊,刘三哥你方才所唱的便是当年孤云子前辈常常吟唱的《醉义歌》嘛!”张明远笑了。在桃庵花客中最著名的还是当年那七个发起人,人称“桃庵七客”,其中,张二少爷最欣赏的便是那孤云道人孤云子。此人是个汉人道士,却唯爱一个契丹僧人的诗,便是这首《醉义歌》,在反清复明的时代潮流下显得尤为突兀率性。听说当年此人有双绝,剑是一绝,而这诗亦是一绝。张明远到底是出身文人世家,虽说算是半个游侠儿,却始终放不下一个“诗”字,平日里自己也没少作诗,在镇上还是享有才子之名的。
刘仙伶懒得说什么,岸上一个青年却是帮了他这个忙,把张明远那喋喋不休的劲头给打断了。
“明远,你也是去看秋彦的吧?让我搭个船。”说着,自说自话地就跃上了刘三儿的小船,惹得船身直晃。
见那青年上船,张明远有些不知所措起来,毕竟这是刘三儿的船,不是他随手雇来的。不过刘仙伶并不打算是给自己正名,任由那青年把自己当成普通船夫,不用听张少爷扯淡了,也乐得自在。
“苏兄,这船是刘三哥的。”张明远本性率直,不会拐弯,“三哥是我朋友。”
“朋友?”青年的名字叫苏晓云,是当地望族苏家的独子,看到刘仙伶一身灰衣虽然干净,但显破旧,而其人又是一派船夫的作风,不由皱眉,不解地望向张明远,也是希望他给个解释,怎么和这等“人物”交起朋友来了。
“苏晓云!”张明远不由望向刘仙伶,后者笑盈盈地坐在船尾,扶着橹,将下巴靠在上面,似乎没有介意苏大公子话语中带的轻视之情。
……
江南秋色,却不如北国肃杀,只有一份有意无意便能略过不提的悲凉。
莫家的正门在南河头的青石路深处,常年紧闭。就算是公子太太们也只能走那道偏门,至于仆人们,就只能走另一扇开在大街的后门了。
梧桐树的落叶从院中飘出来,泛着一丝秋雨的腐臭。
不过,因为偷摸出门而溜回家的莫二少爷来说,走后门才不会被那死板的老头撞见。可是莫兰臣千算万算还是算漏了一点,他那喜欢和下人们走在一起的大哥也爱走后门。
“二弟?”莫松臣看到这个比自己更讨父亲喜爱的二弟鬼鬼祟祟走在这里,先是惊讶了一下,然而他很快也想到了缘由,便恢复了平静,“你回来了,父亲正在找你呢。”
“找我?”莫兰臣皱紧了眉头,这几日本该留在家中为大哥接风洗尘的他却是日日往外跑,老爹莫正梅怕是不会轻易饶过了他。
“他现在人就在退厅,你去请个安吧。他并未恼你外出,只是似乎有要事相商。”莫松臣岂会不知二弟心中所虑,开口安慰道。
“知道了。”莫兰臣点点头,硬着头皮往里走。他没有注意到,大哥的身后站着一个人——莫家的管家笛叔。
“大少爷,老爷他找二少爷怕是要谈下一任家主之事……”笛叔的话语中透着不满。
“咱们还是快去福禄钱庄吧,去晚了,钱老板又要念叨我半日。”莫松臣何尝不知父亲的意思,可是,继承家业终不是他所想,如今父亲看重二弟,也算是断了他这些歪心思。
“大少爷!”笛叔可不这么想,见自家大少爷顾左右而言他,心里直骂他扶不起的阿斗,“二少爷武功再好也只是次子,您是莫家的嫡长子,长子不孝才立次子,如今老爷要立兰二少爷为继承人,那是当面扇您耳瓜子啊!您又没有不孝,反而在上海滩上办起了几处实业,也算是镇里半个有头脸的人物了,您要是有争取的心思,哪有他二少爷什么事?”
“嘿,笛叔,别说了。”莫松臣讪笑,“莫家祖祖辈辈都是武人,我身为大少爷却半点功夫也不会,哪能当这个家?二弟性格豪迈行事任侠,颇有父亲当年之风,他来当这个家,再适合不过了。咱们还是快去钱庄吧。”
笛叔无奈,只得出门喊了个小厮撑出条小船来。
此时的江南,小舟还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至于轿子什么的,只有重大场合才用。
——
邹家在城西有一处偏宅,邹二少爷自从在鹦鹉楼受了惊,就给安排在此处休养,守在院门前的那些下人个个神情肃穆,像是死了老婆似的。
“张少爷又来瞧我们家二少爷啦?”原本那守门的小伙子拿着根棍子满脸警戒,见来人中有个张明远,立即眉开眼笑起来。看来这张明远在邹府的下人们当中挺受欢迎。
“朱二,二少爷他今日可好些了?”张明远笑问。
“哎,二少爷是没事,不过大太太可是吓得不轻,死活要二少爷在此地住一阵子,虽说我们做下人的不该在背后说主子闲话,不过二少爷又不是小娃娃,这不是把他给禁足了么?!”
苏晓云走在张明远身后,这会儿闪了出来,略带不满道:“既然知道不该嚼舌头就别乱说话,明远,咱们快进去吧。”
张明远知晓苏少爷的脾性,知道他无甚恶意,就是眼光高些,嘴巴毒点,于是便迎着朱二惊讶的表情,冲他耸耸肩,把缩在路边树旁不愿近前的刘三儿也拉进了这所宅子。
因为只是一处偏宅,院子不大,三人很快便瞧见了邹秋彦满脸落寞地坐在一颗杏树下面,手里捏着一封已经拆了蜡封的信。
“秋彦!”张少爷冒冒失失地喊了一声,那边邹二少爷听得立即转过了头来,却忘了擦掉眼角的一颗泪珠子。
“你?!”就算知道邹秋彦为人软弱,可是当着大伙儿的面掉泪,那可不是他干得出来的事儿,是以连苏晓云也大为震惊。
“没事没事,沙子迷了眼……哎哟!”小少爷慌乱地揉眼睛,手中那信一个没留神便掉到地上去了,落在一地金黄的落叶上面。
一直为人无视的刘三儿俯身捡起那信,一眼也没瞧,还给了邹二少。惹得张、苏二人都好奇地凑过去了,又只能不尴不尬地缩回来。
“是……师姐的信……”
“消息竟然传得如此之快,衡山已经知道你遇刺了?!”张明远微微动容。
“不,不是的,还不知道……”邹秋彦悻悻地低下头,张少爷是镇上有名的风流才子,自然已经猜到了缘故,奈何苏晓云家教甚严不苟言笑,还坠在云雾里,不解地望着两人,瞧得邹秋彦的脸蛋都能炒鸡蛋了。
三位少爷聊着聊着便忘记了招呼刘仙伶,他也没想跟少爷们搭上伙,自己七转八转地就转出了院子,翻墙走了。若是问他干嘛不好好走正门,这里头还真有讲究,正门没开在水边,他这懒胚子便不愿多走那几步路才回他的小船。撑走了小船,那两位少爷要回府,可要自己雇船了。
“刘三郎,刘三郎,撑着小船乘风凉~喝花酒,补渔网,甩着鱼钩钓姑娘~~”
几日后,刘三儿捡来个小娃娃给他当渔童,那小娃娃唤作“小源”,不过四五岁年纪却生的机灵,每隔一日便帮着刘三儿到酒伯那儿去打些酒回来,顺道还学来一首也不知是谁编的童谣,张了小嘴满船唱着,恼得刘三儿直拿指头弹他脑瓜子。
“叫你学!叫你唱!今朝你就别想吃晚饭了!!”
“刘三郎,刘三郎,撑着小船乘风凉~喝花酒,补渔网,甩着鱼钩钓姑娘~~”
这一回,却是岸上一群放了私塾的小鬼边扮鬼脸边尖声尖气地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