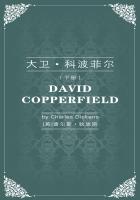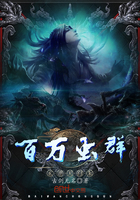凤姐一听,登时放下脸来,立着眉毛问道:“你这话说给谁听?可着你的小老婆养不出孩子来,你倒寻趁上了我?”见贾琏懊恼难言,复又坐下道:“二爷之行,真真令我心寒之极!看此光景,我纵然为这府里操碎了心,熬干了油,你们也并不知情。就算我平日苦心劝你,也不过为的是你自己保重身体,谨慎事务!饶你们在外面做了没脸的事,自己搪不过去了,就都一起按着我的头,弄一堆烂鱼头来让我择,现在把事情给你们办妥当了,我的金的银的也都搭进去了,不但不知感悔,反倒这样一副嘴脸!真正苍天在上,我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我,不知上天如何发落你!”贾琏听了,愈发口讷语塞,太阳穴里几要迸出火星来。半日,说道:“先不要理论这些是是非非,还是先支些银子出来,秋桐那里等着看病调养。”凤姐一听,炮燥难禁,气火攻心,嚷道:“钱我一个也没有!这府里的情况难道二爷是不知道的?这里是事,那里也是事,接接连连的都是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前阵子光为宫里打的饥荒,我还不知道怎么填呢!既是秋桐有事,二爷就该自己想法子解决。我倒是有心把自己的体己拿出来,又怕落人口实,说我心虚害了人命,所以拿钱填补!既这样,索性不管,大家干净!”贾琏气的血冲囟门,指着凤姐的脸道:“你!怨不得人人都说,霸着那么多钱,真准备都带进棺材里花去?”
凤姐满脸紫涨,冲着贾琏一口啐了过去,大骂起来:“呸!我如今就差你来咒了!我趁着金山银海,不是你的,爱怎么使就怎么使!我又没偷人养汉,包娼聚麇,倒怕人说?天底下有你这样没脸的男人!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不管什么脏的烂的,腥的臭的,见了就再不放过!真成了一只喂不饱的狗了!狗也比你体面些!成日里调三窝四,欺天犯上,可惜这五六品的顶带给了你!自己背伦常,没止行,弄的鬼神皆愤,连个儿子也不让你留下!现在倒来混讹我,我还要找你算算这账呢!你们以为什么狐狸不是狐狸耗子不是耗子的东西,都可以大摇大摆的坐在屋里头充主子,也得有那个命才行!可是常言说的‘鬼神暗察,丝毫不漏’,你们还自以为暗地里做的巧,便宜快畅呢,那知祸报一朝斩绝——老天偏绝了你的!又怎知不是你们自己耗损阴德太过,难逃祸罚,是你们自绝的!若不亏我命大,一个正经后代你也别妄想!你还敢来讹上了我!”
贾琏直气的三尸神咋,浑身血液漫过胸膛如海涌,冲开顶门似汪洋,猛擂一阵桌子,一把揪起桌布掀翻过去。可怜上面那些玉盅珍碗,登时碎的碎,残的残,滴溜溜滚了一地。凤姐赶上来,一顿乱脚助力,又踏了个碎上加碎。贾琏血眼猩红,举拳要打,早慌得平儿跪在了地上,一把抱住求饶不迭:“二爷好歹消消气,这原不干奶奶的事!况奶奶的身子也才刚好了,又连日连夜的为府里诸事忙碌操持,老太太、太太才看着高兴了些,太太才把身上的担子卸了一大半去。二爷要是心里有气,就打我吧,我愿意替奶奶让二爷出气!”凤姐凛凛扬着头,喝道:“平儿起来,这儿没你的事!让他只管冲着我来!明儿也好让满府的人都知道知道,你琏二爷为小老婆养不出孩子来,竟要谋杀元配呢!”贾琏听了,气的再也无法,劈手甩开平儿,一脚踹开房门,自顾飞也似的去了。
且说贾琏去后,不免想法凑措银两,为秋桐请医调治。一面命人严刑拷打善姐。谁知那善姐被打的死去活来,仍只一口咬定原来的话不变。后来贾琏打的自己也没了办法,只好暂时撂开了。偏贾母又知道了这事,乃命人叫了贾琏来,说:“那尤二姐生前就偏狭善妒,连凤丫头那样好心待他,他反生出一片歹意来。以前秋桐多少回到我跟前告状,我还都记着。况且素闻他和秋桐两个争宠邀幸,一向不睦,至死挟怨。他生前没生出一男半女来,今见秋桐有了身孕,想必那魂灵儿也是嫉妒的。论理,他已经殁了的人,不该再这样说他,既说出来,也不怕你恼。我想那善姐断无说谎害人之理,还是不要过于折磨冤屈了他才好。况且,又逢这样大喜日子,何苦乐得不施恩呢?”贾琏听了,再无他法,只得回去命人把善姐放了,不提。
谁知过了几日,又有喜事接连传来:原来今年京察,工部保举贾政,圣上念其清操廉洁,优先升放了江西粮道外任。史鼎亦连连升迁,不日便要复调回京了。贾母闻知消息,十分喜悦,知是托元春之福,因望着西北方向默祷一阵,遂吩咐鸳鸯等人:“赶快预备着大家庆贺一番才是,快把凤丫头找来!”谁知话音未落,就见凤姐笑嘻嘻的走进来问道:“老祖宗,什么事儿,这么勾魂儿似的找我?”贾母见了他,笑的浑身直颤,乃对鸳鸯、琥珀等人说:“你们看看这个猴儿,怎么他就象是打那地底下钻出来的似的?亏着我没说他的坏话。”众人都笑了。凤姐蹭上去说道:“老祖宗不知道,因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边,老祖宗这里才冒出个念头来,我就在那边感应着了,再不敢耽搁,连忙放开跟前的一切,就跑来了。只恨不会孙大圣的神通变化罢了,不然早驾着风就来了,还等到这会子呢!”贾母听了,愈发笑个不住,因说道:“看把你能的!既这么说,那还问我做什么,你自然知道我为什么事叫你来了。”凤姐嘬着嘴,故意掐了一回指,笑道:“想必是为了给老爷饯行的事,才拘了我来的罢?”怄的鸳鸯、琥珀等都笑个不了,贾母笑着用手指着他,且说不出话来。半日,方商议起正事来。
且说宝玉这日别了卫若兰回来,见袭人、碧痕、秋纹等几个人埋头在一堆五彩丝线里云组色,因问做什么,袭人说:“紫鹃绣的那幅《丹枫呦鹿》,眼看绣完了,缺了几样颜色,林姑娘才打发了人到这边来问有没有。这不正给找呢么?”碧痕边找边叹息道:“阿弥陀佛,真正要的稀奇颜色!又要象宝石一样的青绿色,又要丹黄掩映的云霞色,又要明丽的宝蓝色中带着灿烂的枫叶色,真正只有林姑娘这样慧心巧智的人能说的出来罢了!”宝玉听说,便上前帮着接线、挑选了一番。一时,跟了黛玉派来的那小丫头同往潇湘馆来。一进门,只觉香风馥馥扑面而来,却见湘云、宝琴、李纹、李绮、喜鸾、四姐几个,或坐或立于长案四周,看黛玉调琴。案正中置一荷塘清趣大茶海,案台上摆着两只八瓣花形有座果盘,一对儿绿地粉彩开光菊石茶碗,四只青花仙鹤茶盅,下面一律配着青花博古菊瓣花形碟。宝钗手里是一只珐琅彩胭脂红茶碗,平端待饮。李纨微侧着脸,与他轻声谈笑,杯中茶已将尽。茶海中有一长柄茶勺,雪雁操勺,复舀茶汤于李纨茶碗内。紫鹃仍埋头坐在暖阁里,临窗刺绣。那黛玉低头敛眉,凝神试弦。身上穿着石青色织金缎小袄,明黄掐牙滚边,领后忽而露出金焰垂绦,外罩着折枝花对襟,下摆一排流苏串珠,下面是冷蓝撒花棉绫裙。愈发显的冷若冰霜,艳若桃李。
众人见了宝玉,才要说笑,宝玉因怕扰了黛玉,连忙摆手示意不要出声,才要寻个地方坐下,那边早有喜鸾过来,推他坐在了自己的位子上。他自己则含笑立在一旁。宝玉因和他悄声说笑几句,又趁着机会,起身到暖阁内看了一回紫鹃的针黹。果然好一幅珍品:整幅画面婉缛明丽,林木丹黄掩映,灿烂如云霞,红叶在其间尤为艳丽显眼。群鹿或立或卧,或隐于林内,或逐于林际。居首一只有角雄鹿,似闻惊警,群鹿亦皆侧首注视一方。宝玉不觉浑身都端肃恭严起来,想要称赏,一时却想不出恰当的话来。
一时黛玉调琴毕,端身正座,抚琴一操。果然缠绵密切,激烈发扬,啸虎闻而不吼,哀猿听而忘啼。一曲才罢,众人称赏不绝。独宝玉又洒下泪来,因怕人看见,赶紧擦了。又劝黛玉道:“病才好些,很不该这样伤神。”又悄悄问雪雁,才吃的什么药。方又笑着对众人说:“咱们下一社,头一个题目就作《调琴啜茗》,可好?”宝钗笑着站起身来,摆着手道:“罢,罢!你们作去吧,我记性差,没的又让林妹妹臊一鼻子灰去。”说的众人都笑了,宝玉红了脸,说:“世上的事,原也难定,那见得事事总一个样,永远不变的?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明儿等我认真作起来,说不定还夺了魁呢!”李纨看着湘云,笑道:“从回回落第到夺魁,这一社倒是很值一等。”湘云拍着手道:“阿弥陀佛,周利盘陀伽要‘扫尘’、‘除垢’了!真正很值一等!”众人轰然大笑起来。喜鸾笑嘻嘻的凑近宝玉说:“二哥哥,赶明你们再作诗,我和四姐也来入社,可使得?”
众人便都看着他,笑问:“喜鸾妹妹也会作诗?”四姐在一旁笑道:“作不好还作不坏么?他要来入社,保证再没别人落第了。”说的大家又笑起来。喜鸾自己也不好意思了,因问着四姐道:“你这敢情是在向大家宣告,你作的一定就比我的好了?”四姐笑道:“我可从来没说过我会作诗,如果有人一定要拉着我也来入社,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既不会,也绝不敢冒充,我老老实实站在一旁给大家捧砚。”喜鸾笑嗤道:“看你这面目,给大家脱鞋或可将就。”众人一发笑个不了。一时笑定,宝琴道:“听了林姐姐的琴,我倒现成的有了一首古风。”众人听说,一力撺他快快写来,宝玉早自那厢取了纸墨笔砚来,只叫他念。却听宝琴道:
闲来一曲亦无聊,千古知音在九霄。
东海渔歌惊巨浪,平沙雁落唳春潮。
蕉窗夜雨梅三弄,箫鼓斜阳锦上花。
半醉且抛身外事,高山流水寄尘涯。
蓬莱春晓坚冰在,洞庭秋思梦犹寒。
古壁蛩声时断续,幽园鹤影久孤单。
龙城复忆莲台下,人去人归月色消。
前路不须神代引,炎凉世界自逍遥。
鸥鹭忘机归何处?寒鸭戏水也销魂。
莫道湘妃多血泪,人生更苦是长门。
乌啼螭困皆相散,凤倦龙潜各不还。
看尽风烟愁未尽,蟾光冷冷照千山。
众人不觉纷纷道妙称绝。宝玉一发赞个不了。倏忽已过了半日。忽不见了湘云和宝琴,黛玉便笑着唤小丫头们到山子后头的青石凳上去找,大家又笑了一回,方一起披裘抖氅的找了出来。不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