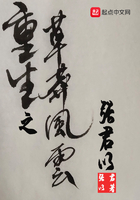陶端晋的妻子是个老实的农村妇女,见卓琳来到,顿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卓琳微笑着从书包里拿出一袋糖果、两斤饼干和一包水果,送到她手中,说道:“这些年,我们太麻烦你们了。”接着,卓琳感激地握着她的手又说:“我们要走了,今天是专门来看你们的,谢谢你们的关照。”
寒暄了一会儿,卓琳起身告辞,来到自己的“师傅”、亲密的女工友程红杏家中。
敲门声响过后,程红杏来开门,一看是卓琳,高兴地拉着她进门问:“什么风吹来了贵客?”
卓琳说:“这几年麻烦了‘师傅’,给我们帮了许多忙,还教会了我电工。这些好吃的送给你,表表我们的心。”
卓琳诚恳、朴实的话语,令程红杏坐立不安。
她一时高兴,忘了给客人倒水,却搬出一个陶罐,拿自制的冻米糖招待客人。卓琳拿起一块冻米糖放在嘴里,同激动的程红杏唠了一会儿,嘱咐她好好工作,要求上进,以后有机会时到北京去玩。
从程红杏家出来,卓琳又来到曾经照顾过邓朴方的女工缪发香家里。
原来,在邓小平和卓琳到江西一年多以后,下肢瘫痪的大儿子邓朴方也来到他们身边。于是,照料好邓朴方,成为邓小平夫妇的一项艰巨任务。
在困难之际,女工缪发香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邓小平夫妇照顾儿子,减轻了他们的压力,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因此,卓琳和邓小平对缪发香十分感激。
一进缪发香的家门,卓琳拉着缪发香的手说:
“这几年我们全家麻烦您了,今天我和孩子们代表老邓来谢谢您。”说着,她把一包糖塞到缪发香手里:“胖胖(邓朴方)今天不来了。这包糖是胖胖送给缪阿姨的。”
“我没做什么呀。”缪发香紧紧握着卓琳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
就这样,卓琳把真诚的情谊送到了一个个工人师傅的家里。
说不尽的深情厚意
1977年盛夏的一天,北京。
夜深了,喧闹的大街安静下来,人们渐渐进入梦乡。
地安门东大街的一所四合院里,一间书房却亮起了灯光。
灯下,一位年近6旬的老人,戴着老花眼镜,坐在写字台前铺开一叠信笺,正在写信。她,就是卓琳。
前些天,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负责人熊廷禄出差途经北京,给邓小平、卓琳写了一封信。
邓小平见信后,写上委托卓琳代他去看望。
待卓琳赶到时,熊廷禄已经离京了。为此,卓琳深感遗憾。
想起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工人师傅,卓琳的心情就不平静,和他们共同劳动、生活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尤其是工人师傅们对邓小平和她的爱戴之情,使她感动不已。此时此刻,她内心翻腾着感情的波涛,拿起笔,给熊廷禄写了一封充满真挚情意的信:
熊廷禄同志:
这次你们来北京时给我们的信已收到,我本来打算要去看望你们,但一联系,说你们已走了?很遗憾,没有能看见你。
我们在你们厂的三年劳动学习中和广大工人和干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工人和干部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使我们感动难忘,每当提到那时情形,对你们总是十分惦念。为此请你代为转达,向他们问好!这次来京虽未能会见,你们如有什么事情和要求可以给我们写信。
最后祝你及全厂同志好!致革命的敬礼!
卓琳。
1977年7月12日。
邓小平和卓琳与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工人师傅们建立的感情是患难之情,弥足珍贵。
离开江西以后,他们一直没有忘记这些曾经与他们朝夕相处、对他们照顾有加的工人师傅,一直关心着工厂的各方面情况。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嘱咐来京开会的江西省委书记黄知真说:“你回去之后,应该扶持一下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增加一些基建投资,再新盖一个车间,工人生活,也要尽量地改善一下。”
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怀下,江西省拨给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一台大型机器和两部汽车,其中一部为厂用客车,供接送工人上下班之用。
后来,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负责人又带了几位同志出差到北京,邓小平得知后,连忙派秘书去看望,并再三询问厂里有什么要求。其间,邓榕还托江西的朋友,询问厂里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困难。
这些都是后话。
此时,邓榕见书房还亮着灯,也悄悄来到母亲身旁。看见母亲在给拖拉机修造厂的负责人写信,她也欣然提笔附言:
按照来信的当天即与你们联系,但你们已走了,很是遗憾。
这次你们来京,我父亲再次让我母亲去看望你们,又没看成。
我的父母对于你们厂和你们厂的广大工人和干部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也愿意表达自己的感情,但一直未有机会。
你们如有什么需要和要求,可来信,他们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致敬礼。
邓榕附笔。
7月12日。
信,写完了,母女俩会心地一笑,这才各自回房休息。
不久,这封带着邓小平一家人的关切与问候的信,越过千山万水,送到了熊廷禄和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工人们的手中。
可怜天下父母心
爱儿女,是人之常情。天下父母都有一颗牵挂儿女的心,卓琳、邓小平夫妇也不例外。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爆发,邓小平就被推向灾难的深渊。三年以后,林彪的“一号命令”,使夫妇二人离开中南海,下放江西劳动。离开北京时,不允许一个子女随行。卓琳作为五个孩子的母亲无限悲伤。她思念着成年与未成年以及被迫害致残的儿女,禁不住泪水涟涟。
作为父亲,邓小平的心中也有万般痛楚。同卓琳一样,他从心底里爱着聪明、活泼、富有朝气的儿女们。尤其在别离的时候,这种感情更强烈。因而,到达南昌,住进“将军楼”的第二天,他就主动向监管人员黄文华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说:“我来时,汪东兴同志同我谈过,同自己的亲属可以通信?”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又补充道:“还有第四、第五个孩子,我来南昌时未见面。第四个孩子(在陕西插队的邓榕),原约定12月到北京会面?其他的都见了面,现在可以不来。”
邓小平想把原定12月同女儿邓榕会面的地点,由北京改为南昌。
黄文华十分理解这种牵挂孩子的慈父心情。
他表示会尽快向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反映这一要求。
几天过去了,已经到了邓榕按原计划该到北京的时候了,答复却一直没有接到。
卓琳着急了,便同邓小平一起来到黄文华的房里。一进门,没等坐稳,她便滔滔不绝地倾诉自己的思念之情,并极力为儿女们的问题进行解释。
卓琳首先谈起大女儿邓林。邓林大学毕业了,却迟迟不给安排工作,还在挨造反派的整,没完没了地交待。应该让她到母亲身边来,用母亲安慰一下她那颗受伤的心。
卓琳建议说:“最好邓林12月底能来南昌。”停了一下又说:“她主要是受我们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中‘站错了队’,别的问题没有。她很老实,对毛泽东思想一直是信仰的?去年因闹派性,把她关起来了,一直关到今年3月才放出来?”
邓小平插话说:“邓林这个学校只有100多人,文化大革命她是个目标。过去北京大学1万多学生,连职工家属近4万人。这个学校一开始就有军代表。可能军代表不得力,也是几进几出。
后来还是毛主席派了8341部队的代表去,很快就转过来了。”
卓琳心情沉重地接过邓小平的话说:“听邓林说,每次去新的军代表,都要找她谈一次话,叫她写一次交待,真是交待得没有个完。”
母亲最了解女儿。卓琳又补充说:“这个女孩比较重感情。”
接下去,谈到邓榕。
卓琳向黄文华解释说:“邓榕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了很大刺激。她年纪轻,是个既懂事又不懂事的孩子,在学校读书时,政治上很积极,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我们被打倒了,她受的刺激就大了。”
诉说完毕,卓琳压抑的心情才略为轻松了一些。
回到家里,她心情不安地等待着。
12月26日,黄文华得到答复,正式通知邓小平、卓琳:“子女可以来这里,但江西省革委会不出证明联系。”
实在是捉弄人的感情。
卓琳听了,顿时泪如雨下。想到儿女们受父母的影响和牵连在运动中受到刺激和打击,邓小平和卓琳难以压抑悲愤的心情。尤其是卓琳,作为母亲心中更是酸楚难忍。
历史并非总是无情的。
不久,中央办公厅明确答复:邓小平的子女可以到江西探望。
这一喜讯,驱散了一些邓小平家中的抑郁空气,邓小平和卓琳脸上开始出现笑容。他们盼望着家人团聚的日子早点到来,盼望着子女们早点来到身边。
1970年春节前夕,远在陕西富县羊泉公社郭家大队插队劳动的小女儿邓榕最先到达父母身边。
刚一看见卓琳、邓小平,她就激动地喊着“妈妈!
爸爸!”跑着扑到父亲的怀里。
久别重逢,母亲卓琳更是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从此,孤零、冷清的“将军楼”里,不时传来邓榕清脆响亮的动人歌声。每当卓琳和邓小平从厂里劳动回来,未进家门,便先听到歌声,夫妻二人的劳累,顿时烟消云散。
然而,这歌声并没有能停留多久。两个月不到,邓榕便告别父母,回到陕西插队的地方去了。
继邓榕之后,1970年冬天,在山西省忻县奇村公社李村插队的小儿子邓质方,回到了父母身边。“文化大革命”初期,只有14岁的他,尤如一只孤雁在外漂零,被无情的风暴卷入运动中去,过早地品尝了家庭支离破碎,人各东西之苦。
望着离别两年的儿子个儿长高了,脸晒黑了,身体结实了,卓琳、邓小平心里充满了喜悦之情。
邓质方从小喜爱无线电,聪明上进,学习非常自觉、刻苦。父母很欣赏他爱学习的劲头。于是,鼓励他上大学深造。在黄文华等人的努力下,经批准,邓质方进了江西工学院。他果然不负父母的期望,学习成绩优异,成为班上的佼佼者。
几年后经考试,取得了出国留学的资格,并在国外学有所成。
最使卓琳、邓小平高兴的,是二女儿邓楠领来了她的未婚夫张宏。见到身体魁梧、仪表不凡的未来女婿,他们满心欢喜。这年月,竟有人敢爱“中国第二号走资派”的女儿,二位老人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
大女儿邓林是最晚回到父母身边的。她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画画得不错,因为受到邓小平的牵连,学校天天逼她交待问题,精神上受到长期的折磨。直到1971年冬天,她才得以来到江西。
儿女们因为父母的“问题”受到牵连,作父母的实在感到于心不安。卓琳和邓小平这时最惦念的,还是远在北京,已经瘫痪在床的大儿子邓朴方。
邓朴方原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害致残,外伤性截瘫,下肢废用性萎缩,完全直不起身来,只能躺在床上。
在那热衷于“革命”的年代,正常人尚不能正常地生活,更何况一个下半身完全瘫痪的残疾人?当卓琳、邓小平听到邓朴方栖身在北京清河救济院,靠编篾篓维持生计,日子苦不堪言的情况时,他们心如刀绞,万般难受。
邓小平铺开纸,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将残疾的孩子接回来,自己照顾。
信由汪东兴转交毛泽东。
邓小平的请求获准。邓朴方得以成行。
1971年元月,邓朴方来到江西。一到新建县望城岗步兵学校,坐在手摇车里的邓朴方加快速度向“将军楼”摇去。
父母闻讯,赶忙迎了上来。
见到日思夜想的儿子,卓琳、邓小平既激动又悲伤。原来活蹦乱跳的小伙子,现在瘫坐在轮椅上。对于作父母的来说,这残酷的现实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然而,他们要面对现实,用慈祥的父爱和温暖的母爱去抚平儿子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
晚上,卓琳、邓小平来到儿子的病榻前。邓朴方下肢瘫痪站不起来,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
他用手指着对父母说:“从胸口往下,都不是我的了,都没有知觉,我成了半截啦!”
卓琳和邓小平内心分外难受。他们帮助邓朴方脱下衣服,用毛巾一遍遍地擦抚他的肌肤,仔细地询问病情。此后,他们承担起护理儿子的重任,将全部的爱倾注在儿子身上。
夏天的南昌,气候炎热难熬。每天,卓琳和邓小平都要为邓朴方擦澡、翻身换衣服。卓琳先把水热好,然后组织全家人一起将邓朴方抬到洗澡间。邓小平的任务最重,是主要劳动力,既要帮助抬,又要给儿子擦胸擦背,常常累得满头大汗。
为了充实儿子的精神生活,卓琳把从北京家中带到江西的藏书送到邓朴方的床头,有《资治通鉴》、《二十四史》、马列经典着作、中外文学名着等等。
生活上,卓琳处处关心照顾儿子,实行“优待政策”,把自己家种的最好吃的菜,自己家的鸡下的蛋都留给他吃。
然而,儿子的病并没有好转,经常发高烧,肌体的各种剧痛不时地折磨着他。
看着痛苦难忍的儿子,卓琳的心颤抖着。她要为儿子解除病痛,并决定不惜一切地为儿子治病。于是,她和邓小平一起,就儿子的病情,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
1972年,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指示:邓朴方的病,还是请301医院来治。
不久,邓朴方在妹妹的陪伴下乘火车告别父母,回到北京住院。但是,由于江青一伙人的干扰,邓朴方到301医院后并没有及时得到应有的治疗。
1973年3月,卓琳、邓小平回到北京。刚安顿好,卓琳便赶到医院看望儿子。见儿子病体依旧,她有如万箭钻心。她听说上海骨科界有一些治疗截瘫病人的办法,便托人私下寻找合适的大夫。
到了1974年的夏天,一些医学界的专家陆续“解放”,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这时候,卓琳在一位姓章的中医世家子弟的秘密帮助下,收到了上海的来信。上海方面希望了解邓朴方的病情。
不久,两名高级骨科专家由上海来北京,和301医院的同仁共同为邓朴方会诊。
然而,太晚了。邓朴方的病由于原来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坏死的脊椎已经完全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了,这意味着他永远站不起来了,按当时国内医学界的条件,他只能长久地躺卧在床上。
命运又一次向邓朴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1979年的一天早晨,护士李大姐发现他的背后又鼓起了一个大包。
经医院检查,是脊椎再度骨折、断骨形成假关节,邓朴方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
当时的中国骨科界对此毫无办法,病人只能卧床等死。
卓琳禁不住哭了。
然而,作母亲的她并不死心。她仍在寻找为儿子治病的机会。
1980年,经过美国骨科学会主席马克斯博士的积极联系,国际骨科界着名的脊柱专家、加拿大的阿姆斯特朗教授表示愿意为邓朴方治疗。这个消息,由当时在美国学习的中国骨科专家吴之康带回北京,向卓琳转达。
邓朴方尚有生活的希望,卓琳听了异常高兴。
于是,邓朴方去加拿大治病一事,很快决定了。
为了帮助邓朴方赴加治病,卓琳特意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动员全家人凑钱。
9月底,全家人用凑好的钱,为邓朴方和护士李大姐买好了去加拿大渥太华的飞机票。
卓琳含泪送儿子到机场。她明白,这一去,儿子将接受生与死的考验。
闯过死亡之路的邓朴方,靠阿姆斯特朗教授为他植入的钢盘铁骨,重新坐起来了。几年后,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领导筹建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康复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