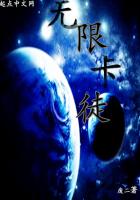艾琳从万福茶楼出来的时候,感觉有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自己,那双眼睛里射出的目光像两块黏黏的牛皮糖粘在她后背上,跟着她向前走了几步后,又跟着她上了一辆黄包车。艾琳始终没有回头,她知道那双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她有一种本能的直觉,这个人并不是日本特务,更像是军统的同志。她想他们的动作很快,明显已经开始对她进行调查了,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
艾琳坐的黄包车转上顺河街青石铺成的路面时,吴鹏刚好走到德生药房里间的布帘外面,他双脚并拢啪地来了个立正,毕恭毕敬喊了报告。里面传出一声轻咳,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让他进去。吴鹏掀起布帘走进去,在他身后,那块蓝底白花的布帘像一道瀑布似的落下来。
德生药房的里间屋依然摆着一张方桌和一把红木椅子,墙上也依然贴着华佗像,左边写着“妙手回春”,右边写着“华佗再世”,只不过坐在桌子后面的换成了一个面皮黄瘦的中年人。吴鹏再次双脚并拢,抬手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说:“处座好。”
军统情报五处处长陶天长了一双褐黄色的鹰眼,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用这双特殊的眼睛盯住别人的眼睛不放,直到对方慌乱地把目光移开时,他才把目光收回来,嘴角上不经意地露出一抹得意的微笑。陶天用鹰眼扫视一下吴鹏,然后从黄绸马褂的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用手在烟盒下面啪地弹一下,一支香烟像签筒里的竹签一样跳出来。陶天把烟拿在手上,一下连着一下向桌面上礅。他礅得咬牙切齿,似乎那根小小的香烟有着天大的重量,直到一端出现一段没有烟丝的空筒时,陶天才停下手,擦着一根火柴把烟点燃。没有烟丝的那段烟纸烧得很快,转眼变成了一截淡白色的灰烬。
陶天把那段灰烬吹掉,再次扫视一眼吴鹏说:“我正在派人对艾琳进行调查,你是她的顶头上司,请你谈谈对她的印象吧,有没有发现她私通共党的迹象?”
吴鹏说:
“报告处座,以卑职之见,艾琳不可能和共党有什么瓜葛,她一直都是效忠党国的。”陶天皱皱眉头说:“那为什么共党军队会出现在我们的阵地上,并且最终不劳而获打了个大胜仗?”吴鹏说:“这件事卑职也觉得有些奇怪,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并非是艾琳从中捣鬼,当初那个计划是她提出来的,如果不是上级临时下达撤退命令,那么,全歼日军的就应该是我们党国的军队,共党不可能坐享其成。”
陶天摆摆手,表示不想再争执下去,吸一口烟又说:“即使艾琳没有背叛党国,但她迟迟没有完成干掉季本尚的任务,总归是一种失职吧?”
吴鹏又一次行了个军礼说:“处座教训得对,卑职保证尽快解决这件事。”
这天晚上,钟鼓楼上的钟刚刚敲响过十二下,季本尚的雪佛兰轿车刚好驶进了万乐门的停车场。三楼舞厅里的艾琳显得非常兴奋,对所有邀请她的男士都来者不拒,淡绿色旗袍的身影一次次出现在舞池里。身穿一件黑色风衣的季本尚,则显得有些落寞,只是和南丽跳了一曲后就坐进了一把红绒面的椅子里,把衣领高高竖起来挡住自己的脸,默默地喝酒,就好像他当晚就是专为喝酒而来的。
艾琳在舞池里旋转起舞时注意到了那些监视的眼睛,它们就像某种肉食动物一样,目光里充满了残忍和贪婪,随时做好了致命一击的准备。艾琳知道,不管是日本特务还是军统,都已经按捺不住要对付季本尚了,但他们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抓人的。
艾琳和季本尚在舞会结束前才跳了第一曲舞。那是一支节奏舒缓的慢四步舞曲,他们跳得从容淡定,仿佛是在林间进行一次悠闲的漫步,似乎根本没有察觉周围危机四伏。乐曲结束时,艾琳拉着季本尚走进了化妆间。
几分钟后,身穿黑色风衣高高竖起衣领的季本尚从化妆间里匆匆走了出来,没有做任何停留,就直接下楼到了停车场,坐进了那辆雪佛兰汽车里。随即,汽车的引擎声响起,黑色轿车像箭一样射向大街上,梅机关跟踪的汽车随后追了上去。几辆汽车加足马力,在南城夜晚的街道上展开了追逐,就好像是在进行一场丛林中的围捕。十几分钟后,雪佛兰汽车在天地庙旁边的街口上被迫停了下来,梅机关的特务从车里跳下来,将雪佛兰团团包围,七八支乌黑的枪口对准了车门。
藤野绘里是最后一个走过来的,边走边摘下两只白色的手套,把它们像旗帜似的在手中摇晃,他的表情悠闲自在,就好像到这里参加一次正常的酒会。他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到汽车旁边,抬起手拉开车门,微微弯下身子,另一只手做了个向下的手势说:“请下车吧,季先生,游戏已经结束了。”
令他惊讶的是季本尚并没有从车里走下来,车后座一个男人怀里抱着一件黑色风衣,正浑身发抖地乞求饶命,嘴里不停地说:“不关我的事啊,不关我的事啊!”
藤野绘里一把将那人拉下车问:“你是什么人?季本尚在哪里?”
其实,不必发问他已经认出来,眼前的人是艾琳的黄包车夫老王,而季本尚却不翼而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