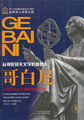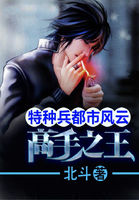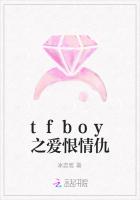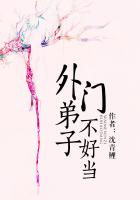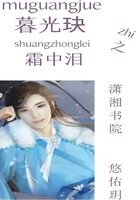1939年到1940年,徐悲鸿下南洋、赴印度,四处办展卖画,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筹款。在救亡图存的大潮中,一个艺术家,一不能扛枪,二不能上前线,他还能做什么呢?当我们采访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刘曦林时,他这样说道:“徐悲鸿是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有爱国心、爱民心的知识分子,这一点上,应该说对他的艺术的内在生命是非常重要的,他也适应了那个时代的思潮。”
此时的徐悲鸿已抛下儿女情长,一边作画,一边到南洋各地区举办画展,这些画展无不盛况空前。徐悲鸿将画展的全部收入捐献给国家,作为抗日烈士的抚恤金。徐悲鸿的这一义举激发了当地华人华侨的爱国热情,他们踊跃捐款买画,支援抗战。
徐悲鸿的儿子徐庆平回忆说:“我曾听他的一个朋友说过在当时南洋展览的盛况。虽然大部分同时代的友人都去世了,但是还有健在的。说当时画展上大家贴红条子,贴上红条子就是这张画已经卖了,你就不能再买了。但是他有好多画人家都喜欢,贴了好几个红条子在上面,那怎么办呢?他就马上再画,只要贴条子,贴四个条子他就再画三幅,贴五个条子他就再画四幅,就是为了抗战能尽多大的力量就尽多大的力量。所以新加坡人很骄傲地说,他们收藏的徐悲鸿的作品数量绝不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之下。”
为了筹集到更多抗日救亡的款项,徐悲鸿在新加坡客居期间,夜以继日地作画。但即便如此,他每天傍晚依然必做一件事。当时徐悲鸿住在新加坡一个朋友家里,朋友的后人后来告诉徐庆平,他曾亲眼看见每晚徐先生都会挑出不满意的画作烧掉,稍有点毛病的就全部烧掉。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徐悲鸿短短58年的一生,留在世上的作品大概只有3000多幅的原因:因为除了一部分毁于战火,还有数以万计的画作,是被他亲手烧掉的。
对自己如此严苛,就像当年把自己的名字从“寿康”改为“悲鸿”,又主动放弃蒋碧微一手置办的法式风格的奢华家园而深入到贫困山区写生作画一样,这也许就是徐悲鸿的执著和追求。
烧掉的那些画早已化为灰烬,而留在世上的却都是真正感染大众的精品。
《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创作于新加坡的其中一幅作品,它没有被烧掉,成为徐悲鸿流传后世的名作之一。
1939年10月,徐悲鸿在新加坡一个广场上看到知名女星王莹的一场街头演出,演的是田汉创作的独幕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剧本讲述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香姐”和父亲靠卖艺为生,又累又饿的“香姐”演不好,父亲就用鞭子抽打她,观众们以为“香姐”是老头买来卖艺的,便向他怒吼:“不许虐待孩子!”“放下你的鞭子!”“香姐”却告诉大家,这是她的亲生父亲,众人不再谩骂,但却感受到贫苦百姓在国破家亡的境遇中生存有多么的不易。徐悲鸿深受感动,邀请王莹做模特,以接近真人的比例,创作了这幅爱国题材油画巨作。
在当年徐悲鸿作品南洋巡展中,还有一幅巨幅画作震撼了许多观众,那就是徐悲鸿的名作《愚公移山》。直至今日,其感染力依然不减当年。
徐悲鸿构思这一作品时,国内的抗日战争正进入到最为惨烈的阶段。为了打通中国与外界的仅有的一条通道,方便抗日物资的输送,几十万中国军民凭借最简陋的工具,在中缅边境的高山峡谷、原始森林中,硬是凿出了一条滇缅公路。创作此画时,徐悲鸿正在印度讲学办画展,同时为著名诗人泰戈尔画像。他把创作《愚公移山》的想法告诉了泰戈尔,得到这位国际友人真诚的支持。印度大诗人立即着手安排他骑马前往喜马拉雅山写生采集素材。
1940年,在喜马拉雅山下的大吉岭,徐悲鸿开始了《愚公移山》的创作。他希望用这幅画来鼓舞国人齐心协力,同仇敌忾,战胜日寇。
对父亲的画作做过深入研究的徐庆平告诉我们:“徐悲鸿到欧洲学习了西方的人体表现之后,掌握大角度的透视的技法,《愚公移山》这张画,为了表现力度就要进行人体表现。我父亲说过,不管你是王侯将相还是乡野农夫,都是靠着那几根骨头,那几块肉,你才有锅可立,有酒可喝,有地可种。都是一样的,你就要把那几块肌肉和骨头表现出灵魂来,你这个画才能够有力量,才能够感动人。所以他在中国绘画中第一个引入这么具体的人体,用它来传达力度。人体如果在大角度透视下,他的力度更加空前。”
这种表现手法不禁让我们想起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米开朗基罗,他尤为擅长画人体,特别是大角度的人体,而且都是一些几乎令人想象不到的角度。在《愚公移山》中,当徐悲鸿描绘画中人物把水桶往前扔出去,锄地的人又以有力的动作抡锄头,无不表现出了空前的力度,这都是必须对大角度人体绘画技法具有大师级的把握才能做到的。为了在《愚公移山》中表现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仿佛让老天爷都受到感动,徐悲鸿大胆地使用了这种手法。因此,整幅画面全是大角度的人体,而且全是比真人还大的人体,表现力度空前。在这幅巨作中,徐悲鸿再次巧妙地将西画技法和中国传统题材相结合,真正实现了将历史绘画中国化,将中国绘画现代化。在那样一个抗日救亡的历史时期,一改中国画颓败的画风,甚至将画笔当成战斗的武器,具有极强的现实性。
在印度期间,徐悲鸿还留下了自己著名的人物肖像画《泰戈尔像》,这幅作品充分体现出了徐悲鸿在人物画领域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刘曦林说:“《泰戈尔像》,其白描的力度和线的力度被他强化得比《愚公移山》和《九方皋》还要好。也就是说他重复地肯定和认识到了任伯年的伟大。任伯年作为清朝末年的一个人物画大家,他的线条深刻影响了徐悲鸿,徐悲鸿又把素描的那一些对形体的塑造、结构的认识融合到中国画里边去。《泰戈尔像》还有背景的衬托,它用深色背景、山林背景来衬托人物肖像,而中国古代肖像画不是这样做的,它可以有山河的背景,但不是像这样用调子的对比来衬托的,徐悲鸿用深色来衬出浅色。他的成功之处就是坚守了中国画最本源的造型原则,又适度地吸收了西洋绘画的一些造型因素、光影因素、结构因素,这点很成功。”
1941年,徐悲鸿告别与自己甚为投缘的泰戈尔,离开印度。他先后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怡保、吉隆坡等地举办赈灾募捐画展。在经过怡保时,一位朋友盛情邀请他留宿家中。大画家一到,主人便拿出笔墨纸砚。徐庆平告诉我们:“我父亲管这种场合叫绑票。那么他肯定是出于某种原因必须给这个朋友画,他当时画了,使用的是新纸,而他从来不用新纸,都是使用旧纸。从来不用墨汁,更不用隔夜的墨。但是这一次,只有隔夜残墨,用的又是新纸,所以他专门在画上把它记下来了,说‘隔夜残墨,用是新纸,颇得意外之效,视可喜也’。”
这幅意外之作就是徐悲鸿的名作《牧牛图》。
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多次画牧童与牛,实际上正是在表达对和平的渴望和对童年生活的美好记忆。徐悲鸿作画从不用新纸和宿墨,他的新纸往往要在柜中放几年再用,画完画如剩墨较多,他会以大号毛笔书写对联,将墨用完,尽量不浪费。徐庆平继续回忆他在研究父亲作品时的发现:“这次作画用的是从来不用的最难用的工具,最不出效果的讨厌的东西,可是出了特别的效果。他画了一头牛,牛的毛是很粗糙的,他这个拉不开笔的墨正好表现那个牛,正合适,它是意外之效果,所以他没想到。画的那个人很简单就勾了一条线,他没有发挥水墨的功能,那发挥不了,那一画出来肯定难看得要命,你看得出来是用那个隔夜墨勾的,但是那张画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真的很奇特。”
原来,徐悲鸿通常会根据画作的需要,确定用什么笔。而他一般都用比较硬一点的笔,但是渲染的时候,要表现这个墨的那种酣畅的时候,徐悲鸿便用羊毫制的笔。如今身在海外,因条件所限,在使用自己不熟悉的作画工具的情况下,他凭借丰富的用水用墨经验,将令毛笔呆滞的宿墨用于画粗糙的牛身、牛尾和牛角,突出了质感。偶得佳作,徐悲鸿自是欢喜。徐庆平还发现此画的左上角有一个印,印上头有四个字,“这四个字我没认出来,确实太难认了,它不规范,不是规范的字,他又加了自己很多创造进去,我找了很多人来帮着认这个字,最后找了一个了不起的中国古文字学家,他的笔名叫大康,是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一辈子研究古文字。他把这四个字看出了,‘腐朽神奇’。这张画是用最差的材料,但是化腐朽为神奇,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据徐庆平介绍,在徐悲鸿的作品中他看到的仅此一幅画作上使用了“腐朽神奇”这一方印章。然而,在那战乱之中,一个画家能以单薄身躯团结南洋如此之多的华人,为抗战不知捐助了多少资金。赤子之心,当以绵薄之力报国,从这一点来看,徐悲鸿手中一支画笔不知幻化了多少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