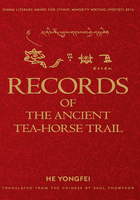在流逝的岁月里,这些战功赫赫的城守护着传统的农耕生活,以花岗岩般严厉的面孔随时准备将外侮拒之门外作为当时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对祖先土地的信仰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当王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向浩瀚的大海时,下意识选择的,通常是城,而不是船15世纪新航路被发现,掲开海洋时代的序幕。到16世纪,海洋贸易打破洲际阻碍,世界的经济互动开始打破传统模式而具有全球意义。东南沿海航海势力以漳州海商为主体,走到前台;欧洲航海势力-葡萄牙东进亚洲水域同时,日本的航海势力扬帆南下。几股东西方航海势力在中国东南海洋区域奔突冲撞。烟波浩渺的洋面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和银元的脆响。
当最具有海洋精神的一群人推动着中国成为海洋大国的时候,中国却遭遇到最不具备海洋精神的时段。
来自内陆安徽凤阳的一个破产农民子弟、皇觉寺的托钵侣僧朱元璋带着同样来自内陆省份的子弟兵取得了这个国家政权之后,宋元以来已形成的东南海洋经济到前有的破时,的序海明朝立国之初,昔日割据一方的张士诚、方国珍残部遁入海岛,对王朝统治的威胁似乎依然存在而东瀛岛国也进入混乱的战国时代,在1392年南北朝统一后失去领地的九州岛豪族开始以海为家,过四处劫掠的生活。15世纪,他们越过洋面南下,侵扰中国与朝鲜沿海,这就是为祸大明王朝和朝鲜李朝的“倭寇”。这两股力量,往往合流,相互勾结,一路攻杀,自辽东、山东到闽、浙、粤的滨海地区,年年如此。对于一个大陆帝国而言,这些骚扰并不构成对王朝统治根本的威胁,但是,来自两淮的这群新王朝的统治者,对于这些来自海洋的骚乱,近乎本能地断然采取激烈的反应。
他们必须用管理陆地的方法,来管理海洋。
既然保甲制度圈住了潜在的竞争对手们跃跃欲试的雄心,那么维系王朝统治的方略必将延伸到海洋。
即便到了若干年后,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在夺取了侄子在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地位之后,他所派出的那支宣扬皇威的巨大的舰队,依然保留这个陆上国的海洋理。
当永乐皇帝朱棣向印度洋和太平洋派出强大的舰队时,他的舰队指挥官郑和突然面对的是空荡荡的大海,欧洲人还没到达这里,所以,他合理地错过了一方的帝的是的治理的朝。
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朱元璋命令靖海侯吴桢籍、方国珍旧部和宁波兰山、秀山船户11万人,编入各卫军,严禁濒海民众私通外国。
洪武七年(1374),明、泉、广市舶司悉数关闭。
洪武十七年(1384)正月,信国公汤和巡视闽、浙,禁百姓入海捕鱼。自登、莱至浙沿海筑59城。
洪武二十年(1387),江夏侯周德兴到福建,又筑16城。
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玮又下诏,禁止民间用番香、番货,限3个月内销尽。
今天,漳州沿海由北而南,镇海、六鳌、悬钟、铜山4座军事要塞-明王朝江夏侯在漳州滨海构筑的第一道军事防线,无言地在21世纪的阳光下展露那中国人无法回避的海洋之痛。
在侵临大海的突出部,黑色的玄武岩和花岗岩托举下,那一座座曾令泛海而来的贼寇闻风丧胆的卫城,壮硕、阳刚、傲岸,仿佛是一群军容严整的老兵,虽然风沙磨走了岁月的模样,却依然坚守在岁月长河里枕戈待旦。
在流逝的岁月里,这些战功赫赫的城守护着传统的农耕生活,以花岗岩般严厉的面孔随时准备将外侮拒之门外。作为当时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对地的,王朝的海时,下意识选择的,通常是城,而不是船。
大明,这个秉承了前朝优秀的航海技术的帝国,统治者似乎天生与海无缘,帝国大得足够让一群马背英雄纵横驰骋。这种大陆思维主导的意识形态,至少持续到下一个王朝行将结束时,才开始改变。
大明律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丝锦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走漏事情者,斩……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往番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远充军……
海禁,这是中国海洋政策的一个巨大变化,在此之前,中国的政策是向海洋开的,在元,来海的。
新主人大明王朝却似乎热衷于做一件泽被子孙的大事,在北方边境修一道长墙,在东南沿海也修一道长墙,把所有的人圈在其中,这一切和万世江山、子女玉帛,都是夸耀天下的财富。
而这一切的主人,就像一个步入春年的家庭长者,身体壮旺,性格偏执,坐拥天下财富,警惕他人染指,包括那些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儿时伙伴、逃往大漠的蒙元残余和令人不悦的海岛诸夷。
曾经欲望燃烧的洋面突然遭遇到严冬。
那些中国最了不起的航海发明:罗盘、尾舵、多重桅杆,因为超越秩序,只能留给欧洲人去做地理大发现的航行,让哥伦布登上了美洲大陆,让麦哲伦越过好望角,让欧洲人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
为制止民间海外贸易,地方官员往往把奇思妙想发挥到极致。景泰四年(1453),一个叫谢骞的漳州知府,下令在月港、海沧随地编甲,本地人户,五日一点校。所有违制大船,一律拆散。海面上飘荡的那些五尺以下小船也要由官府打烙印才可出航,朝出暮归,犹如农家。
成化七年(1471),龙溪商人邱弘敏,前往满剌加和暹罗贸易,那是一次收获满满的旅程,船上甚至还载有暹罗王后赠送的珍宝。但是,不幸却发生在归航中,在家乡的门口,他们被官军捕获,除了当场杀死夕卜,跟随邱弘敏的29个人被处斩。随着大人上船的3个孩子,因为年幼,充军到广西边卫。那个曾经随邱弘敏出入暹罗王宫、安享过富贵荣耀的妻子冯氐,成了大明功臣的奴仆,开始了她供人驱遣的日子。
成化八年(1472),29个龙溪商人在海上遇风沉船,被官军捕获,除病死牢狱夕卜,14人被处斩。
15世纪,对于中国东南沿海世代以海为田的人们来说,似乎是一个前景黯淡的世纪。
这个世纪,北方长城以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姿势雄立,一个心怀远大的宦官率领上万赳赳武士,正在向海洋做告别演出,在整个东方,那色彩斑斓的舞台上上演的那一出海洋神话雄壮而近乎虚妄。
统治阶层的自高自大和对异族的疑惧与排斥,改写了一个秉承伟大文明的优秀民族的全部想象力和财富理念,那些经历过童年的饥饿与战争忧患而后渴望安享太平的帝国首领的潜意识,正在阉割一个走向开放的民族的灵魂并最终一点一滴地抹灭他们分享未来世界荣光的雄心。
16世纪成了一个航海大国的拐点。
一个国家在走向全盛时期突然告别海洋世界舞台,在后世的一片愕然中留下一个巨大的悬念。
在郑和的航线上,那些充满未来的光荣与危难的道路,留给了民间商人英雄。
两个世纪以后,当中华帝国的大门被西方海洋国家的炮火轰开,人们开始意识到,海洋,对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
16世纪的血色残阳
如果朝廷允许!他们乐意作一个体面的商人,用丰厚的奉献,换取家的平安如果君王寡恩!他们将泛海而去,追波逐浪本来就是他们的天性。当他们企望与朝廷建立一种比较和谐的关系时!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往往不是乌纱、不是田地!而是贸易的自由。
并不是所有的贸易热情,都将在皇家秩序下窒息。
尽管在16世纪来临前,大明王朝正迎来她的盛世光芒。
在它的东面,是浩瀚的大海,这片海域上游弋的,只是一些小邦国的帆船在西北,那是曾经征服世界的成吉思汗的后代帖木儿的领地,它已经向明王朝朝贡再往西,曾经辉煌的东罗马帝国已经崩溃,那个神话般壮丽的城市君士坦丁堡,成为土耳其人的新都遥远的欧洲,还没有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宗教纷争和战乱,使它四分五裂,黑死病曾经夺去它的大半人口;而印度已经衰落千年,在那里,一些勤奋的商人,正在营建一些离散社区,不久,它将沦为英国人的在新世纪曙光到来之前,整个世界似乎有些差强人意。
而亚欧大陆靠近太平洋的这块广阔的土地正在大明王朝的皇帝陛下和帝国精英的带领下,闪烁出农耕文明最耀眼的光芒,富庶、强大、势不可挡,正如那支伟大的郑和船队的横空出世。
此时,皇家秩序因为强大,不容动摇。
令人惊讶的是,千百年来一直默默地生活在中华版图和王朝政治权力边的一人,在个国为大横亘在这个国家从农业文明走向商业社会的那一道藩篱——皇家秩序,在有的战当生活在欧洲的君主们因为窘迫的财政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商人,并且索性和这些人一起成为海外扩张的玩家的时候,大明王朝的统治者则因为拥有欧洲君主们无以比拟的威权和物质力量而使国家不知不觉间负担起闭关自守的代价。明初中国政府的海洋政策发生逆转给沿海人民造成巨大的压力,以封闭、内向的海禁政策对待外来问题无疑使强势的封建文化中最脆弱的一面暴露殆尽。
就在帝国统治最脆弱的地带,漳州海商冲破牢笼成为东亚海域的主人,实现了与世界贸易体系的连接,他们在谋求不利于生存的海洋环境下的经济的开拓与发展的时候,自然而然成为现行秩序的反抗力量。
明人郑晓这么评价漳、认汀漳山广人稀,外寇内逋,与南赣声势联络。
海物利市,时起兵端。人悍嗜利、喜争,大抵漳州为劣在奉行儒家传统的道学人士看来,漳州人几乎就是奉行“温、良、恭、俭、让”风范的汉民族中的异数、封建正统眼皮底下的“刁民”。
数个世纪以前,第一批被他们的国家流放到澳大利亚的英国人似乎也是这类人。
作为中原文明在滨海之地的移民城市,漳州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互相渗透的一个中转站。作为曾经的蛮荒之地,它是农耕的汉民族和尚在游农阶段的山地畲族相互融合的一个舞台。
汉族文化中的异质成分在这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碰撞冲突,使这块海山的地、数。
唐朝,汉人与蛮獠在这里交相碰撞。
宋代,这是流亡政府抵抗兀政权的最后根据地。
元代,横扫亚欧大陆的蒙古铁骑在这里屡遭重创。
明初,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军队在这里面临挑战。
这个时期,漳州民间与封建王朝的关系有些令人跑尬。
洪武十四年(1381)十月,漳州府南靖县民暴动。
洪武十四年十二月,漳州府龙岩县民暴动。
洪武十五年(1382)二月,龙岩县民再次暴动。
洪武二十年(1387)九月,龙岩县民江志贤聚众作乱。
永乐十五年(1417)八月,龙溪县人佘马郎、龙岩县人樊承受与沙县、永春、德化人聚众作乱,抢劫龙溪银场。
宣德九年(1434)三月,漳州府龙溪县强贼六十余人往来龙溪、南靖劫掠。正统十二年(1447)闰四月,龙溪县池田敏等数百人四处抄掠。
与现代漳州人平和闲适的人文性格有所不同的是,数百年前,在民族融合的发展阶段,畲族强悍的民风和畳民来去自由的性格深刻地影响着漳州人的生活方式。这个群体在明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一个十分特殊的角色。
如果说,地形地貌、季风洋流决定了漳州海洋文化的走向,巨大的生存压力,也使人们十分现实地把目光伸向更为辽阔的空间。
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在人类拥有机械化穿凿能力之前,海路将是漳州最现实的对外通道。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千百年来,唐诗巨大的感染力使人们几乎忽略了或者比蜀道更难的闽道,与赣南、粤北连绵成势的闽西南,曾经是人迹罕至的人间秘境。甚至在最近的40年前,这一带依然被层层山峦分割成数量庞大的分散居民点,万山环抱,四面阻塞,春种秋收、自给自足、桃花源式的理想生活在这儿完全不是一种奢侈。
闽省山多地少,海商的巢穴海门岛,居民八十户,人口近四百人,靠两百亩地生存,最后田地被海水逐年侵蚀,再无产业。这四百人,除了贩私就是掠劫,此外还能做什么?丰饶的冲积平原,实际上被挤压在河口地带。本地产粮,不足以供应日渐庞大的人口,百姓口腹,仰仗潮州惠州、温州输入,粮船自浙江经海路进入漳州,可获利三倍,一年数百条的船运的规模,使粮食贸易成为一大产业。即使在本省,从漳泉两州贩货到省城,海运每100斤不过花费3分银子,如果被迫选择陆路,开支一下子增加20倍。海路,实际上是漳州的生命线。
明王朝在东南沿海实行海禁政策,对闽浙两省的影响是全然不同的。浙江一带,沿海百姓有鱼盐之利,海洋肃清,百姓一样可以聊生。而在漳泉一带,百姓口粮全仗外省供给,断了海路,米价暴涨,实际上断了是漳州人的活路。
正因为如此,朝廷三令五申与百姓铤而走险,成了明代社会生活的一道血色奇观。
人们成群结队走向大海’最初或许仅仅为了生存,但是,当人们从海洋贸易中转瞬获取十倍利润时,大海的诱惑力就更强大了。
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二月至二十六年(1547)三月,两年多时间内,因为贩海贸易被飓风吹往朝鲜而被押解回国的福建人就达一千多人,其中漳州商人占了一大部分。
等待这些人的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而更多的人正穿越风暴到达彼岸,依靠非法的营生,为自己和族人带来富足而危险的生活。
在漳州河口及周边地区,通番贸易成了家族性、区域性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它造就了无视禁令、追逐利润的海洋商业群体,也造就了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一群人。
有人说,这些汉民族中的异质,有北方移民的进取心、山地民族的强悍和航海族群的自由秉性,在巨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下,这些人身体内部潜伏的不安的基因,正在发出耀眼的光芒。
如果朝廷允许,他们乐意作一个体面的商人,用丰厚的奉献,换取一家的平安如果君王寡恩,他们将泛海而去,追波逐浪本来就是他们的天性。当他们企望与朝廷建立一种比较和谐的关系时,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往往不是乌纱、不是田地,而是贸易的自由。
就这样,历史上所谓的海寇商人出现了。在西方舰队突入中国东南海域、并且把贸易推进到东南沿海的时候,民间海洋力量超越政府海军和那一条脆弱不堪的海洋防线,与西方航海者逐鹿海上。
贸易战争、合纵连横,海商们掀起了太平洋的惊涛骇浪以及数百年的是底彻人的跃丧失话语权,在历史的暗角,漳州海商仿佛选择沉默,将是是非非留待他人评说。
500年后,邵峰——个虚拟的中国海盗首领和他的队伍在《加勒比海盗——世界尽头》中,被强势的好莱坞电影文化刻画成怪异、凶残、狡诈的一群人,和封建王朝的描述如出一辙。
这就是16世纪血色夕阳下漳州海商的绮丽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