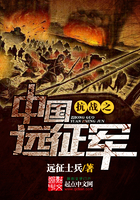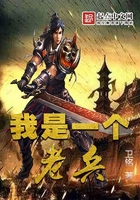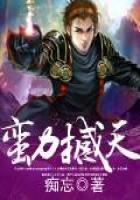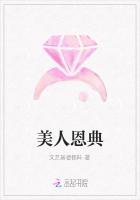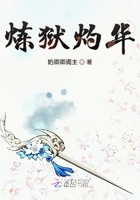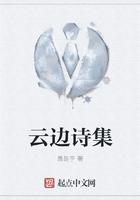裂缝的情形,与作战时的阵形排列相类似。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作战阵形必然要能够确保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火力线,以此火力线为临时依托前进和防守。即便是在古代进行的骑兵交锋,通常也需要由适当数量的步兵配合,这样做正是为了防止给敌军造成可乘之空隙。交战双方纯粹的骑兵对决或者装甲战,通常也会是在对敌军的快速攻击中实现火力线的构筑的,因为快速攻击行动本身已经吸引了敌军的注意力,至于一些军队所故意漏中的缝隙,其目的则是为了引诱敌人进入圈套之中,而一旦这一目的实现,就会立即生成一道对敌军来说难以逾越的弯曲火力线。根据地中避免产生裂缝,其目的也正是为了不给敌人以可乘之空隙。
同时进行力量的创造、维持和使用,这并不是我所说的周期重叠。所谓的周期重叠,具体指的是力量的创造、维持和使用这三个环节重复进行、缺乏协调。现在的力量可以随时投入使用,投入使用的力量可以随时得到补充,投入前线的力量可以随时从力量创造基地进行补充,这样的力量循环系统是密不透风的。但是,在此过程中,由于缺乏协调而必然会导致力量循环系统出现庸肿以致于不堪重负最终崩溃。
无论周期脱节还是周期重叠,事实上者是因为力量的产生、维持和使用这三个环节之间缺乏协调,所不同的是两种缺乏协调的情形刚好彼此对立。
最为理想的状态,是力量产生的速度刚好顶得住使用消耗的速度,力量维持的速度刚好能够承接起力量的补充和投入速度,这样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彼此衔接、协调一致,既可以避免出现脱节、同时又可以保持力量循环系统本身的健康状态。但是,在实际的情形中,这种理论上的最佳状态是极难实现的,不过所有想要保持力量循环系统顺利进行的根据地,都在事实上不断地接近于这种最佳状态。
德国入侵苏联
德国之所以在对苏战争后期难以有所进展,是因为它的战略资源已经消耗殆尽,而苏联之所以在这一阶段难以迅速地驱逐德国人,则是因为其战略基础在战争初期遭到了德国军队的严重破坏。
直到1942年11月苏军终于遏制住了德军的攻势之时,苏联在波罗的海以东、高加索以西、黑海沿岸以北包括东欧平原在内的大片土地沦陷于德军之手,在德军的疯狂进攻下,苏联被破坏的城镇数目高达1700多个,同时还有7万多个村庄废弃,此外,约3万多个工业企业、6万5千公里的铁路以及10万多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被毁。尽管如此,由于苏联的人力资源、国土面积与自然资源规模实在是太过庞大,因此在斯大林被迫将苏联靠近西线的许多工业基地转移到东部地区之后,苏联仍然能够创造出巨大的战争力量。
美国的战略基础
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最终获益最大的胜利者,首要的原由即在于它在本土的战略基础没有受到破坏,不仅如此,由于美国人将其战场维持在大洋对岸的欧洲大陆和西北太平洋之上,这其实反过来又大大扩展了其战略基础的范围和对象。
美国的地理条件肯定不是保障其战略基础的唯一原由,因为同样处于离岸岛国地位的英国就因战争而变得精疲力竭。
权谋之争、间接路线与正面接触关系,所关注的焦点都是既有的力量和力量如何使用,这两种声音争吵不休的同时,另一种更关注力量如何产生的战略思想问世了,它更加强调支撑起国家现有的实力与地位的基础条件,因而我们称之为战略基础派。尽管在前人的著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关注了战略基础即力量的产生这一环节,然而真正将战略基础当成是其论述核心的则要属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了。
保罗?肯尼迪与《大国的兴衰》
经济基础支撑军事力量、军事战争刺激经济发展
保罗?肯尼迪在一开始就点明,该书“重点是描绘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与战略的相互影响。”正因为如此,“本书副标题所讲的‘军事冲突’总是与‘经济变化’联系起来考查”。大国的兴衰不仅仅是其军队作战的结果也同时是其经济资源的利用结果,“在这一时期,任何大国的胜利或崩溃,一般地都是其武装部队长期作战的结果;但也不仅如此,它也是各国在战时能否有效地利用本国可用于生产的经济资源的结果。进一步说,从历史背景上看,也是由于在实际冲突发生以前数十年间,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与其他一流国家相比是上升还是下降所致。”
一流国家因其国力增长速度与技术、组织变革的不同而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以帆船为动力的远洋炮艇与大西洋贸易给西欧各国带来巨大的力量与财富之后,“后来开发的蒸汽动力及其依赖的煤炭和金属资源,大大增加了一些国家的力量。一些国家的生产力一旦得到提高,便自然能比较容易地在平时承受大规模扩军备战的负担,能在战时保持和供养庞大的陆军和舰队。”尽管保罗?肯尼迪也想到了这种说法会给人以重商主义印象,“但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在军事上过度扩张而它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困境,并且如果此时它的经济也正处于衰退地位,那么这种衰退困境就只会变得更加严重。
保罗?肯尼迪认为经济资源是军事力量的基础,但是他并不认为经济与军事之间的是经济支撑军事这种单向度的关系,因为军事力量的不断使用也同时会刺激技术、组织的变革从而导致经济力量的增长。在对比了东方国家虽然规模庞大却深受中央集权体制之害后,保罗?肯尼迪指出,“在欧洲由于没有东方式的最高权力机构,各王国和城邦之间争战不已,这就推动人们经常寻求军事变革。军事变革又有力地推动了在竞争、积极进取的环境中出现的科学技术与商业贸易的发展。”而欧洲社会又因为在变革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较小,因而“很顺利地进入了持续向上的螺旋式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军事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