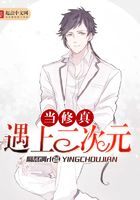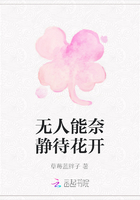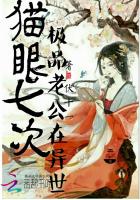虚实篇第六:
“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
军争篇第七: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
九变篇第八: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行军篇第九:
“兵非贵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对此,我只能说,数量从来都不是过时的因素,即便是在今天军事技术突飞猛进、异常发达的时代中也是如此。
九地篇第十一:
“故为兵之事,在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是谓巧能成事。”
为了躲避敌人的锋芒而我方就必须隐藏自己,而为了打击敌人我方就必然要主动出击给敌人以重创,将出动出击的情形建立在我方隐藏自身的等待过程之中,所以由此而得出的观点就变成了畸形的产儿,在敌人来势汹汹而敌我实力相当的时候迎头痛击往往是最佳的选择。
学习兵法而不可拘泥于兵法,这是因为书本中的兵法本身已经不能适应现实战争的需要了。崇尚谋略而尽力回避正面作战,这就是《孙子兵法》中的思维模式。
《孙子兵法》在最初传入日本之后,是被某些上层的统治人物当成是兵法秘笈而禁止在社会上流传的,他们的这种做法使得《孙子兵法》最初在日本人的眼中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儒家将《论语》奉为圭皋,宋朝开国宰相赵普更是声称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然而完全以儒家的学说来治国却行不通;法家以《韩非子》为经典著作,但是完全施行法家学说的秦帝国在短暂的统一之后却迅速灭亡;基督徒将《圣经》当成是他们至高无上的教义表述,但是不同教派对于《圣经》的释义却大不相同甚至水火不容。这并不是说信奉各种经典著作的人不懂得如何施行经典教义,而是因为他们所信奉的经典教义本身就有着不可以施行的东西。
日本的商人们将《孙子兵法》当成是他们获致成功的不二法宝,但是这其实已经使得《孙子兵法》变成了他们的商业帝国中的意识形态话语。大凡成功的人士总是易于找到某种经典教义或者信条来当成是揭示他们成功的秘密,而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在将自己的心理历程寄托在经典教义中的只言片语乃至经典教义本身上。
单就《孙子兵法》与《战争论》对于各处所处的东西方世界军事战略领域的影响力与享有的地位而言,这两者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但是,如果只说在内容上的对应关系,那么西方世界中真正能够与《孙子兵法》相提并论的兵书是约米尼所著的《战争艺术概论》而并非其他。约米尼以战争行动作为一种科学化的研究对象、能够将对于作战行动原则的研究缩小到公式化与图形化的演算之间,这种做法与《孙子兵法》中重视估算的作用、能够依据敌我双方的优劣状况及天时地理条件而将战争的胜负与作战方式估算得十分精确的做法相类似。
另一处相同的地方在于,尽管约米尼认为战争有着为数不多的恒定不变的共同原则,但是他仍然反对将战争视作为一门精确的科学来对等,而只是将战争归结为一种艺术并且强调说在战争中个人的战斗素质、精神力量以及指挥官的性格、毅力和才能等会对战争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中崇尚估算的作用,并且认为估算应当在战争之前就进行并据此而决定是否进行战争和如何进行战争,但是孙武在最后的用间篇中却又强调起间谍的作用,其实是对人的能动作用的强调。
因此,如果说《孙子兵法》是战争行动学的先驱,而《战争艺术概论》则同样也是战争行动学的典范之作。在海湾战争中,美军司令特意将《孙子兵法》手册发放到每一个军事指挥官手中,以期他们能够在实际的战斗指挥中应对自如。
总结:战略不向艺术性妥协
战略的天堂里面拒绝艺术的存在。战略不追求艺术性和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而只要求战略目标的全盘实现。
东方模式的任人唯贤与君臣猜疑是孪生兄弟,在这样的治国方式中,国家的兴衰与否被认为是取决于人某一个或几个聪敏、睿智的高层人士。由于得到了屈指可数的贤才而认为国家必然由此兴盛、由于失去了这些贤才而宿命式地以为国家必定由此走向衰落,原本事实的确有这种迹象,可是信奉这些理论的人却将事实当成是佐证自己既定想法的依据,结果他们总是活在宿命因果链之中。
那些讲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人,如果他们不以实际作战效能来衡量这种战法,而他们讲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做法就只能是流于空想的理想化状态。假如这些人以实际作战效能来衡量这种战法,那么他们就必然要承认只有切合具体的战场环境、能够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的战法才是当时条件下最佳的战法,这样当情形不适合时“不战而屈人之兵”就不能算作是最佳的战法。
讲求实际作战效能的军事指挥官,不以某一种或几种理想化的状态为追求,而是懂得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势来采取在当时情形下最为有效的战法,在他们眼中没有一成不变的战法、也从来就不存在过一直是最优的战法,只要能够收到最佳的战果而任何一种战法都可以成为最优的战法。
以实际作战效能作为衡量战法的标准,就不能笼统地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优越的战法,在必须通过实际的作战行动才能更加有效地达成战争目的的时候,“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做法就是不切实际的和根本行不通的、因而也就不是最佳的战法了。
现在,那些讲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人,一方面承认要想实现这种理想状态需要有一定的必备条件,另一方面却不顾及实情而一概而论地将“不战而屈人之兵”视作为最为理想的战法,这正是因为他们脱离实际、根本不考虑具体的战场情势并且不以实际作战效能来衡量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