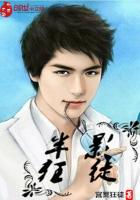然而龙安寺石庭园的非对称,却是极尽艺术家的意识之能事的产物。与其把它叫做意识,莫如把它叫做执拗的直感或许更正确些。日本的艺术家过去并不依赖于方法。他们所思考的美,不是普遍的东西,而是一次性的东西,结果是难以变动,在这点上,与西欧的美别无二致。不过,产生这种结果的努力,不是方法性的,而是行动性的。也就是说,执拗的直感的锻炼,及其不断的尝试就是一切。单凭各自的行动而能捕捉到的美,是不能敷衍的,是不能抽象化的。日本的美,大概就是一种最具体的东西。
这种凭直感探索到的终极的美的姿影,类似废墟的美,这是不可思议的。艺术家心怀的形象,总是与其创造有关,同时也与破灭相连。艺术家不光从事创造,也从事破坏。其创造往往是在破灭的预感中产生,当他思索着描绘某种终极形中的美的时候,被描绘的美的完整性,有时候是对付破灭的完整性,有时候是为了对抗破坏而描摹的破坏的完整性般的完整性。于是,创造几乎失去形状。为什么呢?因为不死之神创造应死生物的时候,那只鸟的美妙的歌声,是从与鸟的肉体之死一起告终为满足的。可是,艺术家如果创造同样的歌声的时候,为了使这种歌声保留至鸟死之后,而不创造鸟应死的肉体,无疑是要创造看不见的不死之鸟。那就是音乐。音乐之美,就是从形象的死开始的。
希腊人相信美之不灭。他们把完整的人体美雕刻在石头上。日本人是不是相信美之不灭,这倒是个疑问。他们思虑具体的美如同肉体那样有消亡的一天,因此,总是模仿死的空寂的形象。石庭园那不均整的美,令人感到仿佛暗示着死本身的不死。
奥林匹亚的废墟之美,究竟属于哪种类型的美呢?或许其废墟和残垣断壁仍然是美本身,就关系到整体结构是依据左右相称的方法这点上。残垣断壁失去部分的构图,是容易让人窥知的。不论是帕台农神庙还是厄瑞克忒翁庙,我们想象它失去的部分时,不是依据实感,而是根据推理。那种想象的喜悦,不是所谓的空想的诗,而是悟性的陶醉。看到它时,我们的感动,就是看到普遍性的东西的形骸之感动。
而且不妨想象一下,废墟所给予的感动,之所以可能超过我们看到它!11的实在原形时所受到的感动,其理由还不仅于此。希腊人思考出来的美的方法,是重新编织生,是再组合自然。瓦莱里也曾说过Z所谓秩序是伟大的反自然的计划。”废墟偶然地使希腊人所思考的那种不灭之美,从希腊人自身的羁绊中解放了出来。
在山顶城邦的各处,我们可以感受到希腊的群山、东方的鲁卡贝托斯山、北方的帕尔纳素斯山、眼前的萨罗尼克湾的萨拉米斯岛,乘上猛刮向它们的希腊的劲风,插上搏动的翅膀。(这正是希腊的风!正是这种风吹拂着我的脸颊,拍打着我的耳朵。)
这些翅膀是从废墟失去的部分中生长出来的,残存的废墟是石头。人在失去的部分得到了翅膀。人正是从这里振翅的。
我们从山顶城邦的蔚蓝天空,看到了摆脱羁绊的生。获得诸神不死的无形的肉体、振翅的景象。从大理石与大理石之间,我们可以看到绽开的火红的黑粟花」U野生的麦和芒随风摇曳。这里小神殿的奈基之所以没有翅膀,并非偶然。因为那木造的无翅膀的奈基像已经失落了。就是说她已经获得翅膀了。
不光是山顶城邦,就是看宙斯神殿的圆柱群,它那引人生悲的圆柱的耸立姿态,使我仿佛看到了摆脱束缚的普罗米修斯。这里虽然不是高台,但由于废墟的周边是一片矮草,所以看上去神殿的大理石显得越发鲜艳有生气。
今天我依然沉浸在无尽的酩酊中。我似乎受到狄俄尼索斯的诱惑。上午两个小时,我就是在狄俄尼索斯剧场的大理石的空席上度过的。下午,我漫步在草地上,凝视着宙斯神殿的圆柱群,度过了一个小时的时光。
今天也是绝妙的蓝空。绝妙的风。强烈的光。……对了,希腊的日光超过温和的程度,过于毕露、过于强烈。我从内心底里爱这样的光和风。我不喜欢巴黎,我之所以不喜欢印象派,乃是因为那温和而适度的日光。
毋宁说,这是亚热带的光,实际上山顶城邦的外壁,葳蕤丛生着一大片仙人掌。如今松、丝杉和仙人掌,还有黄色的禾本科植物的观众,从看不见一个观众姿影的狄俄尼索斯剧场观众席的更高处,凝然地鸟瞰着空荡的舞台。
我看到在投影半圆舞台上飞掠而过的燕子、那位阿那克里翁歌唱过的燕子。燕群翻腾着白色的腹部,往返翱翔在狄俄尼索斯剧场和演奏场的上空。今天任何一处小屋都休息,它们的心情烦躁地啁啾鸣啭,四处飞翔。
我坐在狄俄尼索斯神的神甫的坐席上,静听虫声。不知怎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希腊少年,打从刚才起就缠绕在我身边不肯离去。他大概是想要钱吧,还是想要我正在抽着的英国香烟,抑或是打算把古代希腊的少年爱传授给我呢?如果是这样,我早已知道了。
希腊人相信外界。这是伟大的思想。在基督教发明“精神”以前,人不需要什么“精神”,自豪地生存着。希腊人所思考的内面,总是保持着同外面左右相称。希腊戏剧没有任何诸如基督教所思考的那种精神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过分的内面性必然归结到遭到复仇这一种教切!的反复上。我们不能把希腊剧的上演同奥林匹克竞赛分割开来考虑。在这种充分的强烈的阳光下,思考着不断地跃动又静止、不断地破坏又保持下来的、选手们的肌肉般的泛神论式的均衡,让我沉醉在幸福之中。
狄俄尼索斯剧场,作为装饰品,仅残存着蹲踞的狄俄尼索斯神的雕像,以及其周围的浮雕。我们看到剧场背后,像采石场般的石头的堆积,还看到像经过惨剧似的四处散乱着衣裳皱褶的残片、圆柱的残片、裸体的残片。
我渐渐移动到各个坐席上,度过了接近上演一出悲剧所需要的时间。不论是从神甫席、民众席或任何一个席位上,无疑都可以透过假面具明晰地听到希腊剧的台词,看到演员伴随着鲜明的影子清晰地变动着姿态。方才有个手持照相机的英国海军士官出现在半圆舞台上,可以很容易地目测到剧场的规模和演员的身高的均衡。
为了重访奥林匹亚,我从山顶城邦启程走了一段宽阔的人行道。领带飘在我肩上,迎面走来的老绅士的白发被风拂乱了。
我又发现了一处恰好的位置来观赏宙斯神殿。我坐在十三根柱子和两根柱子之间的正居中一带的草地上。这个位置,可以像眺望军队的纵队那样地观望十三根圆柱。
只见中央的六根柱子、右边的四根、左边的三根分别成一组,准确地将透过申殿可以望见的天空一分为二。但是,中央的六根最具重量感。右方的四根和左方的三根都不均衡,以略差的量感向中央逼将过来。中央最前头望及的圆柱,率领着其背后的五根,显得特别凛然和气质尚雅。
神殿的左右,以希腊市镇的远景为背景,屹立着两三棵丝杉。从山顶透过神殿望见的空间的、低约四分之三的位置上,缓缓起伏着褐色的山脉,横穿过圆柱绵延而去,剩下占四分之三的部分,则是绝妙的蔚蓝的天空。
从这个位置上看神殿,简直就是一首诗。
我足足凝神眺望了一个多小时,无疑我站起身来的时候,正是最佳的时机。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游览车来了,此前我独自占领的诗的领域被喧嚣的观光客所取代,他们成群结队地人侵了。
对我来说,望着他们的姿影,更觉忧郁。因为我具备其他方便的条件,明天将成为旅游团的成员之一乘坐游览车,奔赴德尔斐。
(叶渭渠译)
威廉·斯泰伦
(1925-2006)美国小说家。生于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苏菲的选择》、《躺在黑暗中》、《长途行军》、《给这栋房子放把火》、《南特·特纳的自白》《普利策奖),自传《看得见的黑暗》、《黎明的潮水:三个青年时代的故事》等。
威廉·福克纳
世界上他最憎厌的事情就是自己的隐私权受到侵犯了。虽然福克纳太太和他的女儿吉尔一再向我表示,在这所房子里我是受欢迎的,虽然我知道她们的欢迎确实是真诚的,但我仍然感到自己是个人侵者。哀伤,像为数不多的其他事物一样,是件纯属个人的事情。而且,福克纳很讨厌那种人(为数可不少呢),他们总是对着他的私人生活嗅嗅闻闻一这是些文学界的“包打听”与“小广播”,就想从与名人的接近中得到短暂的剌激与些许折射回来的光彩。他自己不止一次很有道理地说过,一个作家唯一与别人有关的事情就应该是他的作品。如今他已经去世,无能为力地躺在那具灰色的棺木里,我更觉得自己是个在我不应来的地方到处剌探的闯人者了。
可是除却使我们那样无精打采的死亡这一确切的事实之外,这一天最突出的因素却是闷热,这热就像是一种微小、歹毒的死亡,仿佛一个人正被闷死在一件潮乎乎的呢子大衣里。连北边六十英里的孟菲斯的几种报纸也评论了这恶劣的气候。奥克斯福被浸淹在一片闷热之中,这个星期六的上午,支配着法院广场一带人们情绪的是一种酷热与出汗造成的濒临绝望的倦怠感。一辆辆福特、雪佛莱和轻型货车斜着停靠在马路牙子外面,在无情的阳光下挨烤。在这种气温里,密西西比州人已经学会了缓慢、几乎是胆战心惊的移动。他们走起路来小心翼翼且步步斟酌。在第一国家银行的门廊下与法院周围那树荫稀疏的便道上,光穿衬衣的农民、额头汗涔涔的家庭主妇与做买卖的黑人都是有气无力、动作慢腾腾的。在法院西边一幢建筑侧边一面墙的高处,是一幅至少有二十米长的巨大招牌。上面刷着“叛党美容学院”这几个字,顶上还画着幅联邦的旗子。招牌、旗帜与墙占领了广场一个热烘烘的角落,在炙灼的阳光照耀下像是有马上燃烧起来的危险。这是一种超常的炎热,让你身心都受到很大的折磨,一场依稀记得的噩梦也会造成的同样的后果,最后你明白你以前不是没有遇见过,那是在福克纳所有那些长短篇小说里,在那里这样邪恶的天气一当然也包括较为宜人的天气一以几乎摸触得着的真实感在起作。
在《奥克斯福鹰报》的底层办公室里,主编兼老板合伙人尼娜·古尔斯贝夫人在一只空调机的嗡嗡声里忙个不停。这是个高大、开朗、健谈的女子,她很得意地告诉我《鹰报》新近荣获密西西比州报业协会的本年度最佳周报一等奖。她刚从街上回来,是到镇上去散发传单的,传单上印的是:
为纪念威廉.福克纳,敝号于今日,即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下午二时至二时十五分暂停营业。
她说,这是她出的主意,接着又说人们总是说奥克斯福对比尔·福克纳漠不关心,其实蛮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为他感到骄傲。你瞧。”她让我看一些过期的《鹰报》,有一张头版上的标题是“诺贝尔文学奖落入奥克斯福人之手。”另一期有一整版广告,出资者之中有老密西干洗商店、加思赖特-里德药行、米勒咖啡馆、A.H.艾文特轧棉储存公司等等。广告中的祝贺话语是“欢迎比尔·福克纳荣归乡里。兹特向全国父老宣告一我奥克斯福镇与全体镇民均为我镇荣获诺贝尔奖之作家威廉·福克纳感到无比骄傲。”版面上还登了好些福克纳在斯德哥尔摩的照片。从瑞典国王手里接过诺贝尔奖、在雪地里和他们女儿一起行走、在一辆雪橇旁弯下腰来与“一个瑞典小男孩”耶卩天。
“你可以看到我们为他感到多么骄傲。我们对他一直是引以为荣的,”古尔斯贝夫人说,“嗨,我从小就认识比尔·福克纳。我住的地方离他家还不到两条街。他散步我们遇到时总停下来聊上好一阵。天哪,他总穿一件极其高雅的花呢短上装,肘弯处钉有两块皮,手杖的弯把挂在前臂上,我总说,倘若他们不让比尔·福克纳穿着那件花呢短上装入土,那是很不合适的。”回到福克纳的家中,在小路上空合抱的老雪松的阴影与柱廊也只能稍肖减轻中午时分的一些热气。这种天气你只能穿一件衬衫,事实上不少男人已把他们的西服上衣脱了。在大门口聚集了一些家庭成员,这里有约翰·福克纳。他也是一位作家,他简直是他哥哥的复制品或者说是鬼魂,连那疑问般抬起的眉毛与斜着下垂的上髭都与乃兄的一模一样。这里还有约翰的已长大成人的几个儿子。还有另一个弟弟默雷,他眼神忧郁,语音柔和,是联邦调查局派驻在莫比尔的一个工作人员。这里有吉尔的丈夫保尔·萨默斯,他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是位律师,和吉尔一样,他也管福克纳叫“爸”。大伙儿聊天的内容很普通天太热、坐喷气式飞机旅行的长处、密西西比州不合时代潮流的禁酒法令的繁琐。大伙儿往西边退去好让一位夫人过去,她捧着一个很大的洒有紫莓色糖霜的蛋糕,这仅仅是这天送来的许多个蛋糕里的一个。
屋子里面稍微凉快一些,在门左面的书房里一它正对着空出来停放灵柩的起居室一时间像是容易打发一些。这是个宽敞、杂乱、舒适的房。一面墙上挂着幅金边镜框的福克纳穿着猎装的肖像,戴着他那顶黑色高顶礼帽,一副得意扬扬的样子,挨近它放在桌子上的是一尊瘦削憔悴的堂吉诃德的木雕。这里还有两幅黑人佣仆的亲切、充满爱意的画像,是“莫德·福克纳小姐”的作品(她按照家庭传统,拼“福克纳”时少一个“u”,和她儿子不同)。其他几面墙都是书,什么人写的都有,毫无次序地放在一起,有的带书皮有的不带,还有不少是上下颠倒放的,如《金驴记》、维多里尼的《在西西里》、《卡拉马佐夫兄弟》、考尔德·威林厄姆的《杰拉尔丁·布雷德肖》、《厄内斯特·海明威短篇小说集》、《从这里到永恒》、莎士比亚的《喜剧集》、艾拉·沃尔弗特的《爱的行动》、《S.J.佩雷尔曼作品精粹》以及许许多多别的,让人数不过来。
就在这间书房里我遇见了射尔比·富特,他是小说家、内战史家,也是福克纳为数极少的文学界朋友中的一个。这是个性格开朗、皮肤黝黑的四十五六岁的密西西比州人,他穿一套绉面条纹薄西服,看上去一点儿也不热。他告诉我,像我这样一个纯粹的弗吉尼亚人自然不能适应这样的酷热。“你得慢慢儿地在这里面穿行,”他教导我,“千万别做出任何多余的动作。”接着他又让人沮丧地说:“这闷热不过才刚开了个头。你八月里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