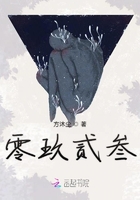接着讲道德问题。我认为在基督的道德品性中存在着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那就是他相信地狱。我自己认为,真正非常慈悲的人决不会相信永远的惩罚。《福音》书中描绘的基督无疑是相信永远的惩罚的,我们也一再发现把不听从他切!导的那些人视为寇仇的报复;理,这种态度在传教士中并不少见,但它确实有损于他至善至美的形象。举例来说,苏格拉底就没有这种态度,他对不听从导的人总是和颜悦色,彬彬有礼;我自己认为,采取这样的态度要比采取愤怒的态度,对于圣贤来说,是更值得称道的。也许大家还记得他临终的遗言,以及他平时对持不同观点的人所说的话吧。你们会发现基督在《福音》中曾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这是对那些不听他教诲的人讲的。我认为这并不是很高明的口气,而诸如此类关于地狱的描写也比比皆是。当然,还有一段经文,是关于亵渎圣灵的罪的,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句经文给世界带来了无穷苦难,使各种各样的人都以为自己已犯下了亵渎圣灵的大罪,今生来世都不能得到饶恕。我坚决相信,生性还有一点仁慈的人,就绝不会把世界置于这种畏惧和恐怖的笼罩之下。基督还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他还不断谈到哀哭切齿,这种说法在一节又一节的经文中一再出现,使读者明显地觉得说话的人对于别人哀哭切齿感到某种乐趣,否则他就不会这样津津乐道。大家当然记得分别绵羊和山羊的故事,讲到他第二次降临时将如何把人类分成绵羊和山羊两大类。他要对山羊说:“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永火里去。”他继续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他又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他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他也一再重复这一说法。我必须承认,我认为把地狱的水火当做是对罪恶的惩罚的这种种理论,是一种惨无人道的理论。它是给世界带来残忍,使世界多少世代受到残酷折磨的理论。《福音》中的基督,如果你相信他的传记编写者所描绘的那样,无疑是对于这一点必须负部分责任的。另外还有些重要性较小的例子。例如格拉森猪群的事件,驱使恶魔进入猪群,使它们撞下山崖,投海而死,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很仁慈的。你要记得他是无所不能的,能叫魔鬼走开了事,但他却让它们进入猪群。还有无花果树的那个奇怪的故事,我也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大家都知道无花果树的遭遇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彼得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诅咒的无花果树,已经干枯了。”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故事,因为那时本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你真的不能怪罪无花果树不结果。我自己觉得,无论是就智慧还是就美德来说,基督都没有达到某些历史名人的高度。在那些方面,我想我应该把佛和苏格拉底置于基督之上。
感精因素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不认为人们接受宗教的真正原因跟论证有任何的关系。他们接受宗教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人们经常被告知,攻击宗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举动,因为宗教使人有道德。我就是这么被告知的,但我未加理睬。你们都知道在塞缪尔·勃特勒(SamuelButler)的《重访埃瑞磺》(ErewhonRevisited)一书中对这种说法的讽刺。在这本书中,有一位希格斯访问一个边远国家,住了一段时间后乘气球逃离那里。二十年后,他故地重游,发现那里有了一个崇拜他的新宗教,他被称之为“太阳之子”,传说他飞升上了天堂。他发觉庆祝升天的大典即将举行,又听到汉基和盘基教授,这两位“太阳之子”教的大祭司,在私下交谈中透露他们从没见过这位希格斯,并希望永远不会见到他。他感到很气愤,就过去对他们说:“我要去揭露这个骗局,告诉埃瑞璜人民,我就是那位希格斯,我是人,我只是乘气球飞走而已。”他被告知:“你不能这么干,因为这个国家的所有道德规范都与这个神话紧密相连。一旦人们知道你并没有飞上了天堂,他们的道德就会败坏。”这样,他被说服了,悄悄地离去。
这就是那个理念如果我们不坚持基督教,我们全都会道德败坏。在我看来,那些坚持基督教的人恰恰是最为败坏的人。你们发现有这么个古怪的事实,那就是在任何时期,宗教越强盛,对教条的信仰越强烈,残酷的行为也就越严重,事态也就越糟糕。在人们全心全意相信基督教的所谓“信仰的世纪”,有让人备受折磨的宗教裁判所;有几百万不幸的妇女被当做女巫烧死;以及在宗教的名义下对各色各样的人所实施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发指的行径。
当你考察这个世界,你会发现人类情感的每一点小小的进步,刑法的每一个改善,减少战争的每一个步骤,更好地对待有色人种的每一次进程,对奴役制度的每一次削弱,世界上道德水准的每一次提高,都是与反抗教会组织息息相关的。我可以很谨慎地说,被教会组织起来的基督教,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世界道德进步的主要敌人。
教会是怎祥阻碍进步的
我说今日的教会依然阻碍着人类的进步,你也许觉得有些过火。我并不认为这样。现在只说一件事实。请你们原谅我提到这样的事。这不是令人愉快的事,但是教会强迫我们谈论令人不愉快的事。假定在我们今天居住的世界上,有一个天真无知的少女嫁给了一个梅毒病患者,天主教会就说:“这是不可变更的神圣誓约。你们必须共同生活一辈子。”女方还不能采取任何措施以预防生养患梅毒病的婴儿,这就是天主教的主张。我认为这是穷凶极恶的残忍,只要人类天然的同情心还没有被教条完全润灭,只要人类的道德天性对苦难的感觉还没有达到麻木不仁的地步,谁也不能说这种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种事态应该继续下去。这还只是一个例子。目前,教会仍然拥有各种手段坚持它所称为的道德,使各种人民蒙受不应有和不必要的痛苦,当然,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它仍然反对减轻世界上痛苦的各种各样的发展和进步。因为它把某些同人类幸福毫无关系的狭隘的行为准则,美其名为道德;如果你认为应该做这做那,因为它有利于人类幸福,他们却说这同问题毫无关系。“人类的幸福与道德有什么关系呢?道德的目的并不在于让人类幸福”。
恐犋是宗教的基础
我认为宗教基本上或主要是以恐惧为基础的。这一部分是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怖、一部分是像我已说过的。希望在一切困难和纷争中有个老大哥以助一臂之力的愿望。恐惧是整个问题的基础一对神秘的事物,对失败,对死亡的恐惧。恐惧是残忍的根源,因此,残忍和宗教携手并进也便不足为奇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依靠科学的力量已经开始能了解一点事物、掌握一点事物。科学终于在同基督教的斗争中,在同一切教会势力们斗争中,在一切陈腐箴言的逆流中,一步一步艰难而顽强地发展起来了。科学能够帮助我们战胜多少世代以来人类一直生活在其中的怯懦的恐惧。科学能使我们懂得,我们扪心自问也该知道:我们再也不要到处寻找子虚乌有的帮助,再也不要幻想天上的救星,而宁可脚踏实地,依靠我们自己在地上的努力,把多少世纪以来教会造成的这个世界改造成为适于生活的地方。
我们要做什幺
我们要独立思考、光明正大地看待世界的一切一善的、恶的、美的、丑的,正视客观而不是害怕现实。用智慧征服自然而不是仅仅慑于自然的淫威,甘愿俯首听命。有关上帝的整个观念来源于古代东方专制主义。这种观念是同自由人格格不入的。当你听见人们在教堂中自我贬斥,说他们是可怜的罪人这类话时,会感到是可耻的,是同有自尊的人不相称的。我们应当昂然奋起、坦率地正视世界。我们应当把世界建设得尽可能美好些,纵然不能十全十美尽如人意,也总要比别人在过去干的强得多。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需要的是知识、善良、勇气,而不是对以往嗟悔不已,也不是用许久以前无知的人们用过的话语来禁锢我们自由的思想。这需要的是大无畏的观点和自由的思想。这需要的是对未来的憧憬,而不是对于业已死亡的过去永无止息的怀恋。我们深信用人类智慧创造的未来世界将远远地超过死亡的过去。
(佚名译)
岛崎藤村
(1872-1943)原名岛崎春树,别号古藤庵,出生于曰本长野县筑摩郡。着有长篇小说《破戒》和诗歌《藤村诗集》等。其《破戒》以“宣告日本近代文学的确立”而在曰本文学史上成为一座瞩目的里程碑。
落叶
每年十月二十日,可以看到初霜。在城里,只有冬天来到杂木丛生和布满武藏野的时候,才能看到薄薄的、令人喜悦的微霜。你对这些是司空见惯了的。我很想让你也瞧一瞧这高山的霜景呢!这儿的桑园,要是来上三四场霜,那就看吧,桑叶会骤然缩成卷儿,像烧焦了似的,田里的土块也会迅速松散开来……看了这种景象,着实有点怕人哩。显示着冬天浩大威力的,正是这霜啊!到时候,你会感到雪反而是柔美的,那厚厚的积雪给人的是一种平和的感觉。
十月末的一个早晨,我走出自家的后门,望着被深秋的雨水染红的柿子树叶,欣欣然地飘落。柿树的叶片,肉质肥厚,即使经秋霜打过,也不凋残,不蜷曲。当朝暾初升、霜花渐融的时候,叶片耐不住重量,才变脆脱落下来。我伫立良久,茫然眺望着眼前的景色。心想,这天早晨定是下了一场罕见的严霜吧。
进人十一月,寒气骤然加剧。天长节清晨,起来一看,上下一白,望不到边际。后门口的柿子树叶,一下子落了,连路都埋了起来。没有一丝风,那叶子是一片、两片,静静地飘零下来的。屋顶上鸟雀欢叫,听起来11:平常嘹亮、悦耳。
这是个阴霾的天气,空中弥漫着灰蒙蒙的雨雾。我真想到厨房里暖一暖冻僵的双手。穿着布袜子的脚趾也感到冷冰冰的。看样子,可怕的冬天就要临近了。住在这座山上的人们,从十一月到明年三月,几乎要度过五个月漫长的冬季,他们要为过冬做好准备。
寒冷的北风刮了起来。
这是十一月中旬,一天早晨,我被奔腾的潮水般的响声惊醒,原来是风在高空呼啸。进而渐渐趋于平息,时而又狂吹起来,震得门窗咯咯有声。尤其是朝南的窗子,树叶纷纷敲打着窗纸,噼噼啪啪响个不停。千曲川河水,听起来更觉得近在咫尺了。
推开窗户,树叶就飞到屋内来。天气晴朗,白云悠悠。屋后小溪岸边的杨柳,在猛烈的北风中披头散发地挺立着。干枯的桑园里,经霜打落的黄叶,左右飞旋。
这天,我到学校去,来回都经过车站前的道路,遇见了不少行人。男的戴着丝绵帽,或用绒布裹着头;女人家则扎着毛巾,将两手缩在衣袖里。人们你来我往,流着鼻水,红着眼圈,有的还淌着眼泪。大家面色苍白,唯有两颊、耳朵和鼻尖红彤彤的,屈身俯首,瑟瑟缩缩地赶路。顺风的人,疾步如飞。逆风的人,一步一歇,仿佛负着重载一般。
土地,岩石,人的肤色,在我的眼里都变得一片灰暗,就连阳光也成灰黄的了。寒风在山野间奔突,呼号,暴烈而又雄壮!所有的树木都被吹得枝叶纷披,根干动摇。那柳树、竹林,更是如野草一般随风俯仰。残留在树梢的柿子刮掉了。梅、李、樱、榉、银杏等,一日之间,霜叶尽脱,满地的落叶顺着风势飞舞。霎时,群山的景色顿时变得苍凉而明净了。
(陈德文译)
普里什文
(1873-1954)苏联着名散文家。生于一个商人家庭。散文集以《大自然的日历》、《叶芹草》和《林中水滴》等为代表。
一年四季(节选)
自然睛雨表
一会儿细雨蒙蒙,一会儿太阳当空。我拍摄下了我那条小河,不料把一只脚弄湿了,正要在蚂蚁做窝的土丘上坐下来(这是冬天的习惯),猛然发现蚂蚁都爬出来了,一个挤一个,黑压压的一群,待在那里,不知要等待什么东西呢,还是要在开始工作以前醒醒头脑。大寒的前几天,天气也很温暖,我们奇怪为什么不见蚂蚁,为什么白桦还没有流汁水。后来夜里温度降到零下十八度,我们才明白:白桦和蚂蚁从结冻的土地上,都猜到了天会转冷。而现在,大地解冻了,白桦就流出了汁水,蚂蚁也爬出来了。
最沏的小溪
我听见一只鸟儿发出鸽子般的“咕咕”叫声,轻轻地飞了起来,我就跑去找狗,想证明一下,是不是山鹬来了。但是肯达安静地跑着。我于是回来欣赏泛滥的雪融的水,可路上又听见还是那个鸽子般“咕咕”叫的声音,并且一再一再地听见了。我拿定了主意,再听见这响声时,不走了。于是慢慢地,这响声变得连续不断起来,而我也终于明白,这是在不知什么地方的雪底下,有一条极小的溪水在轻轻地歌唱。我就是喜欢这样在走路的时候,谛听那些小溪的水声,从它们的声音上诧异地认出各种生物来。
晶晶的水辟
风和日丽,春光明媚。青鸟和交喙鸟同声歌唱。雪地上结的冰壳宛女口玻璃,从滑雪板下面发出裂帛声飞溅开去。小白桦树林衬着黑暗的云杉树林的背景,在阳光下幻成粉红色。太阳在铁皮屋顶上开了一条山区冰河似的,水像在真正的冰河中一样从那里流动着,因冰河便渐渐往后面退缩,而冰河和屋檐之间的那部分晒热的铁皮却愈来愈大,露出原来的颜色。细小的水流从暖热的屋顶上倾注到挂在阴冷处的冰柱上。那水接触到冰柱以后,就冻住了,因此早上的时候,冰柱就从上头开始变粗起来。当太阳抹过屋顶,照到冰柱上的时候,严寒消失了,冰河里的水就顺着冰柱跑下来,金色的水珠一颗一颗地往下滴着。城里各处屋檐上都一样,黄昏前都滴着金色的有趣的水珠。
背阳的地方还不到黄昏时,早就变冷了,虽然屋顶上的冰河仍然后退着,水还在冰柱上流,有些水珠却毕竟在阴影处的冰柱的末尾上冰结住,并且愈结愈多。冰柱到黄昏开始往长里长了。而翌日,又复艳阳天,冰河又复向后通,冰柱早上往粗里长,晚上往长里长,每天见粗,每天见长。
舂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