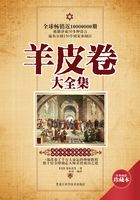安雪晨一直以为段庭坚只是以婚姻做为条件才结婚的,他应该有许多的无奈和随意。
但照片里的段庭坚,穿着精心准备的礼服,头发刻意的修剪过,庄重的脸上呈现出掩饰不住的欣喜。如果把照片给其他人看,相信所有看过的照片的人一定都能感觉到他的欢喜和幸福。
这样的幸福表情令段庭坚一贯冷峻沉定的脸上竟泛起让人心动的温柔。
当段庭坚将婚戒带入安雪晨左手无名指时,脸上竟显出一丝激动的神情,他捧起安雪晨的脸,亲吻她时,竟小心翼翼的像是捧着一个好似稍不留心就会摔碎的稀世珍宝,而在这份小心翼翼中却透出一丝难以掩饰的快乐,这个快乐仿佛充溢着段庭坚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从他的身上由内而外,从上到下的向外散发出来,感染了周边的每一个人。
安雪晨一定也被段庭坚的这份快乐所感染了,否则她怎么会那样没有掩饰任何情绪的痴痴地望着他?
如果让不知情的人看到这样的照片,一定以为她们是一对感情深浓,如漆似胶的亲密恋人。
照片再次翻到了最后一张,安雪晨把手压在照片上,慢慢抬起头望向书桌上相架里的照片。
段庭坚最不讨厌拍照,家里基本上找不到他的照片。
安雪晨也素来都不喜欢留影。她和段庭坚在一起这么久,两人从来没有拍过照片,更没有合过影,如果不是段庭坚安排摄像师拍下婚礼上的这些照片,她也许只能从杂志上去搜寻他的相片了。
想到这里,安雪晨眼里的雾气更浓了一层。
一些从来没有细细思量过的东西从她大脑的深层意识中渐渐苏醒,在她的脑海里不断膨胀,并迅速冲击入她的心间,让她的心绪渐渐起伏波动起来,直至最后竟难以自持,眼里的雾气已凝聚成泪滴欲夺眶而出。
安雪晨轻轻闭上了眼睛,将眼泪再次压回眼底,片刻后,她待心绪稍稍平复了些后才缓缓睁开眼睛。
安雪晨慢慢合上相册,把它放到旁边,然后伸手从快递信封里拿出了另外几件东西,当安雪晨看到展现在她面前的这几件东西时,更是呆愣的大脑里有一瞬的空白。
安雪晨把几样东西一一摊放在书桌上,一支发簪,一张银行卡,一枚淡紫色蝴蝶形的胸针。这几样东西安雪晨都很熟悉,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她曾经使用过的。
发簪是安雪晨第一次和段庭坚在酒店里见面时她用来挽发的,后来被段庭坚从她的头发上拔下来后便没有再找到。
银行卡是那一夜安雪晨准备离开时,段庭坚交到她手里的,她从里取出了四万元后又退还给了段庭坚了。
安雪晨的眼睛盯着那枚淡紫色蝴蝶形的胸针,她凝神想了想,终于想起来,这是她之前所在的那家服装公司的老总汪一鸣让她参加一个酒会时,为她准备了一套礼服上的饰物,这枚胸针当时别在一件白色的披肩上。
就是在那个酒会上她第二次遇见了段庭坚,也是在那个晚上,段庭坚把她从酒会上带回了家,从那以后两人便开始了说不清也理不完的纠葛。
安雪晨记得那天晚上,段庭坚满脸怒意的粗暴地把披肩从她身上扯下扔到了地毯上,第二天清晨她醒来时,在卧室里没有再看到礼服和披肩,她当时因为看到手机上好多个医院打来的未接电话,根本就没有留意那套礼服。她从手提包里拿出酒会前进入酒店时所穿的衬衫和牛仔裤换上后,便急奔下楼赶往了医院。
安雪晨忽然想起什么,她倏地站起身,疾步走出书房,上了二楼,走进衣物间,走到衣橱前,蹲下身子,把衣櫉最底层的一个抽屉完全拉开,一个粉红色的长方形纸盒从抽屉的最里侧处露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