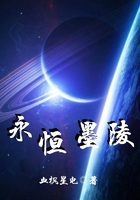初秋里,鸣蝉依旧悠然,享受日光里夏的温存。北大楼上爬山虎还是郁郁葱葱,同放假那天看似没有什么不同,但偶尔有一阵稍劲的风,便发出“沙沙”的声,那临近秋而变得又干又脆的事实,便如同过了三十的秦淮歌女眼角的纹,躲无可躲。
将钢笔套拧紧,套上笔杆,再夹住笔记本,与课本一同小心放进书包,低着头,继续在抽屉里摸索,抽屉黑暗的深处,被我在课中无意识地从鬓边取下的绣球花发卡安静地躺着,此刻也被我用手探到,妥帖放进包里,再无可供我装模作样低头找寻的物件了。
“程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
十七八岁男孩子故作雄壮的嗓音一声声敲击着我,将微微发烫脸颊边的一缕头发塞进耳后,定定神,将包背上肩,向教室门口走去,心中暗自诅咒编排课程与教室的职员,竟将这课排在了只有前门的教室里,这个过程中还不住低头在桌椅间扫视,似是在找东西。余光瞥见讲台上,锃亮的黑皮鞋,卡其色的西裤,笔直地矗立在那里,心中默念“一二三”,抬头,正对上双手插在口袋里,漫不经心扫视教室,却又刚好扫到我的眼。
“老师再见!”低语如蚊虫鸣叫。
他“唔”了一声,便扭头看教室窗户外头垂下的藤蔓,我得了令般加快步子走了出去。回南京后第一次不自在的相遇便告了终,只是这样的尴尬,每周有一回,得持续到过年之前才能完。
走出东大楼的大门,西晒仍然炽热,刚从阴暗楼道里走出的我,被闪得不由得用右手搭了凉棚,一个瞬间,外头四周过于明亮,以至于旁的都看不到了。
“冷伊!”熟悉的声音从对面传来,虽看不清,却也知道是蒋芙雪。我揉揉眼睛,迎了上去,见得她张着一把鹅黄的油纸伞,却与夫子庙里常见的不一样,伞骨份外结实,看上去有檀木的承重,伞架也密实得多,那伞面上一个朱红衣裳的女子,用宽袖掩面,后面便是一座白雪皑皑的山,只山脚一圈是灰蓝灰蓝的,这就标准的雪山,但凡听到“雪山”这个词,就会想到的那种山。
“芙雪,好漂亮的伞!”我由着她把伞的阴影移到我头上,由衷地抬头赞叹,这才发现,伞的里面鹅黄的底子,上面粉粉的樱花,淡淡的一点痕迹。“和式的伞?”想来价格不菲。
她挥挥另一只手上的手绢,“还是有些热的。这伞?是啊,我在青岛一个日本人的店里头淘的。”
“你暑假去了青岛?”我有些诧异,青岛自然是暑假的理想去处,能去当然是再高兴不过的事情,只是这对我们这样普通的女学生来说称得上大事的事情,她居然放假前都没吱一声。
她大概也是看出我的惊异,“假放了不到一半,关外的一个姑妈邀我去的,待了十几天就回来了。”故作平静,却掩不住那一点点似是要冒出泡来的小骄傲。
我弯弯嘴角,笑问道,“那里的军官多得很。”
她似被火烫了般,用手绢作势要扇我,却也只是在肩上碰了碰,“那些军官啊,今天在这儿,明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哪里作数。”这话这腔调拿捏得若是从她母亲口中说出才最为合宜。
我回头看着她,“某些人光天化日之下,可莫要口是心非啊,这话你被别人教烦了才背出来的,还是心里想的?”说完猫了猫从她的伞下窜到一边。果然又躲过她的手绢。
“那些军官有什么……”话还没说完,她瞧着我身后愣了愣,收了声。
我双手在背后握着,垫着左脚脚尖,转了个弯过去,却见得程昊霖还是刚刚那个样子,站在教室的讲台上,望着窗外的藤蔓,这会儿也就顺道望到了藤蔓外头的我俩。
我不自在地点点头,他也微微点头,没有方才的漫不经心,倒像是要笑,只是那表情的变换太过缓慢,我没有等到看见那笑容,已垂下头走回蒋芙雪的伞下,胳臂有些僵硬,这才记得把握着的双手从身后解开,甩了甩,又懊恼这姿势不潇洒,甩得太高,显得粗野。
蒋芙雪那没说完的话也生生憋了回去,静了会儿,“程将军课上得怎么样?”
“还,还行。”一个不留神,说起话来竟结巴了。我不是很清楚,大抵是不错的,不像旁的老师,第一课总念叨些琐碎的打分、考试之类的细枝末节,他上来就来了句俄语,原是普希金的一首诗歌,之后便引开了去,内容也不和之前听过的讲座重复,浑厚的嗓音听在耳中本就沉沉的,若是用俄语念诗歌,那回荡的音便愈发低沉,让我的思绪不住地往别处跑。
思绪跑到王依那里,那夜她只是把我送到离家门口最近的巷子口,看着我进了巷子,没有再多说什么,第二天我依着前一天晚上记忆不太深刻的路磕磕绊绊找去的时候,竟已是人去楼空,回到南京这么两个星期也再没看见,问了娘也说不知道;思绪跑到那个叫昊霆的男子,他是程昊霖的弟弟没错了,原来是他与王依有纠葛,可程昊霖愤愤的是做什么?思绪又跑到那七里山塘灯光映照下的船上,博容立在窗户里,里面还有个玲玉,我是久久难以忘怀的,他后来竟再也没有来登门,完了,真的是完了,每每想到这里,心窝总隐隐作痛。
一堂课想了这么多事情,他往细处讲了些什么自然是没听进多少。
校门口,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刚刚起步,那玻璃背后的阴影里,依稀看见程虹雨依旧一席盛装,那压煞人的傲气,听说她们系今天刚开学。回来南京的两个礼拜,发现冷琮那不起眼的杂志色居然也有这样忙得夜以继日的时候,这半个月,他也就回来吃了三四次晚饭,旁的时候都半夜了才回,娘只让他注意身子,别的也帮不上忙,我见着他那乌黑的眼圈,几次想开口说说暑假里的见闻,又住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