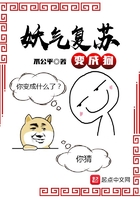那年的雪真大。
大雪不间断地下了三天三夜,雪花像娘做棉袄的棉絮,在木格子窗外大片大片慢悠悠地飘,把娘的心飘得火烧火燎。刚开始飘雪团的时候,娘就把家里能烧的柴草背到堂屋的灶旁,所以除了担心爹,我们在炕上围着娘很欢喜。炕是火炕,暖烘烘的,烧炕的锯末是爹冬闲帮人家打家具剩下的。爹出门了,他挣来的温暖,可替他守着他的老婆孩子呢。夜晚,院子里传来“喀吧喀吧”的声音,娘披衣起来,一边借着雪光往外看,一边宽慰我们:“有啥怕的,娘在家呢……哦,树枝让风刮下来了。”
她上炕来,却不躺下,倚着墙不做声。
“娘,你咋不睡?”
“也不知你爹啥时候回来。这大冷天的,他的棉裤可不厚实……”
我想的跟娘不太一样,我最想我的红棉袄。
我三岁那年的正月,二爷爷卖草鞋回来,送给爹一个咸鸡蛋下酒。爹切开的时候,鸡蛋里那汪橙黄的蛋黄让爹舍不得吃。他闻几下,小心地喂我吃了半块。夜里,我就咳嗽起来,一咳嗽就是一个月,以后每年都如此,毫不间断。
娘说,爹做生产队长,秋后都要外出开会一个月,这一个月里,爹吃得好,又不累,出门前又黑又瘦,回来就变得白胖。可接下来,爹就提心吊胆地等着我的咳嗽,把他身上的肉再咳下来。这样,爹的外出学习也就加了一项任务——淘换药方子。芦根泡的雪水、炸过的陈年豆腐、冰糖焖木瓜、艾草煮鹅蛋……我一个个药方吃过去,爹的煎熬还在继续。
十一岁那年,爹听一个老中医说,我这毛病,如果十五岁之前不好,就是一辈子的病根。爹跟娘没了办法,求村里通仙术的六奶奶。我躺在土炕上,六奶奶将娘买来的冥纸点燃,绕着我的身子旋转,口中念念有词;我在被窝里憋不住,“咯咯”笑出了声。娘给了我一巴掌,那是记忆里她唯一一次打我。
六奶奶临走时寒着脸说:“明年,就看孩子的造化啦。本命年,正月里给她穿件红棉袄,避避邪。”于是,腊月二十临时外出学习兄弟省市农业先进经验的爹,要给我买件红棉袄。我不管什么避邪,有一件买来的红棉袄过新年,村里我可是头一份。
第三天早上,太阳出来了,娘打开门,铲掉门口夜风旋来的一米高的雪墙,在昨天院子里扫拢的雪堆上,看到了一只兔子的尾巴。兔子当然不是撞死的,难道一堆雪会撞死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吗?可它明明就是一头扎在雪堆上,然后被夜里的雪几乎盖住了整个身子。兔子身子僵僵的,怪可怜,一点也没有夏天在野地里发现他们时的机灵活泼的样子。
“这大冷天,兔子都冻死了,大概饿得没办法,来村子找食。”娘一边拾掇兔子,一边满腹心事。
弟最高兴,过年了能吃上兔子肉,那是除“二踢脚”之外最让他欢喜的。
小清河上的冰结得老厚,拐子用镐头砸了一个上午,还是空着水桶回来,他说小清河水冻干了。二爷爷下雪前下到河里兜鱼的渔网也提不上来。娘把院门外田野里的雪用水桶盛回来,倒在大铁锅里,烧火融化。
年二十九了。傍晚,我和娘站在村头等爹,把地瓜饭都等凉了,也没见到爹的影子。我们草草吃过饭,吹灭煤油灯,躺在火炕上想爹。
“吱呀”一声,栅栏门响了,爹回来啦!
走进屋里的爹一瘸一拐。他一边口齿不清地吩咐娘端来一盆未融化的雪,一边从身后的包袱里掏出一把山楂,一件通红通红的棉袄,递给坐在火炕上眼巴巴看着他的我们!
爹躺在炕上,娘把雪放到爹僵硬的腿上脚上,用力地搓着;我和弟听娘的吩咐,把两块砖放进灶洞里旺火烧热,包上手巾,放在爹的前心后背。一袋烟的工夫,爹缓过劲来,喝着熬热的地瓜汤,说:“差点回不来了。”
二百多里的雪地,爹是徒步走回来的。这样的雪天,根本没有车通行,开会的同行都已经接受安排,住在外省的招待所里,准备过年以后再回来。爹走了三天,夜里找人家住下,终于在年三十前赶回来了。
大年初一的街道上,我穿着火红的棉袄,走在一群穿着粗格子布上衣的伙伴中间,将整条街道都照亮了。那天,我也留下了人生的第一张照片:远处是小清河坝上的树木,若隐若现,近处是白雪皑皑的田野,我的红棉袄似乎要将整个严冬融化。
整个正月,我没有咳嗽一声!以后,每个正月也都没咳嗽一声。
那年,爹落下了一辈子也没有根治的关节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