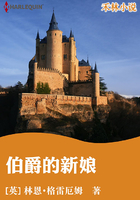胡炎
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夏天。
我的高考成绩很不理想,仅高出本科录取线3分。如果幸运垂赐我,我会走进大学的校门,而一旦稍有闪失,我就会名落孙山。
我的忐忑在逼人的暑热里不断发酵、膨胀,我开始失眠。接着,我的饭量迅速减少,一点胃口也没有。不久,我就瘦得皮包骨头了。
父亲常年在外,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陪爸爸到乡下转转吧。”父亲说。
我不大情愿,但又不愿让父亲失望。
我们骑着车,穿过郊区,一直到了县域。父亲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总骑在我前面。后来,我们到了一条河边。说是河,水却枯了,裸露的河床是一片开阔的沙滩。对岸一片树林,蓊蓊郁郁的。父亲说:“咱们到那儿乘凉。”沙子被日头烤得碳一样烫,脚刚踏上去,就被烧得跳起来。我欷歔着,下意识地调转车头。父亲说:“都大男子汉了,还那么娇气?”说着,顾自在前边深一脚浅一脚走,虽吃力,却沉稳。我无奈,只得跟随。脚上的感觉渐渐只剩下了热,后来,连热也没有了,只有麻木。半个小时后,父亲上了岸,我还有段距离。我不能不钦佩父亲。父亲向我招手,给我加油。我也上岸了,一霎间,我有点想哭。
树林里的确是个好地方,凉爽,而且有风,把疲惫一点点地舔了去。坐下来拿出双脚,才知父亲和我都有了轻微的灼伤。父亲说这算个什么呀,他小时候天天就这样光脚跑,一点事没有。但是父亲还是从附近掐了一些草,揉碎了,敷在我的脚上。过了会儿,父亲变戏法似的从沙子里扒出一粒花生来。这是农民收割遗留下的,父亲说这么大的沙滩,再翻找一遍至少能装满一个麻袋。父亲剥开花生,露出粉白的仁,放进嘴里,轻轻一嚼,由于沙子的烘烤,竟格外的香甜。
我们拣了截树枝,不停地在沙土里翻拣着,果真找到了不少花生,品尝了一顿天然的美味。
父亲说:“现在感觉怎样?”
我笑了笑。我很久没有这么轻松地笑了。
父亲说:“再难的事,一咬牙,也就挺过来了。”
休息了一阵后,父亲还未尽兴。我们骑上车,又启程了。这次,我们进了一片农民收摘后的果林。父亲说:“这树上肯定还有果子,你能给爸爸摘一个解解渴吗?”我点点头。我很快发现了一个果子,但长得很高。我不怕,脱下鞋子爬树。爬到了粗大的树杈上,再爬,树枝越来越细,心里面越来越虚。我不能再爬了,但我多想把果子摘下来。这时,父亲在下边叫我:“下来吃果子了。”我循声望去,父亲的手里竟托着好几个果子!我爬下树,心灰又自惭。
父亲拍拍我的头:“长果子的树不止一棵啊,总有适合你摘的,人活着,怎么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我默然无语。
第二天,父亲走了,我的心情却好了一些。我开始冷静地想一些事情,比如落榜后该怎么走,比如理想的院校未录取该怎么办。我有了思路,心中渐渐踏实了。
一段日子后,父亲又回来了。父亲拎上网,说:“咱们去河里捉鱼吧。”
父亲过去捉鱼捉得上瘾,只是这些年调往异地,少有闲暇,很少下河了。
我们沿着过去经常捉鱼的地方走着。该下网了,可父亲不下。父亲说:
“走,往上游走。”这是我极熟悉的一条河,却又是我极陌生的一条河。人工的防护堤没了,花坛和草坪没了,代之以古朴的桑树、老槐,一人高的藤草,愈来愈分不清路的小径。一股沟汊,两股沟汊……蜿蜒着,交汇起来。水清得像空气一样透明,螃蟹在临水的洞口和水中的石块上悠然地爬行……
我有些沉醉了。
父亲说:“多走几里路,不一样了吧?”
我使劲点点头。
父亲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看看吧,你的。”我接过来,意外的惊喜让我一下子痴得手足无措:我被第一志愿录取了,幸运之神站在了我的身边!
父亲说:“祝贺你,孩子!以后,还得走得再远一些,像这河,追求无止境啊。”
我的泪潸然而下。我突然明白,我刚刚走过了我生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夏天。那是父亲给予我的夏天,让我受益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