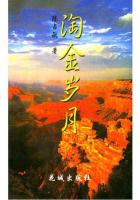江岸
十多年前,我在某大学学习。宿舍里八大金刚,竟有六名来自城镇,只有我和金州来自农村。我来自豫南大别山区黄泥湾,金州来自豫西伏牛山区槐树庄,都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山里娃,都是一副土头土脑的样子,都操着一口让人讥笑的方言。在这种情况下,我和金州的感情直线上升,成了无话不谈、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谢天谢地,我和金州占据了年级总成绩的头两把交椅,引人侧目,也令辅导员大跌眼镜。他宠信的好几个班干部都有功课要补考。成绩公布的那几天,辅导员的脸老是黑着,阴沉得能拧出水来。
第二学期一开学,辅导员就找到我和金州,让我们出任新一届的班干部。
我低着头,不置可否。我岂愿让班务浪费宝贵的光阴?正沉吟间,金州却鸡啄米似的点着头,欣然同意了。后来,金州出任了班级学习委员,我依然是布衣。
此后的金州俨然变了一个人。由于忙于班务,他的学业荒疏了,但他渐渐融入了城镇同学的圈子,博得全班绝大多数人的喜爱,与此同时,他和我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私下里他又屡屡表示,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也想相信金州的话,但总觉有些别扭,总觉我们的交往不如当初那么自然、坦诚。只是每到考试前夕,金州才会抽出时间,专门陪我散散步,聊聊天。考试仿佛是春暖花开的季节,金州仿佛一只准时的候鸟,毫无疑问地栖落在我的身旁,分享我的学习成果。
悲剧终于在大三下学期发生了。
一次开卷考试,金州有事外出,托我替他答卷。那门功课是顶顶乏味的一门课,授课的教授又是一位老头子,蒙一个小老头儿还不是小菜一碟?孰料老头子把两份一模一样的答卷交给了系里。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我几乎魂飞天外。最后,我和金州受了留校察看的处分,“事迹”在全校通报了。从此,我们开始了最为灰暗的大学生活。金州的干部职务被撸下来了,入党的资格也被取消。我呢,丧失了次年的奖学金。我们俩在一起,我总是摆脱不了从内心深处不由自主浮现出来的两只可怜的小老鼠过街的形象。
终于熬到了毕业前夕。有一天,金州突然对我说,我决定了,不能坐以待毙。我不解,反问他,你决定什么了?金州斩钉截铁地说,就是死,我也要死在省会。我垂头不语。金州默默看我几眼,走了,几天后才在宿舍露面。
原来,金州请假回了老家,动员老父亲卖掉了家里唯一值钱的那头耕牛。
据他悄悄告诉我,他还给老父亲拍了胸脯,今日借您一头牛,日后还您一座楼。他就这样拿到了一千多元钱。在当时,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金州终于以清白之身和优异的学习成绩被省直某厅挑走了。而我却背着那个重如泰山的处分,离开了我的大学。辗转半年之后,才人不人鬼不鬼地分到了故乡中学。某一天深夜,我躺在学校潮湿阴暗的宿舍里,总也合不上眼睛,大学期间的一幕幕往事潮水一样冲刷着我脆弱的心灵防线,我不禁泪流满面。
最令我感到痛心的还是金州,我恍然明白了金州和我的友谊存在的全部理由。
金州后来往我家里寄过几封信,我看都未看就撕了个粉碎。我不愿再回首那变了味的友谊。此后我们就彻底断了交往。
前几天,我正讲着课,学校里竟次第开进来一溜小轿车。不一会儿,上了年纪的老校长颠颠地跑进教室,用从未有过的亲切语调大声嚷嚷,新到任的县委副书记,省里来锻炼的,是你大学同学,特地来看你呢,快去。
我狐疑地走进校长办公室,看到一群人簇拥着一个方面大耳、红光满面的胖子,人人脸上都堆着十足的笑,但我一个都不认识。我正想退出去,为首的胖子居然徐步朝我走来,大喊一声,老同学,我是金州啊。
这个胖子是金州吗?怎么可能是金州呢?金州原本是一根“豆芽菜”,烧成了灰我都认识。看着这个大胖子,我一时间愣住了。
金州一行人坐车走后,我突然想,金州借他老父亲的一头耕牛大概早就还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