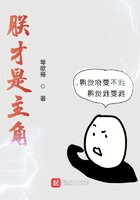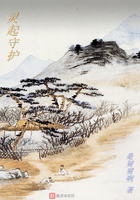郑俊甫
哥终于要定亲了。
一大早,母亲就开始忙前忙后,把哥收拾得利利落落,然后,把一个蓝布包小心地塞进哥贴身的口袋里。布包里是1000元钱。相亲的时候,女方说了,给1000元钱,再买两件衣裳,就把亲事定下来。那段日子,为了这1000元钱,母亲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她先是把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头猪低价给卖了——那头猪还不够斤两,可母亲也顾不得了,又四处磕头作揖求亲戚告邻居,总算筹到了800元钱。还差200,母亲实在没有辙了,最后,母亲把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我正打算去县里的一所中学复读,刚刚跟母亲要了200元钱。母亲犹豫着说:“小小,要不……把你的学费给你哥吧?娘回来再给你筹。”“我不!”我捂着口袋说,“我就不!”我知道,这钱给了哥,我就再也念不成书了。母亲的泪就下来了,母亲哀求着说:“小小,你晚读一年书不当紧,总不能让你哥一辈子打光棍吧?”
我也哭了。为自己,也为哥。
那年,哥已经29岁了。在豫北乡下,跟哥一样大的人,孩子差不多都该念小学了,可哥仍旧单着身。不是哥长得丑,哥的模样周周正正,稍微拾掇一下就像极了电影里的明星。也不是哥的脑子笨,哥读小学的时候,也没少往家里拿奖状。说到底,都是因为家里穷啊。父亲在一家砖窑搬砖,不小心伤了腰,虽然没有落下什么大病,却再也干不成重活了。母亲守着几亩薄田,一年到头打的粮食刚够填饱全家的肚子,哪有钱给哥盖新房啊。辍学后,哥也曾提出去砖窑搬砖,母亲死活不答应,母亲说,宁可过着穷日子也不愿意家里再添一个病人了。几年里,媒人给哥介绍的对象,走马灯似的在我们家的土坯房里变着脸,来的时候都是欢天喜地的,走的时候却一个个撅着嘴,虎着脸。
我成全了哥。那天早上,哥带着钱走后,我们全家都待在家里,急切地等着哥的消息。母亲甚至隔上一会儿就要跑到村头,看看哥回来了没有。天擦黑的时候,哥终于回来了,一回来,哥就哭丧着脸蹲在院子里的枣树下,一言不发。母亲不停地追问,问了好几遍,哥才嗫嚅着说:“娘,我把钱丢了。”“在哪儿丢的?”母亲一惊。“在城里,买衣裳的时候,可能遭到贼了。”哥说。
哥的话像一记闷棍,母亲立时就瘫在了地上。屋里的父亲佝偻着腰冲出来,顺手操起一把扫帚就往哥的身上拍。哥不躲,哥就那么呆愣愣地蹲着,承受着父亲暴风骤雨般的拍打。打了一会儿,父亲忽然丢了扫帚,痛苦地蹲在母亲身边,无助地扯起了自己的头发……
第二天,媒人来了,问哥为什么不去送衣裳和钱。母亲苦着脸说明了情况。媒人摇了摇头,说:“老大咋这么命苦哇?”顿了一下,媒人又说:“可这事咋办呢?那边说了,三天送不去衣裳和定亲钱,这事就……”媒人看看哥,又看看母亲,没有再说下去。母亲强打着精神笑了笑,说:“他婶,你放心,三天里我一准把钱凑齐。”
母亲又开始借钱了。从早上天不亮出门,一直到屋里亮起了灯,母亲整整奔波了三天。三天后,母亲坐在桌前,把借来的块块毛毛都摊在桌上,和父亲一遍又一遍地数着。一共315元,离1000元还差得远呢。我听见父亲用手捶着桌子,恨恨地骂了一句:“龟儿子,让他一辈子圈在家里算啦!”
媒人又来了,母亲拎出一篮准备好的鸡蛋,央求到:“他婶,你能不能再去说和说和,让她们缓上一段日子?”媒人没有接,媒人瞅瞅那篮鸡蛋,叹了口气,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登过我们家的门。
过了几天,哥又提出要去砖窑搬砖,母亲仍旧不同意。可这次哥似乎铁了心,哥说:“娘,你总得让我把丢的钱挣回来吧?”母亲拿眼光扫着父亲,父亲正抽着一袋旱烟,袅袅的烟雾滑过他清瘦的脸。沉吟了一会儿,父亲终于说:“还是放他去吧,总不能真的让他在家圈一辈子吧?”
哥收拾行囊走了。走的那一天,哥悄悄地把我扯到一边,从怀里掏出一个蓝布包递给我。我问哥是啥?哥笑笑,什么也没说。
哥走出去好远,我才想起打开那个包。打开后,我就愣了,蓝布包里包着的正是母亲交给哥的定亲钱!钱上面还压着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条,纸条上是哥的字:小小,好好念书吧。
我对着哥的背影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哥——”,就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