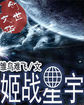第二天,淮安府大街。
吉成和夏谨言两人随意漫步在这个因漕运的发达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大都邑,虽然街头巷尾的人声鼎沸,勾栏酒肆的妩媚妖娆,贩夫走卒的大声叫卖,各色衣衫的普通百姓匆匆的步伐,无不显示着这个城市的繁荣。可是,在吉成的心中,依旧是一片宁静,在这个世界多过一天,自己感觉就跟这个世界多融入了一分,后世的经历慢慢变成了一种怀念,回不去了。昨日有缘结交了这么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倒是意外收获。一整夜的彻夜长谈,抵足而眠,让吉成第一次感受到古时士人至诚至信的风骨。不比后世,面赤酒憨之际,比亲兄弟还亲,第二天翻脸不认人之事比比皆是。忠孝仁义的悌礼,在大明士子心中的地位,还是根深蒂固,无法撼动的。当然,不去提那些投降派、软骨头。
吉成就这么默默地走着,在夏谨言看来,这种有些呆呆的神情,有些深邃。男人玩深沉,自古而今对女人来说,始终是一种大杀器。让夏谨言越发好奇的是,自己始终无法看透眼前之人,貌似纨绔的富家公子,昨天的谈吐却很让人意外。在她看来,自己见过的男人没有上百也有几十,无一不是被自己一眼就看穿那些个死德行,有粗鄙厚颜的,有装腔作势的,有仗势欺人的,甚至还有鸡鸣狗盗之辈,实在是不堪其扰,这也是夏谨言死命要跟父亲一起出游的原因。
眼前的这位外表看起来呆呆傻傻,但偶尔又有些街巷地痞恶习之人,却时不时地显露出如此深邃的眼神,让这位姑娘的心,居然有些别样的感觉,是鄙视还是不屑呢?一个与父亲,与大盐商有共同语言之人,好像不能随便鄙视吧?说是略有好奇和崇敬?让本姑娘对一个江南偏隅之人崇敬,无疑是痴人说梦。再或者说是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切,还是杀了本姑娘吧,这辈子托付给如此匹夫,两个字,糟践!
各自想着心事的两个人,胡乱地穿过一些大街小巷之后,在同一时间放慢了脚步。这位姑娘因练武而具备耳聪目明,告诉了她周边的危险。而那位街巷地痞,凭着多年的混迹江湖,似乎也感觉到了周遭不寻常之处。
他俩所处的位置这恰巧是从一条大街,刚刚拐进小巷,距离到达另一条大街还有几十步。巷子不宽,二三个人并排通过还有点困难,原本巷子里面有两三人行走,可是走到巷口都是快步跑走了,似乎在躲避着什么,巷口远处也好像有人在指指点点。
果不其然,前方巷口的光线忽然一暗下来,两个铁塔似地大汉出现在眼前,而巷子的后方,另一个大汉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两人。
来者不善呐,这架势看起来,对方显然是极富打斗经验,地点选择,时间选择,都是刚刚好。不过,在精心的策划,在实力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吉成心里并不害怕,这样的街头斗殴早就见怪不怪,最多自己也受点伤呗,那老头的女儿在这里,虽然没见过她出手,可老头动起手来那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强悍太深刻了,吉成侧过头,看了一眼这位在大街上一路没说满三句话的清丽美女,在她的眼睛里似乎闪过了一丝笑意,吉成心中冒火,这小丫头难不成想看我的笑话?
前方的两人开始动作起来,只见他们一高一矮,高的那位步伐稳健,面色肃穆,就似欠他好多钱似地,矮小的那个,脚有点跛,一脸的淫笑,盯着夏谨言上下乱看。后面一人,自从出现以后,并没有太大的动作,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似乎是这三人之中领头之人。
夏谨言被那矮个子无礼地乱瞄,顿时火冒三丈,冷哼一声道:“哪来的狗屁倒灶的东西,污了本姑娘眼睛,真是晦气!”
此言一出,在场其余四人皆惊,那三位狗屁倒灶之人好不容易等了一上午的肥羊,这两个小年轻四处乱逛,一看就是外地来的富家子,本来吃定他们的,这女子一声吼,看来这茬似乎也不太好惹。不过事到如今,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二个铁塔大汉一溜小跑就冲了过来,夏谨言出手了,真快,快如闪电。她并没有抽出背后的短剑,赤手空拳,以一敌二。只听得砰砰的闷响,几下子过后,两个大汉已经处于下风了,眼看着就要被踢飞。
吉成还未反应过来,背后的脚步声逐渐变大,夏谨言偷空瞟了一眼吉成,那眼神充满了不屑、挑衅和看好戏的的感觉。这女人,简直不可理喻,明明可以帮助自己,嘿,非要看自己的好戏,这些事情的发生其实也就是几个呼吸之间,吉成感觉后面一拳就要打来,此时自己才刚刚反应过来,只是本能的一个侧身闪避动作,跨出一脚,略一扭腰,正巧堪堪避过那位壮汉的虎拳,急智之下,吉成的脑子忽然闪过了后世格斗教科书中的动作,紧接着,吉成双手抓住伸过来的一只壮手,往自己脖子边一绕,后背一拱,腰部用力,一下子就把那壮汉一个背包翻了过来,这壮汉根本没想到这年轻人的手法如此迅捷娴熟,一下子就吃了个大亏,甩到地上之后,正准备挣扎着爬起来,可吉成哪会让你这么便宜,狠狠地一脚提到壮汉小腹上,壮汉吃痛,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冒了出来,别说爬起来了。这个时候,吉成才发觉,自己的这个躯体素质还真是好,身强力壮,力道十足。
那边的两个地痞,在夏谨言流星蝴蝶般的身影掠过之后,一人脑袋挨了一记肘击,另一人肋部却是着着实实地挨了粉足一脚。现在的三人都坐在地上痛苦呻吟,看来这笔买卖是做砸了。
这时,夏谨言回过身来,有些奇怪地看着那边仿佛没事人一般吉成,虽说以一敌二,可自己也是费了点小功夫的,毕竟这两个壮汉看得出来也是混江湖的,打斗的经验可是不缺的。而吉成这边,打到一个人貌似也很迅速。本来夏谨言就已经想好了,就算吉成不被这人打倒,至少也是一番缠斗,还等着看这家伙的好戏。不过眼前的景象,却是吉成一招制敌,干净利落,没有任何拖沓的痕迹,吉成的脸上也不红气也不喘,只是悠悠着站在那边,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实际上吉成是惊魂之后,正在那边深沉地回味着自己那几手,没想到自己的潜力这么出色。
夏谨言正准备出言讥讽两句,吉成却侧过脸去,朝着地上的三人,脸色一沉,怒道“兄弟,哪条路上的,是认错人了还是想劫财啊?”
地上的壮汉还没缓过劲来,忍着疼痛:“好汉手下留情,我们三个也不是坏人,只是迫于生计,实在是没得吃,好汉,我看你们形单,又带了个姑娘,便想讨口饭吃,求求你放我们一马吧!”
“哼,本公子今天心情好,暂且放你们去,好好认认我这张脸,见着就滚远点!”
“是,是是,麻二李三,快走,快!”其余二人一听,如蒙大赦,手脚并用,爬起来就往巷口子跑去,嘴里还不停喊着哎呦呻吟着。
其实刚才的两人,看到这姑娘的神色临危不惧,已经觉得不太对了,常常混迹江湖,再一看那姑娘脚步移动的步伐,就知道这姑娘是练武之人,只是苦于大哥的命令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吉成回过头来,用不屑和挑衅的眼神同样地回敬夏谨言道“这位高手,以一敌两啊,在下佩服的紧!”
夏谨言心中本来倒对吉成观感有些转变,听到这调侃之语,俏脸微变。不过,吉成忽而又收起那戏谑的神色,一脸虔诚道:“姑娘,前方巷口,好像有座御鲜楼,就给个机会,让在下略备小菜,为姑娘压压惊吧。”
夏谨言看着吉成的脸色和语气急剧的变化,噗嗤一声,低骂了一声:“死呆瓜!”那种娇艳无比的神态,看的让人眼珠子都要差点要掉出来。
夏谨言在杭州,论武功,等闲几个好手,根本就不是对手,就算是卫所教习,以一敌二都也没有问题,父亲曾经邀请杭州卫指挥使司的家将和自己比试过,若不是纯比气力,武艺技巧根本就不落下风。论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自己也能在杭州的才子圈内数得着。由此造就了夏谨言高傲目空一切男子的性格。
而当夏谨言这两天来面对眼前的这位时,心中可就不那么平静了,主要是实在看不透这家伙,说到谈古论今,居然能与那位大商人兼士子的杜老头侃侃而谈;再说两次遇突变,看似偶然的出招,却每次都化解了杀机,他的言辞沉稳,但又不乏幽默,这样的男人,不多见,不曾见。
夏谨言心念电转,哼,都两天了,也没见这么大方过,今天是怎么了,我还偏不领你的情,旋即,只见她拉长俏脸,狠狠地朝他剜了一眼,正要开口拒绝。不过吉成早已快步走到前面,冲那门口拿着条白布巾东张西望地招呼客人的小二就喊道:“小二,来个雅座,楼上的有吗!”小二一看有客人上门,咧起大嘴就答道:“有,有!客官,楼上雅座!请!”夏谨言一看这形势,大庭广众的,翻脸拒绝自己又做不出来,只能使劲一跺脚,极为不情愿地跟了上去。
杜府。
杜首昌与两位在正堂喝着茶,只听见似乎院子的侧面喧哗声渐起,看这方位,应该是侧厢房外,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杜府的关老管家匆匆来报,费二管家被人杀了,尸首就躺在西厢房后面,老杜二话不说,一撩袍子,心急火燎地就向外走去。这关、费二位管家,均是为杜家忠心耿耿效力十几年的老伙计,而这费管家是老杜家中的外交官,所有对外联络、公关、迎来送往、家族祭祀都由这个费管家负责办理,为杜首昌鞍前马后这么多年,主仆二人可谓是感情极深。这关老管家年岁已大,一直陪在杜首昌的身边,做些简单的服侍活计,也算是杜老的心腹了。这时也紧紧地跟在老杜后面。
吉成二人也是一惊,没有多想,也跟在了老杜后面,一探究竟。几人刚走到西厢房边,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夏谨言眉头紧皱,赶忙抬手捂住口鼻。西厢外边的一具男尸,正是杜家二管事费进的。吉成与夏谨言不约而同地凑过去看一眼,只见杜家的下人正在准备敛尸,杜首昌只是一副悲痛之情,站在那里也不知所措,紧握的拳头上青筋爆出,可见费管家的死引起了杜老的极大愤怒。
忽然,吉成低喝一句:“杜先生且慢,”老杜不免一怔,有些疑惑地看了看吉成,然后示意下人退开少许。在这乱世末期,官员腐坏堕落至极,整个官僚系统反应迟缓,一般大户人家出了事情很少报官,报了官查不出个头绪不说,供官吏查案的吃喝应付就得花去不少,甚至名为破案,实为借机索要钱财,也因此一旦有事,基本都由家主决定,私下草草处理。所以一般这些人命案件没有官府专业仵作和捕快的勘察,就更难查出死亡原因,更别说抓住凶手了。这件事情不用说,作为杜老家的规矩,无非还是这样,死了人,不管是自杀还是他杀,同情一下罢了。
吉成蹲下身去,现场的脚印十分凌乱,这个时代根本就没有保护现场一说,看起来找寻线索极为困难。费管家胸口一大滩的血迹,略略发稠发黑,看来死亡时间已有至少一个时辰。
忽然,吉成发现,尸体下面的血迹是由西厢房的后门口歪歪扭扭地处延伸出来的,这就有点意思了,看来这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吉成站起来看了老杜一眼,道:“杜先生,请随我来,其他人暂时不要动尸体。”
西厢房是供下人休息和放置工具杂物的地方,靠里还有一张简单的木板小床,供临时休息之用。吉成来到小床边,这地上留着一小滩血迹,很明显,这里才是杀害费管家的第一现场。可为什么,凶手要把尸体拖到厢房外面呢?
吉成道:“凶手是个女人!”
老杜惊讶地看着吉成,在他看来这简直是神了,一会儿工夫居然能够推断出凶手是女人!顿时就问道:“小友,这何以见得?”
吉成好整以暇,道:“在我看来,这个女凶手杀人之后,知道天之将黑,一些下人会将白天干活的工具扔到这小厢房内,凶手怕人看见尸体,于是就想先把尸体拖到厢房后面。因为一般人没事不会跑到厢房后面去,同时,厢房的后方不远就是侧门,凶手想趁天黑把尸体搬运出去。”
说罢,吉成拉着杜老来到一长条血迹旁边,指着其中几个似乎因停顿而多出来的几滩血迹,说道:“如果是男人,费管家身材矮小,完全一次性就拖拽到位,而地上这几个停顿,说明凶手力气不大,需要使劲拖拽,而拖了一程,需要歇息一下,从而在地上留下多滩血迹。”
杜老越来越佩服这位小友的明锐洞察力,只听吉成继续说道:“另外,杜先生请来看费管家的伤口,伤口很小,致死的伤口就在胸口,居然正中心脏。伤口是什么造成的呢,我看,刀剑不肯能造成的这么小的创口,倒像是女人的发簪!”
杜首昌这下有点不可置信了,惊讶地看着吉成,这就算是官府捕快仵作勘察,也不一定能这么快还原凶杀情景。吉成勘察之细致,眼光之锐利,实在是居于同龄人之冠。
“行之高见,老朽佩服!”,吉成微微一笑道:“杜老且慢给小生戴高帽,凶手还没抓到,请杜老将所有府门关闭,许进不许出,我们来让凶手自己现形!”
“这……”杜老更加不可思议地道:“难道小友认为凶手杀了人之后,还会呆在我这宅院之中?“
吉成胸有成竹地说道:“杜先生请先听小友安排,一会必有分晓。”
不到一炷香的功夫,只听见护院首领和两个护院大汉,扭着一个妇人进了大堂,杜首昌一惊,站起身来,这不是后院的那个专职洗衣的妇人嘛。一看这架势,杜首昌心中火起:“你这个贼妇,说,是不是你害了费老,?!”右手猛拍桌角,桌上的上好乌龙茶撒了半张桌子,本来在大堂一角蜷缩着的那只黑猫也一下吓得怕了开去。
大堂的那个妇人脚一软,扑通就跪倒在地:“老爷,饶命啊,我说,我都说,奴婢也是没办法,都是家里那个死鬼,欠了一屁股赌债,被人追杀上门来啦,老爷,求求你,饶了我吧!
老杜怒极,上前一步,狠狠一脚把妇人踹翻在地,老杜歇斯底里吼道:“你这刁妇,欠了赌债就可以随便杀人!?”
这时的老杜哪里还有大商人的睿智,士子的风流倜傥,不过这也难怪,毕竟老杜跟费管家感情至深至矣人之常情罢了。
妇人吃痛呻吟,又是哭哭啼啼,嘴里断断续续地说道,“奴婢也是一时糊涂,家里那个天杀的有一次说海棠什么的,曾经许给他诺言,只要帮他们办好这件事,赌债就免了,否则就是灭门全家!杜老爷,奴婢错了,奴婢怎么做下了这丧心病狂的事情呢这!”说完嚎啕大哭,震彻屋瓦。
海棠门?!听到这个词语,吉成、夏谨言、老杜瞬时六眼相对,每个人的神情都有些复杂。杜首昌沉吟着,这费管家是在杜家可是操持着家族生意的,难道是自己又在哪方面得罪了海棠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