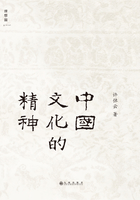“舻声听未了,山水送孤帆;对面青如画,回头绿满岩。半空云袅袅,一带水巉巉;船尾澄流迥,峰腰旭照衔。青疑留古岸,翠欲上征衫;流响惊凫雁,浓荫郁桧杉。”吉成一席灰袍,双手负后,昂然矗立在船头,极目眺望着这两岸如诗如画的景色,内心一片安宁。
离开江阴县已经四天多了,客船进入淮安府的治地。淮安,府治于山阳县,京杭大运河从其境内穿过,发达的水系,造就了淮安漕运的繁荣。在鼎盛时期,淮安府与江南的扬州府、苏州府、杭州府并称运河线上的“四大都市”。淮安府还有一个传统,就是畜牧业,养马也给淮安当地创造了大量财富,到这明末时期,淮安府依旧保持着这个传统的产业。
吉成一行所乘坐的,是运河里较为最常见的一种客船,长约数十丈,宽数丈,最中间是个较为宽敞的舱室,主要是供客人用餐、会客的公共区域,放置着两个小茶几,几个圆凳。公共舱两边各有几间船舱,是旅客睡眠休息区,船舱虽小,不过里面的床铺设施却是井有条。船头船尾部分别作为驾驶,厨房等船工的使用区域。
吉成正与周恒生坐在茶案上闲聊。这时,舱门外似乎有个影子,一下遮掉了部分光线,就见一位老者探进头来,笑眯眯地朝着吉成道“不知老朽能否借宝地一用?”
吉成闻言转过头,只见一位精神矍铄,面色和蔼的老者正看着自己,他立即做了一个请的姿势,道:“老先生这边请,此地并无他人!”
老者微微一笑,大大方方地跨入船舱,只见这位老者身着一席宽大的过膝青衣,头戴方形布帽,下颌的银须随风微动,深深凹陷的眼眶中,是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目光清澈柔和,给吉成二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仙风道骨。
老者一捋青袍,大喇喇地就坐到了吉成的对面,还没言语,自顾自地端起桌上茶壶,为吉成和周恒生各斟满一茶,又为自己的茶杯斟满,很陶醉似地抿了一口。接着老者抬起头,目光如炬地在吉成脸上逡巡了一遍,让吉成不免一阵恶寒,这老头怎么古里古怪的,我的脸很招人喜欢嘛?
吉成内心嘀咕,为了不使场面继续尴尬,不免就主动问道:“在下吉成,敢问老先生尊姓?”
老者神色不动,抬起茶杯道:“相逢即为缘,老夫在此先敬年轻人一杯。”
吉成怔了一怔,老者扫了自己的面子,居然避而不回答自己的问题,反而还向自己这个年轻人敬茶,真是让人匪夷所思。不过吉成没多想,回道:“不敢,先生请!”说完就端起茶杯,仰头一饮而尽。
老者既然在旁边,吉成与周恒生也不好过多地谈论家事,两人见老者没有多话,就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老周在旅途中的一些趣闻了。不料,这些趣闻倒是似乎颇感兴趣,开口道:“这位老弟,还去过北地?不知北地是何种状况呢?”老者摸了摸自己颌下的银须问道。
老周长年在外,与人打交道自然是拿手就来,道:“总的来说,关内比关外好,关外比辽东好。”
“噢,关内比关外好,这个好说,关外跟辽东是什么个状况呢?”老者追问道。
“老先生有所不知,在咱们万历老皇帝和天启小皇帝手中,关外辽东大片沃土,都一直属于我大明天下,只可惜自从那努尔哈赤“七大恨”拥兵造反以后,女真族的势力越来越大,关外土地一天天地被鞑子蚕食,到今天,我大明实际能控制的地盘不过锦州城方圆数数百里,就这样,还时不时要受到鞑子的袭扰。”
老者逐渐收起那和蔼的笑容,不自觉地就露出一副严肃的表情,有些让人望而生畏的感觉。
周恒生说得起劲,也没太在意,喝了一口茶,继续道:“女真族在努尔哈赤手中,日子过得艰苦,毕竟是游牧部落,靠天吃饭,居无定所,资源又极度匮乏,直到最近的十几年,四贝勒皇太极当权之后,才开始学习中原文化,逐步汉化,推行耕种,修生养息。到现在,女真族的整体实力越来越强了。”
周恒生自顾自地说着,一点也没在意身边两人古怪的神色,当然,就算在意,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话已经深深地勾起了两人心中各不相同的记忆。
老者忆起当年在辽东征战多年,对北地的严峻局势不可谓不清楚,又一直跟在德高望重的阁老身边,多多少少对国家大事,军事战略总有些了解。卸甲归田身处杭州的这些年来,冷眼看着那些所谓的上层精英们,日日寻欢作乐,灯红酒绿,醉生梦死地度着那看似太平的虚幻光阴。为官者上下窜通,沆瀣一气,贪污弄权,无法无天。为商者,勾结官府,为虎作伥,无恶不作。这些站在所谓大明金字塔最高层的精英们,根本不知在那寒风凛冽,人烟寂寥的辽东大地,有个强大的敌人正在逐渐强大,虎视眈眈。阁老督师边疆辽地军政民政多年,自然是理解极为深刻,曾有诗云:“春懒荒台草亦稀,幔亭风日满征衣。最怜王谢乌衣巷,无复寻常燕子飞”,由此可见一斑。
而对于吉成,对明末这段大厦倾覆的历史也有所了解。这时让他没能想到的是,一个走南闯北的生意人,也能够把形势能够看得这么清楚,那么在大明朝的庙堂之上的精英们,有那么多的消息来源和渠道,对危机难道真的是视而不见,或者还是自顾自身利益,这大明江山是朱家的,管他是否会亡国亡族呢?
耀眼的阳光没有受到云层阻挡,直射在微波荡漾的水面上,偶尔有几艘运粮的漕船驶过,船后的水波形成一个逐渐扩大的三角形,一浪一浪地向吉成的客船滚来,原本平稳的船身,也随着波纹的传来,开始颠簸起来,水面上一大片金光也因此而变得无数个破碎的小光点,耀人眼球。这个时间,正是离吉成诸人的午餐结束不久,吉大公子也就懒洋洋准备就在这船舱内小睡,周恒生顺手拿出了一个羊绒靠枕,递给吉成。谁也不会想到,危险正在一步步地靠近。
就见接近船舷的水面下,似乎有一团黑色在逐渐变大,接着,水面一下子呼啦分了开来,一个全身黑衣水靠,满脸麻疤的汉子一手搭着船舷,正在使劲往船舱中窜来,嘴里叼的一把精钢匕首寒光闪闪,那慑人的寒芒,让不懂兵器的吉成也清楚地知道,要是被这样的兵器哪怕是撩出一条小伤口,那也将会是痛彻心扉。
黑衣人就要爬上船舷,右手已从嘴角边取下匕首,手臂微缩,正准备蓄力刺向吉成,这些个动作一瞬间完成,让人来不及思考,要是常人,遇到如此变故,一定是目瞪口呆,来不及应变,此时的吉成也不例外,这一刻,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坐起身或者退后避让,仓促之间,吉成只是下意识地将手中的羊绒靠枕往黑衣人的脑袋扔了过去,黑衣人刚刚浮出水面不久,大量的水珠还挂在面孔上,看实物一时尚不真切,只觉眼前一黑,无法判断是何物飞来,万一是坚硬器物,砸在脑袋上就不得了了,于是下意识地把头一偏,以避开来物。正是这一瞬间的机会,给了身旁周恒生应变的机会,他江湖经验丰富,顺手就抄起身边的圆凳,使尽力气往黑衣人砸去,一阵闷响,正好砸中黑衣人胸口,黑衣人吃痛,迅速下潜。
而船的另一侧,有两名黑衣人趁着这边的打斗,湿淋淋的从船帮上爬上来,船舱中的那位青衣老者,似乎船上的变故跟他毫无关联,临危不变,在摇晃中还在继续喝着那杯身前的茶水。不过这位老者的眼神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是一种特有的气质,目光锐利,表情肃杀,一只捏着茶杯的手,青筋隐隐,眼看着就要发动。
吉成思绪混乱,想着这才穿越了二个月,小命就要葬送在这条运河里,这波澜壮阔的大明末世自己可还没有经历够呐,胡思乱想之际,,感觉有阵风在身边响起,接着眼睛里闪过一片青色,就好似后世电影中的片段一样,砰砰砰砰几下子闷响之后,青衣老者已经站定收手,然后慢慢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就见水里飘散开一片血红,几团黑影慢慢地远离,其中有一个似乎漂浮在水面上,被同伴拉着往远处游去,直至不见踪迹。水面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一片金光粼粼。
船老大好一会才敢冒出头来,来到船舱,颤颤巍巍地问道:“客官,可有受伤?”
青衣老者脸上又显现出那招牌式的微笑,船老大一看,便安下心来,刚才的打斗自己也偷偷的瞧到了,这年头山匪,水匪层出不穷,遇到这种事情,就是船老大倒霉,客人被劫了财,船老大总会赔一些,这一趟就会白跑了。这次要不是这个老者在,估计自己又要遭殃了,这次不知哪来的蟊贼,一般的水匪可是平时已经打点好了的。
青衣老者也不管船老大,朝着吉成微微点了点头,示意吉成过去。吉成也是惊魂未定,只是不在脸上表现出来罢了,随即便站起身,拍了拍溅到衣裳的水迹,坐到了老者的桌前,拱起手来就要致谢。老者抬手摸了摸嘴下的青须,打断道道:“这位后生,不用谢我,不过我看你遇事还算冷静,反应也很正确,不知是否练过把式呢?”
吉成这时候对老者是发自内心的尊敬了,回到:“老先生,在下不曾习武。”
“噢?那是相当的不错了,刚才的那一刺,速度快,力量大,普通人一般都来不及反应,你却能在一瞬之间把枕头扔过去,也算是自己救了自己了!”
吉成有些尴尬,这自保的动作,怎么从老者嘴里说出来,好像是自己很有武学的潜质似地,心里撇了撇嘴。
“后生,你可知道这些是什么人吗?”
“在下不知,还望先生赐教!”
“是海棠门。”老者不动声色的答道。
吉成一怔,怎么又是他们?随即又问道:“敢问前辈,您怎么能看出这伙人来自海棠门?”
老者似乎很满意吉成的问话,颌首道:“恩,海棠门的宗旨是兵贵精而不贵多,这3人的身手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手,当然,在我面前,就不值一提了。不过,用来杀你,是绰绰有余了。”
“噢?先生教我。”
老者并未停顿,自顾说道:“这些人平时有自己正当的营生,只是在肩膀处纹有黑色海棠花的标记,刚才被老朽抓破手臂衣物之后,我看到了这个标记。”
说完,老者眼神一凛:“你这后生,怎么会得罪他们呢,他们平时不会轻易出手,轮得到他们出手的事情一般都与自己的商会有关,其他的事情是不会去沾惹的。”
吉成一脸苦笑,道:“老先生,其实我自己也是一头雾水,一点也搞不明白啊。”
老者略有疑惑地看了看吉成,又道:“海棠门,之所以用海棠花命名,是因为海棠花的花高贵美丽,不过可惜的是没有香味,暗合着那主事之人的行事风格,既高贵又低调。海棠门依附于江南富商集团之下,没有大的利益纠葛,他们是不会出现的。这件事在江湖上也很少为人知晓”。
吉成心中一直在打鼓,这件事肯定又是跟那鲁三财有关,不过这些细节可不能为眼前的这位老者所知晓,只能先搪塞一下了。但是,听老者这么一说,自己的那么点事,用得着启用这么厉害的组织来暗杀自己吗?难道这里面另有隐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