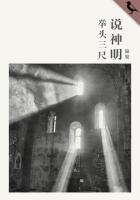王清明有些激动,或者说兴奋。这种感觉是突如其来的,夹杂着不安。当高杨丧母的消息传来时,他心里一紧,荒凉一片,像是遥遥望见了自己逝去的母亲,以及母亲逝去后那些难挨的日子。而那些日子,只不过像是秋风肆虐了很久之后,忽然降下了寒霜,使原先的荒凉变成了冰凉。他有一个混日子的父亲,有一个贤德的母亲,可是母亲却早早地弃他而去,那种深入骨髓的凉意,不是他人能够真正体会的。当他身边竟然也出现了这样一个时,难免不使他感同身受、同病相怜,甚至不再对这小子有轻蔑之心。然而,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高杨被绑架了!这不像是真正的生活,或者说,它扰动了生活这摊阴凉的水,反射起了片片白光,所以,才使他年轻的心兴奋起来吧?——生活总得发生些变化,来使处身其中的人感觉到自己活着,这是人们普遍的心态吧?虽然,这时候,在王清明的心里,高杨那么可怜!
那天早上接到勒索电话后,王胜利就离开洗浴中心回了家。第二天临近中午,他儿子王金钟给王清明打了个电话,让他出来一趟。王清明出了洗浴中心小院儿,来到小区主路上,在前排楼下看到了堂弟的那辆奥拓。他走过去,堂弟正缩在车里抽烟,抖抖索索的。
“啥事?”
“你先进来。”
王清明从另一侧上了车,王金钟给他支烟,点上,说:“哥,高杨的事你知道了吧?”
王清明点点头。
“咱抢那二百万去吧。”王金钟说。
“啊?”王清明愣了一下。有个念头一闪而过,他隐隐有些觉得绑架高杨的就是王金钟,可马上又抛掉了这个念头。
“二百万呐哥!那是我爸多少年攒下来的!咱跟着我爸的车,等那帮孙子把钱拿上了,咱再把它抢回来!不能便宜了那些孙子!”
“没报警啊?”
“报了,谁知道那些警察能不能把钱拿回来呢?”
“那大爸知道这事吗?”
“肯定不能让他知道,咱自己去,还有我警校的同学赵宇和黄立峰,我已经叫了他们了,一会儿就到。”
“那怎么抢?”
王金钟扯开羽绒服胸襟,露出警服来给堂兄看了看,又从腰上取下一支枪来,举到王清明面前。
王清明把枪接过来,说“你们警校还发枪?”
金钟说:“发个屁,看不出来吧?这是仿真枪,能打破玻璃。——我吓也要吓死他们!”
清明说:“那他们要是有真枪呢?”
金钟说:“到时候再说,随机应变吧。”
俩人就开车出去,到一家小饭店去等援兵。
王金钟在他爸的车上装了电子跟踪器,带监听的,他不想被父亲发觉他在跟踪。警察也在他爸的车上装了跟踪器,他还得时刻注意不与警察撞在一起。
昨天,王胜利到家时,王金钟和母亲、姐姐都还睡着没起,后来金钟听到父母在客厅大声说话,刚开始还烦他们吵得他睡不好,后来就渐渐听了进去,而后,他的小舅舅,高杨的父亲就被叫了来。
王胜利狠狠地抽烟,把客厅里抽得烟雾缭绕。虽然说,高杨是在他的店里干活,还叫他姑夫,但是绑架了高杨向他索钱,却是让他不能接受的——我跟他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凭什么?!他老婆也不能接受,可被绑的终究是她弟弟的儿子,她却又不能不管,就把弟弟叫了来,商量怎么办。弟弟来了,苦着脸。他媳妇刚死,而且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死的,儿子又不见了,心里压抑着,几天没有休息好,正发着烧,脸颊红热,嘴唇开裂,一副又萎顿又局部兴奋的样子。他当然没钱。亲戚里面也没有那么有钱的,除了姐姐。那些人的刀扎得可真准哪!姐姐尽管也说她没那么多钱,可是为了那条命,借也得借够啊!——“不知道高杨一辈子能不能挣这么多钱呢!”姐姐说。弟弟似乎有点麻木了,没反应。那怎么办?大家想办法。报警啊!
警方有理由怀疑绑架者跟那些贩卖管制药品的人有关——高杨毁了他们的钱,他们就用高杨的命来换,才不管这钱由谁出,关键是要出得起!绑架者给了王胜利一天半的时间筹钱,第二天下午听指示。警方说你拿上钱我们跟你去,咱尽可能一举破案。于是,这天午后两点钟,大家就一起上路了。
赵宇是骑摩托车来的,黄立峰开的家里的奇瑞,王金钟打量了打量,说,还是开我这破车吧,不然绑匪会怀疑咱是警察。赵宇说,你就不怕他们拿了钱你追不上?王金钟说,屁大点儿的地方,我就不信他们能跑哪儿去?奇瑞比奥拓也快不了多少。定了这事,几个人就回饭店吃了点东西,等着那边传来消息。当王金钟的手机里传来王胜利和高松坐进车里的声音后,王清明就跟着他们钻进了奥拓,坐在副驾驶上。
车是往城外开去的,先上了环城路,后进了高速,再往前走,盘到了一条破败的柏油路上,一直往西山扎去。王金钟没敢跟得很紧,但是远远的,他认出了高松平时开的那辆金杯。家里还有辆凯美瑞,他给两辆车都装了跟踪器。警方不仅在父亲的车上装了跟踪器,在装钱的小行李箱里也装了。王金钟让车里的人注意外面哪辆车像是警方的,好避开他们,但视野里的车都不像,偶尔一辆车超过他们,车里也都坐的不像警察。西山是座煤山,虽然已近年关,但进出的车辆并未绝迹。
王金钟只是简单地跟王清明说了下高父去他家的事,但是就那样一个简短的过程,却在王清明的脑海里敷衍出了整个情状,从吃饭到上路,他都一直没能摆脱对那个情状的描摹。那太像是他自己的经历了。
家里本来就不富裕,父亲又是个沉湎于麻将没有担当的人,母亲患了乳腺癌之后,这个家顿时逼近了将要坍塌的悬崖。父亲求过人,回到家里讲起经过来痛哭流涕。然后他就让王清明带着妹妹去求人。王清明硬着头皮走了一圈亲戚,倒也得到不少的同情,可是面对这样一个烧钱的病,很快那点同情就被蒸发了。母亲做过一次手术,而后就放弃了治疗。不久,她便撒手人寰。王清明不知道母亲的病到底还有没有得治。他知道,有些女明星就是死于这个病,比如梅艳芳,可是他也有病而不死的例子,他有两个同学的母亲就得过这个病,在一次次的化疗之后,竟然挺了过来,所以他认为,要是有足够的钱,母亲也不一定就会死去,起码,不至于这么快就死去。这件事,让他从反面体会到了自尊的含义。——当时的父亲是没有尊严的,此时的高父,一定也陷入了同样的窘境。
他们几个人在车里能够听到王胜利与绑架者的对话,王金钟打开了监听手机的扬声器。道路上满是裂纹,散落着煤渣。在山岭背阴的一面,有片片边缘起伏的残雪在灌木丛下静静地伸展,风从灌木丛中穿过,稀稀疏疏插在雪中的小草不为所动。绑架者问王胜利,你们到哪儿了?然后说,往前大概走多远,往哪儿拐,再往前走多远。听起来,绑架者是以逸待劳,以静制动,并没有监视着王胜利。可是,到了地点,他们就一定不会不露面了。这时,有一辆青色的丰田霸道长按着喇叭超过了他们的奥拓。车前盖两侧贴着红底黑字的小对联,一边写:日行千里路;一边是:夜走八百程。黄立峰笑道,日,这是牛车还是马车?怎么这么土?这不寒碜霸道么?赵宇说,你不看还有横批呢,贴在车牌上。黄立峰道,一路平安啊。赵宇说,那是后面,前面是百年好合!俩人一阵笑。笑完,赵宇又道,这小煤老板刚嫁完闺女又急着过年了。黄立峰说,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是娶媳妇是嫁女哩呢?赵宇说,小煤老板都生的是女儿不好呀?俩人又是一阵调笑。说话的档儿,那霸道已经遮没在了山后。监听手机里传来绑架者和王胜利的对话,金杯停了下来。王金钟不由踩紧了油门。
走的路似路非路,车轱辘不断地碾上煤块,发出“咔咔”声,不时有一小块煤斜飞出去,在路边的石块上打个水漂,“叮叮当当”很是悦耳。
“走到哪儿了?看见前面那个废窑口了没有?好,你下车,把钱扔进去,使劲扔。”
奥拓躲在山侧,不敢动了。
王胜利照办,回到车里。
“你开车原路返回,十分钟后我告诉你去哪儿找你侄子。”
金杯车开始调头。
“金钟,怎么办?”黄立峰问。
“高杨不跟他们在一块!”王金钟双手死死地攥着方向盘。“我爸一知道高杨在哪儿了咱就过去拿钱。”
“十分钟哪,他们早把钱拿走了!”赵宇说。
王金钟的手机就在仪表台上插着,GPS上那个小绿点缓缓地移动。很快,他们就听见了汽车过去的声音。
“赵宇跟我来,黄蜂和我哥在车上守着。”王金钟跳下车朝小山包背着金杯车的一侧跑去。赵宇跟上,俩人一转眼就隐没在了山后。
黄立峰递过来一支烟,王清明下意识地接了。他的心“嘭嘭”跳。车上的时间显示,刚刚过去了四分钟。这时,从王金钟的手机里又传来金杯车里的声音:
“操你妈,有警察!收尸去吧!”
绑架者的话是从王胜利的手机传到跟踪器,又从跟踪器传到王金钟的手机里的,所以听上去声音并不大,但王清明依然受了一惊。车里车外一阵寂静。忽然,不知从哪个方向传来一声巨响,小山包上的碎石“哗啦啦”滚落下来。
“放炮了!”黄立峰说。
“谁放的?”王清明紧张道。
难道高杨就这么死了?
“日你妈!”王胜利咆哮起来。“快拐过去!拐过去!那边!快!快!”
“去看看!”黄立峰下了车,朝小山包上面跑去。王清明紧紧跟上。
斜阳悬在更远处的西山之上,其红如血。一阵烟尘从一座小山后面腾起。路上见过的那辆霸道一闪而过,向烟尘驶去。高松开的那辆金杯也进入了视界,在山岭之间弯弯绕绕。
“埋废井里了!”王清明说,“咱们也去救人吧!”
“别!”黄立峰还在看,“一会儿他们回来该找不着咱们了。”
四下里并没有王金钟和赵宇的身影。
“坏事了!”黄立峰说,“可能是他俩暴露了!咱走!”
黄立峰拽着王清明朝下面跑去。坐进车里,黄立峰马上给赵宇打电话,却接不通。
“怎么办?他俩再不回来咱四人就惹下祸了!”
“那要真是那些人看见了警察呢?”王清明说。
“那谁说得清啊!”
监听手机里听不见任何声音了。王胜利,和高松,会合了霸道里的警察——对,警察,他们是警察——一起去救埋在废井里的高杨了。
黄立峰一遍遍地重拨,赵宇的手机始终不通。“那就坐以待毙吧!”他焦躁地说。
王清明倒没担心警察会对他们怎么样,他只是不敢相信那个曾跟自己在一起干过几个月活儿的高杨就这样给没了,这个跟自己有着相似的命运,嘴边老挂着“傻逼”二字的从没有笑过的小子就这样给没了。而且,他的死,跟自己竟然还会扯上关系。虽然他并不喜欢他,但是他依然很难相信他不会再见到他了。
正当黄立峰焦虑无措的时候,赵宇打过了电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