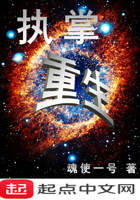岂料她打了个哈欠,瘪着个比扁担还瘪的嘴说——
“我要评价三点,第一,这个女孩儿不一定是冻死的,她有可能是饿死的,因为在火柴的幻象里看到的全是吃的,由此可以判定,她是个吃货,而能看到这么些与吃有关的幻象,不是饿的紧,那就是有妄想症,总之,这人脑子不大正常。第二,她绝对有抑郁症,只有这种心态不平衡的人,才会跟随死人的召唤,白白送命的,所以不值得同情。第三,她是一个脑子拐不过弯儿的人,东西卖不出去,可以学我们村寨里的大叔大婶儿一样,把东西换出去,所以像这种笨的要死的人,会死简直是一定的。”
我吃惊地望着这个土到人神共愤的人,试探性着问了句:“你不觉得,这个女孩儿很可怜吗?”
她转了转大大的眼睛,不明了地说:“一个浑身有病的人,有哪里需要可怜吗?又不是你可怜一下病就能好的,我们要相信医学。”
我倒!我简直不敢相信格林兄弟笔下一个这么悲剧性的人物竟然被她说的这么不堪,她不是一般的土,也不是一般地土到掉渣,这果真是一点儿罗曼蒂克的情怀也没有的,简直没得说。
最让我想不通地是,正当我思考着该用怎样的长篇大论来教育开导她,阿哥就进来了。
而阿哥进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寸草,你又找她麻烦了是不是?”
我无奈地摆摆手,委屈地说:“哪儿有,我在给她讲故事。”
阿哥走过去亲昵地摸了摸蜜豆的头,问她说:“故事好听吗?”
蜜豆看看我,很不高兴地摇摇头。
然后阿哥就笑了:“那寸金哥哥给你讲好不好?”
我纳闷儿地差了句嘴:“阿哥你要跟她讲什么呢?”
阿哥跟蜜豆对视一笑,异口同声地说:“阿拉丁神灯的故事。”
最后我郁闷了,最后我看着他们对视着彼此笑了,最后的最后蜜豆就跟个神棍似的喋喋不休地说白话,更让我想不通的是,最后的最后又最后,蜜豆这土妞连鞋都不要了,光着脚丫子跟在阿哥的后面屁颠屁颠地跑了。
我忽然间有些了解她许的那些愿望了,阿哥在她的心里是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西施,而我在她的心里就是一个东施效颦的东施,连根狗尾巴草都不如。不过到了蜜豆七岁的那年,这一切都发生了改观(当然,我又可以忽略不计)。
那一年,蜜豆没有阿爹了,村里头说她阿爹是因为种罂粟让人给毙了。就因为这个原因,她来我们家的次数少了,变得跟个闷葫芦似的郁郁寡欢。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初秋后,我阿爸阿妈遭了瘟疫病逝的日子。我和阿哥成了孤儿,而不妙的是,阿哥让蜜豆的大姨给领了去,那个大姨,就是蜜豆认定的出卖了她父亲的仇人。所以从那之后,蜜豆就再也不理我阿哥了。阿哥去她家找过她几次,可是基本上都是连人都没见着,就被阁楼上的脏水给冷不防地泼了出来。
我第一次撞见阿哥顶着一身湿哒哒的脏水回家的时候,我难过极了,我明知故问地质询他:“谁干的?”他不说话,只是垂头丧气地朝十里渠(蜜豆家的位置)张望,那憔悴的样子,简直比倾家荡产还要惨。
我真的觉得抱歉,我一直没敢告诉蜜豆,她姨当年想领养的人,其实是我的,然而,阿哥替了我。
“寸草,去到张大爷家一定要听话,太调皮会不招人喜欢的。”过继的头一天,阿哥曾这么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他第一次这么郑重地嘱咐我,这沧桑的语气,给人的感觉好像老了几十岁。
“为什么要换?”我问。
而他,却答非所问:“你喜欢窦泌么?”
我犹豫着不敢说话,要知道这件事是打死我我都不敢承认的,因为阿哥永远都比我优秀,面对那么优秀的他,我是没有竞争的资本的,况且,我没打算争。
“窦泌的性格我了解,谁要是进了窦家,那她就恨谁一辈子。”阿哥一面收拾包袱,一面托付我说:“替我照顾她,你别看她大咧咧的,其实心里头是很脆弱的,她不喜欢吵吵,你跟她在一起的时候,要学会安静些。”
我决定,去找蜜豆聊一聊,为了阿哥,也为了我自己。值得欣慰的是,她对我依旧那么不冷不热,没有因为我是窦秋波养子的亲弟弟,而对我红刀子进白刀子出。
“来看笑话儿?”这是她开门的时候,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里带刺儿的话,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也是唯一一句带火药味儿的话儿。
实际的情况是,她还是让开了一条缝,让我进了门,甚至有搬凳子给我坐,更甚至,还给我沏了茶。
“还好么?”我把热茶放到了桌上,小声地问她。
“你死了爹你能好么?”她眨着大眼睛问我。
我笑着,跟她开了个冷得真切的玩笑:“我爹正死不瞑目着呢,你懂医术,跟我去坟地里救救?”
“切!”她朝我晾凉的茶杯里加了些热茶,冷脸说:“你还是那么贫,一点儿没变。”
“我阿哥病了,”我调侃说:“相思病,你不去看看?”
“给他煮点儿姜汤吧。”她明白我的用意,随即说道:“深秋的水凉。”
我用力地一拍桌子生气地说:“知道你还泼他!”
“如果你是来吵架的,那就恕我不待见了。”她起身把门拉开,凉凉的冷风把屋里的温度都给吹低了。
“不,我想好好聊聊。”我走过去,用手杵着门:“还记得你对着油灯许的那三个愿吗?”
她沉默着,木然地望向窗外。
“你说,希望寸金越长越漂亮,但愿寸草越长越丑,而你的第三个愿望,”我笑着扭头望向她:“是让我们越长越不像,最好再把我变成一根狗尾巴草,对不对?”
“这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她蜷着单薄的身子面向风口,手边的衣袋像失了重心的细叶,不安分地飞。
我替她把风钩稍稍向里收了些,看着那条拇指粗的细缝忐忑地问她:“那现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