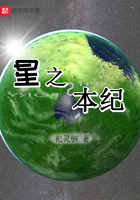如秦云衡所料,石氏果然豪爽大方,听十六娘说罢,当即便嘱了小厮备车马,由健壮奴子驾了一同往她娘家去。
“奴看来,娘子这事儿有些蹊跷呢。”上了马车,石氏盘算了一阵子,突道:“大嫂嫂的娘家不敢报官,是怕那些匪类知晓,还是怕闹到裴公面前不好看?”
“我看着,这两般都是有的。”十六娘道:“我那二叔父,对我阿爷想来是不甚亲近的。至于二婶娘,多半也有些怕我家中。十三姊来寻我求援时,还一再说不要同我爷娘说呢。”
石氏点点头,道:“这般吧,奴家中有金银,连夜叫奴子给铸成金砖,留下些印记。到时候带人来,前脚拿走这金子,奴家中立时便报官道是被窃,娘子看如何?官家总不能放着二百两黄金的大案不管的。”
“那么,此般便多劳你……。”
“无妨,娘子。”石氏笑道:“又不是不还这二百两金子,有什么大不了的?”
说话间马车便停下了,石氏自己跳下车,扶了十六娘下去,道:“如今我家中,爷娘已然不管事了,当家的是我五弟,便是那日架隼子的少年郎君。”
“哦,是他?”十六娘又回忆了一番那日的少年,道:“当真是好生俊俏的少年,怎么,他做商贾,也很是有天分么?”
“不是常说我们波斯人天生下来便是行商的?”石氏道:“这五弟的阿娘是中原人,不过也还好,他的心窍仿佛比别人还灵些。我家族的生意,如今是越来越好了。”
十六娘恍然明白,为何当日见到的石五郎虽然生着胡人少年的高鼻深目,却有一双乌黑清透的眼眸。
“他可好说话?若是不便,我也不忍心叫你为难……。”
“总归是我五弟,能不给我这做阿姊的颜面么?”石氏倒是信心充沛模样:“娘子放心,这二百两黄金,明日便可来拿!”
这边说着话,自有石家的婢子开了门。石家宅子,依律不能高起,亦不能阔大。然而进了门,十六娘才觉出里头别有天地来。
她进惯了达官贵人那轩阔宅子,如今这石氏的院落虽小巧,却布置得别致,显然主人是用了心思的。
“这儿是前年重新掇弄的,”石氏见十六娘盯着假山上自流泉水看,笑道:“便是五弟做的主,非要这假山不可。爷娘都说这东西摆着占地方,谁知他还从假山下头开了条路呢,倒是好玩得很!”
她话音未落,自后宅中便走出一个少年来。不是石五郎又是哪个?
“阿姊!这位,是秦将军的娘子吧?”少年含笑道,又朝十六娘行了礼:“在下石廷荣,迎得晚了,娘子莫怪。”
他此日只穿着平民的白衣,然而一眼看上去,便知那衣料极精良。十六娘暗暗赞叹了一声石家的富裕,但并不还礼,只是抬扇遮面,颔首微笑以示知晓。
“阿姊今日突然归宁,是为了什么?”石五郎引他们入了房中,便问道。
“给我二百两黄金。”石氏开口便道:“今日叫奴子们重熔铸了,都打上咱们家的印迹,明日我要。”
“好。”石五郎答应得爽快,叫始终心中不安的十六娘舒了口气。
他旋即又与石氏以波斯语问答了几句,便起身叫奴子们去取金子了。不过是一盏茶时分,那二百两黄金便码在了十六娘面前。
饶是十六娘自小娇养,富里生,贵里长,然而也未曾见过这么多金子摆在面前。
她叫金子的光泽耀得有些眼晕,微微别过头去,心道,怪不得世人皆爱这东西。二百两金子一摆,这气势真叫人心里头一颤的。
“娘子若验看了成色,我现下便叫奴子们去重铸。”石五郎道:“最迟不过明日早晨,娘子便可派人来取。”
这是第四日,十六娘算来时间够用,忙谢了这位胡商。
“娘子何必言谢?”石五郎微眯了同石氏一模一样妩媚的双目,笑道:“自娘子向惠妃引荐了我家的金工,叫他进了尚方,我石家金珠玉宝便卖得比寻常多出三四倍来。这样的好处,莫说只为娘子借二百两黄金,便是这二百两黄金都不必还,我也不会说半个不字的。”
“当真?”十六娘问了这两个字,方笑道:“罢了罢了,我秦家亦不是欠了人情不还的。”
“娘子好爽快。”少年击掌笑道:“我就喜欢娘子这样脾性的,这样才好做买卖!”
“浑说什么!”石氏忙斥他:“娘子那是有意相帮咱们,怎生算得上买卖?”
“娘子是聪明人。”石五郎却道:“世上万事,皆是买卖!娘子试想,便连父母疼宠子女,亦是为了延绵香火,这世上那一桩事算不得买卖的?只是有些买卖是好做的,有些却是难为的。两边儿都欢喜的买卖,便是大好事,一边儿心里头别着的,便叫人不痛快。”
“这话说得有意思。”十六娘亦笑了:“却也是如此,石娘子亦莫斥五郎了,他说的话,也在理儿!便连你我亲好,不也是为了在一起时两人都欢悦么?”
“这小子最会乱说!娘子可莫信!”石氏这么讲着,看着自家弟弟的目光却满是骄傲。
出了石家宅子,她才同十六娘说,这位五弟平日素喜念书,家中爷娘原道他收不住手上的买卖,甚是担心。可谁曾想五弟聪颖,又见识广博,买卖竟比阿爷当家时还做得风生水起。
石氏说话之间,眉飞色舞,竟是十足疼溺兄弟的阿姊模样。
十六娘亦笑起来,道:“他还未曾婚配?也不知谁家小娘子有幸嫁与这般郎君!家里既宽裕,又是个知书达理的,可叹我不识得旁的昭武人,否则做个媒子,倒也不失一桩美事。”
“五弟尚未去讨人家呢。”石氏道:“他自己阿娘便是中原女子,便讨位中原小娘子也无甚大不了,只是到底还是昭武九姓出身的最好!”
“你们倒比禁婚家还讲究。”
“可不是‘我们’,”石氏笑着纠正:“是‘他们’!奴虽是昭武人,但家中来得太早了,原本便有些中原血脉,哪里能和那群非金发娘子不要的后来人比?否则阿爷也没有讨一位中原女子做正妻的道理了。”
说罢这话,石氏神色突然微变,一击掌道:“娘子,那信上可写了几时去送金子?”
十六娘一愣,道:“……这似乎真是没有的!这……似是有诈啊?”
“奴也这么想。只是娘子先前为何未曾想起过?”
“我只念着那二百两金子了。”十六娘苦笑:“到底是条人命。再说,那信上又说了五日为限,我只当有这时间便是!”
“娘子好生糊涂!若是真绑匪,哪儿有不说清时间的道理?”石氏道:“便是怕咱们抓他,这东西也总该有!难不成,那绑匪的目的其实并不是金钱?”
“这我也想过啊。”十六娘已然开始慌了:“可不为钱财还能为什么?”
“也许,是为了叫咱们中的谁犯些错?”石氏道:“那也不对啊,奴从不曾记得家中有甚仇人,裴氏和秦氏,也不是一般人敢惹的!”
十六娘忖思一阵子,道:“那如今要怎么办?”
“便还是送金子过去吧……只是,咱们大可以留几个人在那边监看着,彼时也好得到些消息。若果然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毛贼,当场抓了也好。”
石氏说着,脸上神情却甚是忧虑。显然,她也并不信,做出这样事情的,会只是寻常的盗匪。
转眼便是第五日,秦云衡特地嘱了十六娘不要跟出来,便嘱咐人叫二十三个健壮家丁过来。他尚须得先去秦云朝那里,因此面上颇有些不乐。
然而便是此时,素来跟着他的小厮直跑了过来,脸累得通红,汗顺着脖子往下淌:“郎君!那地方去不得!”
“……怎么?”秦云衡怔了怔。
“刚刚威德卫宋将军遣了小校来,送来个口信,道兵部今日正要查私调兵卒的事儿。郎君虽只带着家丁,到底是将军,手上也有些兵权,让兵部的主官们抓了不好说清楚,叫郎君莫惹闲呢。”
秦云衡原本没将这案子同宋务年讲的打算,然而前一日宋务年恰好来秦府拜会,吃着酒便提到了此事。
如今,他却遣了人来通风报信了!
秦云衡心下岂能不纳闷的,这神京中,多有军将让治下兵丁替自己做些私事的,兵部并非不知。甚至连兵部的尚书侍郎们,亦大有私遣士卒如家奴的事儿,素来便是人人皆知而不举的。然而怎生偏是今日,便查了起来?难不成是针对了他的?
所幸,他并未要宋务年调士卒助他,否则这事儿,便是说也说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