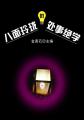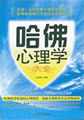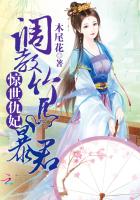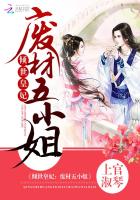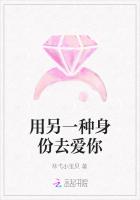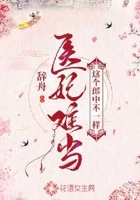文明用什么方法来抑制与自己对抗的攻击性,使其无害,并且可能摆脱它呢?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其中的几种方法,但是尚未发现似乎是最重要的方法。对此我们可以在个人的发展历史中加以研究。如果使个人的攻击愿望变得无害,这将会给他带来什么呢?将会带来某种十分重要的东西,我们也许从未猜测过它,然而它却是很明显的。他的攻击性将会转向内部,实际上也就是回到其发源地——即指向他的自我。在那里它被一部分自我所接管,这部分自我作为超我使自己与自我的其他部分相对立,并且总是以“良心”的形式,用自我本来喜欢在其他的、外部的个体上予以满足的同样严厉的攻击性来反对自我。严厉的超我和受制于它的自我之间的紧张关系被我们叫做内疚感,它表明了一种对惩罚的需要。因此,文明通过减弱、消除个人的危险的攻击愿望,并在个人内心建立一个力量,像一座被占领的城市中的驻军一样监视这种愿望,从而控制了它。
至于说内疚感的起源,分析家和其他心理学家有着不同的观点;但即使是分析家也发现要解释这一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如果问一个人怎么会有了内疚感时,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不容怀疑的答案:当一个人做了某种他知道是“坏的”事情时,他就会感到内疚(虔诚的人们会说是“邪恶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一答案并未讲出什么东西。也许通过稍稍考虑,我们会补充说,即使一个人没有真正去做坏事,而只是意识到自己想要干坏事,他也可能会感到内疚的。于是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把做坏事的意图和做坏事的行为等同起来呢?然而,两种情况都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就是他已经认识到坏事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是不应当做的。这一判断是怎样得到的呢?我们可以否定存在着一个原初的即天生的辨别是非的能力。坏事对于自我来说常常并不是什么有害的或危险的东西,而是相反,可能是自我所欲望和欣赏的东西。因此,这里有一个外部的影响在起作用,恰恰是这一影响决定了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由于一个人自身的情感并不会把他引向这条途径,所以他必须有一个服从这一外部影响的动机。在个人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和对别人的依靠中,可以轻易地发现这一动机,我们可以恰当地把这一动机称为对丧失爱的惧怕。如果他失去了他所依靠的人的爱,也就失去了免受种种危险的保护。首先,他就会面临这个较有力的人用惩罚的形式来显示其优势的危险。所以在最初,坏的事物就是使个人受到失去爱的威胁的事物。因为害怕那种丧失,也就必须避免那种丧失。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干了坏事和准备干坏事之间存有多大差别的原因。无论哪一种情况,只要被上述权威所发现,丧失爱的危险就会降临,并且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权威的做法都是一样的。
这种精神状态被叫做“内心惭愧”,但实际上它不应得到这一名称,因为在这一时期,内疚感显然只是一种对失去爱的恐惧,一种“社会性的”焦虑。在小孩子中间,内疚感绝不会是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在许多成年人中,它也只是被改变到这样一种程度,即父亲的或者双亲的位置被一个更大的人类集体所取代。因此,只要这些人确信权威不会知晓他们所干的坏事,或者不能责备他们,他们就习惯于允许自己去干种种可能给予他们享乐的坏事;他们所害怕的只是被发现。如今的社会大多必须认真对付这种精神状况。
只有在外部权威通过超我的建立而内在化后,情形才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良心这一现象于是达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实际上,直到现在我们才应当谈论良心或者内疚感。也正是到了这时,对于被发觉的恐惧不复存在了,而且做坏事和想做坏事间的区别也全然消失了,因为一切东西都瞒不过超我,即使是思想也是如此。从现实的观点来看,上述情况的严重性确实已经消失了,因为新的权威超我并没有我们所知道的虐待自我的动机,而是与自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遗传的影响却使过去的和被超越的东西继续生存下来,以致人们感到事情从根本上讲就同它的开端一样。超我使邪恶的自我遭受同样的焦虑情感的折磨,并且寻找着通过外部世界来惩罚自我的机会。
在良心发展的这第二个阶段,它呈现出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在第一阶段是没有的,并且不再那么容易解释了。因为一个人越是正直,他对自己的行为就越是严厉和不信任,所以最终恰恰是这些最圣洁的人责备自己罪恶深重。这意味着美德丧失了一部分应得的奖赏;驯服和节制的自我并没有获得它的忠实朋友的信任,它获取这种信任的努力看来是徒劳的。我相信很快就会有人提出异议,说这些困难是人为的,并且有人会说更为严格和保持警惕的良心恰恰是一个守道德的人的标志。此外,当有德性的人称他们自己为罪人时,他们并没有错,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本能满足的诱惑——因为众所周知,诱惑只是在频频受挫后才会增强,而对它们的偶尔满足却会使它们至少是暂时地被削弱。道德学领域充满了问题,它呈现给我们另一个事实:即恶运——外部挫折——大大增强了超我中良心的力量。当一个人一切都顺利时,他的良心便是宽容的,并且让自我做各种事情。但是当恶运降临到他头上时,他就检查他的灵魂,承认他的过错,提高他的良心的要求,强制自己禁欲并且用苦行来惩罚自己。整个人类已经这样做了,而且还在这样做。然而,这一点很容易用原初的、早期阶段的良心来解释。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良心进入超我阶段后,这一早期的良心并没有被放弃,而是始终和超我在一起,并作为它的后盾。命运被认为是父母力量的替代者。如果一个人不走运,那就意味着他不再为这一最高力量所爱,并且由于受到这种失去爱的威胁,他就会再一次服从于他的超我,即父母的代表——在他走运时他总是忽视这一代表。在严格的宗教意义上,命运被看做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在这里,上述情况更显而易见。以色列人相信他们自己是上帝的宠儿,而且当伟大的天父将一场接一场的不幸降到他们头上时,他们从来没有动摇过对于天父与他们关系的信念,或者怀疑上帝的威力和正义。他们用先知作为天父的代表,向先知宣布他们所犯的罪过。由于他们的内疚感,他们创造了具有教士的宗教,它包含极其严格的训诫。原始人的所作所为则极为不同。如果他遇到了不幸,他不是责备自己,而是责备他的物神显然没有尽到责任,并且他不会自罚而是鞭打他的物神。
因而,我们懂了内疚感的两个来源:一个是起源于对于某个权威的恐惧,另一个是后来起源对于超我的恐惧。第一个坚持要克制自己的本能的满足;第二个也是这样做,迫切要求进行惩罚,因为被禁止的欲望的继续存在是瞒不过超我的。我们还知道了超我的严厉性——良心的要求——是怎样被理解的。它只不过是外部权威的严厉性的延续,它继承了后者而且部分地取代了后者。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对本能的克制是在怎样的关系中坚持内疚感的。最初,对本能的克制是对外部权威的恐惧的结果:一个人为了不丧失外部权威的爱便放弃了他的满足。如果一个人实现了这样的克制,他就可以说是服从于外部权威了,并且也不再有内疚感了。但是对于超我的恐惧,情形就不同了。在这里,对本能的克制是不够的,因为本能的欲念依然存在并且不能瞒过超我。因此,尽管做了克制,内疚感还是会发生的。这就在超我的建立过程中,或者说是在良心的构成中,造成了一个很不稳定的条件。对本能的克制再也没有全然自由的结果了;虔诚的节欲也不再保证会得到爱的奖赏了。外部不幸的威胁——失去爱和外部权威的惩罚——已经换成了永久的内心的不幸和加剧了的内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