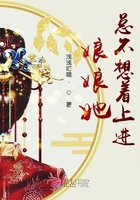大渊的东部和宁朝接壤。两国之间的关系有些微妙,基本上可以说从未发生过正式的战争,只在二十年前,那时还是宁朝老国君和锦阳帝在位时期,在边界线上有过一次挺危险的两军对峙。对峙时间长达两月,硝烟味浓浓地布满漫长边界线上。战争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临界点,最后还是宁朝方面让了一步,先行撤军。这才没有打起来。
大渊和宁朝,战争是没发生过,但经常会有些小摩擦,皆是民间纠纷。也就是两国边民在做生意时谁吃了亏谁占了便宜;或者一边的牛羊走失到了另一边,牧民追索过去对方不还等等。
大渊之东接宁朝之西,两边都是两国主要的牧区,因此这种走失牲畜的纠纷几乎每个月都有好几起,二十年前那次军队对峙事件,其实最初的起因也是这个。两国的边民因为几头牛羊闹出了人命,之后边防军介入为已方的百姓打抱不平,然后矛盾不断激化升级,最终演变成了两国边防军共计十三万人马,在边界上对峙两月的危险事件。
从那次之后,两国各自总结教训。从此严令边军不得介入民事纠纷。边民如果有了纠纷,切记绝不可动手。不管原本对错,谁动手谁理亏。自己实难解决的事可以上报官衙,接到报案的一国官衙,就会立刻向另一国通报,然后此事就由两国官方调停化解。
自从这项法.规出台后,十几年来,好歹再也没闹出过人命来。两国的关系也一直微妙着,既无战事,亦不融洽。
这样的关系,直到两国都换了新君,还是如此。
这种如走钢丝般的,危险而又微妙的平衡,终于还是被打破了。
隆晖四年的五月十七,大渊这边又有一户人家的两只羊跑过了界,这家的主人连忙过界找羊去了,结果一天一夜未归。这人的妻子慌了手脚,只有跑到官衙去敲了惊堂鼓。县丞一听此事,也紧张起来。立刻派人去通知了宁朝方面。
当天今晚,那个人的尸体被送回了大渊这边。尸体伤痕累累,惨不忍睹,一看便知是被活活打死的。县丞一见当即大怒,质问宁朝方面的来人为何将此人打死?两国联合制定的法规难道不知吗?
来人不但没表现出惶恐欠疚,反而振振有词,说这个人在宁朝那边行止不端,调戏一个女子,人家的兄弟和他讲理,他不但不道歉,反而先动了手,那姑娘的兄弟年纪十七,正是血气方刚之时,又气此人无耻无礼,下手难免重些,此人又不禁打,就死了。
大渊的县丞顿时卡壳,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连他也要背上个教化不严的罪名,还那有脸面为死者讨还公道。
死者的妻子听到宁朝那几人的话,立刻又哭又骂,说她丈夫是老实人,是绝不会做这种事的,他们这些人是胡说八道,老爷你要给民妇做主啊!
后来宁朝的几人回去,把那个被辱女子和她兄弟带来,大渊死者之妻也去找了和她丈夫相熟的邻里朋友作证。两拨人在大渊县丞的大堂上足足吵了一天。那死者的邻里朋友都说他的确是个老实人,木讷少言,若说他会调戏女子,真是怎么都不能信。
可是宁朝那位据说是受了羞辱的姑娘哭得是寻死觅活,她兄弟在一旁满脸悲愤,牙咬得咯咯响。这些也不像作伪,再说了,人家姑娘牺牲名节,陷害一个贫苦牧民,图什么啊!
县丞在内心里是相信宁朝那双姐弟的,他打发他们回去,而后和死者的妻子谈判,许了她一口棺材,三只羊加五两银子,让她不要再闹了,回家料理丈夫后事去吧。
这个死者真是太冤了。他哪有调戏那女子?再说,那女子一身好功夫,有岂是他调戏得了的?他在路上遇到他们,他们听说他是大渊人,冲过来就打,他直到被打死了还是个糊涂鬼。
其实,打死这个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挑衅找茬的第一步。
第一步只是试探,第二步便是一记耳光,重重打了大渊凌尧帝的脸。
七月初三,有二十多个到宁朝那边做小生意的大渊人被砍了。砍脑袋,自然是被宁朝的官府捉去砍的。这事已经不是自己能解决能遮掩的了。县丞抹去满脑门的冷汗,果断将这消息上报。
这消息层层上报,最后到了金殿上,放在凌尧帝的面前。
大渊宁朝两国通商到已通了一百多年,就算宁朝想要单方面结束通商,也该事先知会通告一声。可是没有,无论是地方还是朝中,都没有收到宁朝的只言片语声明从此不许大渊人过界做生意,就这样蛮横地一次杀了二十人。
天景怒了,她写了封措词激烈的国书质问百里容珏,为何做出如此令人发指之事,究竟意欲何为?
几天后,百里容珏的回复到了,他的话说得尖酸刻薄,称并非是不愿意两边民间通商,数天前捕杀的那批大渊人并非什么良善之辈,他们打着做生意的旗号过界,在宁朝行偷盗窃取等不堪之事,宁朝乃礼仪之帮,法度森严,偷盗十两银子就是斩刑。而这些大渊人在宁朝偷盗皆有百金以上,因此必须按律法办。不知凌尧帝是以何等道德标准教化治下万民?难道大渊子民个个都是这种鼠窃狗偷的不堪之徒?也亏得凌尧帝竟然还发国书向朕质问!若是换了朕,必然羞都羞死了。哪里还好意思问。
天景攥着那封国书气得发抖,鬼才相信这番胡言乱语。就算那二十人当真是毛贼强盗,宁朝西边五百里范围都是荒僻小城,那二十人竟能盗取百金,在百里容珏的概念里,是拿铜钱当金吗?这分明就是找茬。但这样无缘无故的找茬,百里容珏究竟想干什么?是想打仗吗?
天景把国书摔在了一旁,提笔开始写一封谕旨:封锁大渊至宁朝的边境,所有边民后撤五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