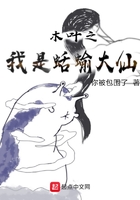心灵之痛让人颓靡
肉体之痛让人抽离
不知道谁发明了坚强这个词,这简直就是人类为了自己玩自己而挖的一个大坑。当一个人要担起坚强二字,必是遭了大难,要么是心灵的重创,要么是肉体的剧痛。伤的是你,被称颂的也是你,循环在伤痛与忍耐之间的,还是你。多数时候,人们会觉得心灵之痛要甚于肉体之痛,所谓“哀莫大于心死”,死都不怕,疼算什么。但那只是人们为了遮蔽生命的脆弱,而故意放大了精神的痛苦,心灵之痛让人颓靡,肉体之痛让人抽离。大多数人都曾经历过心灵之痛,这是自我与世界对话的谈资。而肉体之痛却会让人瞬间放下所有心灵之痛,进而在剧痛消退之后扭转内心的格局。
每一次剧痛, 都成为我生命的刻度, 就像那些音乐和女人……
八岁那年,我上三年级。在那个没有iPad 的年代,一个小学生的课后娱乐全凭自己的想象力。那时候学校旁边的大院里在建一个职工食堂,工地是男孩子的“迪斯尼”。每天放学后,我会拉几个小朋友去工地上玩。开始我们就是玩玩沙子,某天我发现工地的地基下面还有像迷宫一样的排水地道。于是从凡尔纳与地道战交织而来的探险精神突然迸发,我们要去那地道里寻找另一番天地。
为了地道的探险,我做了很多准备,先是从垃圾堆里捡来几个烂笤帚,又去工地上找了点儿废油毡,用火柴点着油毡滴在笤帚上,做成一个真正的火把,然后我们就点着这火把下地道了。猫着身子在地道里缓步前行,我们当然并没有发现宝藏,却被一个横在面前的深坑挡住了去路。那个坑有一米多宽,如果在地面上就跳过去了,可是地道太矮,没法跳啊。这时候,八岁的我沉着淡定,我对小伙伴说:“楼上脚手架上有一些铁板是工人横穿脚手架用的,我们去抱一块来就能爬过深坑了。”于是,我们钻出了地道,顺着脚手架往上爬,一直爬到二层。那食堂其实一共就两层,但是单位食堂大家都见过,一层就有宿舍楼三层那么高,那时候我还不恐高,看着眼前那块横在两根脚手架钢管之间的铁板,我开始幻想地道更深处的神秘景象……我一只手抓着脚手架,一只手去抬那块铁板,它真的好重啊,我想把它从脚手架上掀下去,这样就不用费力搬动它了。我用手指抠在铁板的孔上,使足了力气一拽,然后那块铁板就从十米高的脚手架上掉下来,跟它一起掉下来的,还有八岁的我。
我重重地摔在下面的一堆沙子上,我想我是昏了过去,那片安静的工地没有工人,小伙伴们一定以为我摔死了,全都吓跑了。当然这一切我并不知道,我就一直躺在那里,像睡着了一样。不知道躺了多久,我慢慢睁开了眼睛,看到天还亮着,惊恐地以为自己睡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动了动身子,全身每个地方都疼,我站不起来,只好继续躺在那里。这时我看到那本该冉冉升起的太阳居然在慢慢落下,才知道我只是躺了一小会儿,现在回家,妈妈只当是我刚放学,不会发现我又出去做了大事。我挣扎着爬起来,脑子里根本没有刚刚错过死神的余悸,唯一庆幸的就是我还能走路,现在赶紧回家写作业,不要被妈妈发现暴打一顿。
捡起书包斜挎在肩膀的那一刻,疼得我又一屁股坐在地上,我没哭,一声都没哭,不是我坚强,是我的脑袋还处在巨大的混沌中没有完全出来,一切都是蒙的。我又试着爬起来,手里拎着书包向家里走去。路上遇到一位妈妈的同事,阿姨看着我关切地问你生病了吗?怎么脸色煞白煞白的?我说没事,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走回了家,全身的疼痛很快就消散了,只剩下右肩膀剧烈地疼痛,写作业疼,睡觉也疼。我不敢吱声,就这么忍着。
肩膀的剧痛在一个月后慢慢好了,只是每次上体育课跑步都特别煎熬,每跑一步都很疼。让人欣慰的是不跑步的时候它也不疼,所以我还能忍,只是跑步的时候耸着右肩的样子有点儿滑稽。这跑步的疼痛在半年以后也消失了,后来,因为时间太久,我都已经不觉得这疼痛跟我从楼上掉下来有什么关系。
一年以后,我上四年级了。学校查体,例行地给大家照照X线,大夫意外地在我的右侧锁骨上发现了一根深深的裂纹,那是骨折之后自己愈合留下的印记。每次有人问我骨折过吗,我都会说从来没有,因为我觉得只有打了石膏夹板才算是骨折,一个八岁的孩子觉得自己每天扛着骨折的锁骨上学放学,都是天经地义的。
十三岁那年,我上初二,自小学卸任路队长之后,重回“官场”当上了动物课代表。对这份工作,我很认真,觉得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终于来了。一天上课,老师让我把上次考试的卷子发下去,我抱着一摞卷子行走在课桌之间的过道中,像个勤奋的饭馆跑堂一样兴冲冲地把卷子分给每个同学。就在我发卷子发到了前排那哥们儿时,看着他那63 分的成绩一阵得意,我用力地把卷子拍在了他的桌子上,一股钻心的剧痛让我瞬间眼前一黑。我从他的卷子上抬起自己的右手掌,看到刚才上课解剖青蛙用的那根针大头朝里插在我的手心,只隔着一层皮就从我的手背穿出来了。那根大针被他插在课桌上,我重重拍下那张卷子时,针扎进了我的手心——那是诡异而恐怖的一幕,我的手心里有一根直挺着针尖的针,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掉光了刺的仙人掌。
同学都吓傻了,老师也不知所措,赶紧陪我去医务室。一路上我就用左手托着右手,那种异物感让疼痛又加重了十倍。到了医务室,校医也有点儿惊慌。她假模假式地戴上橡胶手套,拿着一个大镊子去夹那根针。我分明看到校医的手也在抖,所以她夹住针之后的每一次尝试都引来我阵阵惨叫。惨叫彻底吓坏了校医,她决定送我上医院去做手术,我开始幻想自己的手心被手术刀一点点切开,那根大针的针孔挂着我的血管被揪出来。我说我不去,那样以后就不能写字了,校医一个劲儿地安慰我说左手也可以写字,其实她不知道我到今天仍然只会用右手打飞机。
校医叫来了校长的司机,让司机赶紧送我上医院,司机漫不经心地走进医务室,看我好像也没啥事,就问我怎么了。我抬起右手掌给他看那根针,司机轻轻地托着我的手,像个古董贩子一样盯着那根针左右端详,不时还惊叹着:“这么大的大头针,怎么能扎到肉里去呢?”他用手指捏着针左晃晃右晃晃,好像检查他们家炉子的烟囱一样。突然,司机噌地一下就把那根针拔出来了,我疼得直接跳了起来,刚想骂人,看到手上就剩下个针眼,当时就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