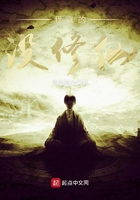城东的默巷,咔地一声裂响,众人仿佛从梦中乍然惊醒。老僧木然凝望手中的长刀,锋利得泛出青光的刀刃上崩出一个小口子,裂纹自雪亮的刀刃延伸,仿佛蜿蜒在冰封的湖面,忽地崩出一声刺耳的、打铁一样的金属撞击声,整个刀身裂为数片。
可惜这把上古的“龙牙”,在地下埋藏了上千年的邪刀,还未来得及向世人展示它的狂暴与威猛,甚至还没有几个人认识它,第一刀便碎了。
老僧口唇微动,不知道和谁说话,莫非是和不知何时立回身畔的白犬?但见他一张黄皮也掩不住脸色的灰败,眼神中净是深深的惊怖,任谁都觉得惊怖这种表情绝不该出现在这胆气冲天,功夫高绝的可怕僧人身上。他喃喃道:“凭空驭实,化气结灵,真有这样的秘术,我佛‘万象皆空’岂不成一句笑话!”白犬默不作声,以眼神回视主人,一双微红极深的瞳孔里好似也承装了与主人一模一样的灰败与痛苦。
羽林天军小队的头头打个哆嗦,这才找回自己的声音,一声断喝“大胆!京畿重地岂容你行凶!”催马上前便要捉拿,身后的伙伴也纷纷回神,将马鞭狠狠敲下去,马蹄一时将小街上激得尘土飞扬,呛得给他们掩在身后的紫袍男孩不住地咳嗽。
那白犬在尘土中扭过头来,向他们看了一眼。
羽林卫胯下的骏马竟一个急刹,纷纷扬起前蹄,就像之前那匹粟河马一样惊声长嘶,频频交错四蹄的位置原地踩踏,甚至摇晃头部,试图脱出缰绳的控制。守卫上阳皇城的羽林天军配的都是最好的纯血战马,就是在山里遇见群狼也从未如此惊恐,给那畜生扫了一眼竟像是看到了地狱。
人马寸步难行时,老僧已垂着两只手转身,白犬默默跟上,两个竹竿般又硬又细的身影片刻便消失在街巷的尽头。
马车也在羽林军的簇拥下走了,不愧是训练有素的军马,从短暂的惊恐中平静下来只用了片刻,离开得极其平静迅速。随着羽林天军的队伍一起来的小男孩吓得连自己的枣红小马也骑不住,也坐在朱漆的小马车上,两个孩子面面相觑,谁都说不出话来。
顺丰镖局这个倒霉的镖师也走了,是给上阳府衙一群皂衣的衙役带走的,倒是客客气气没有披枷带锁,但从抓人的到被抓的那脸上的神气都是一般难看晦气。好好一个春天白日里,遇上一遭诡异道极点的无头公案,逮不着主犯,拉住一个受害人无论如何也交代不过去,但若连这受害人也放跑了,府衙的乌沙怕是颤巍巍就要落地。
兵荒马乱地过去了一刻钟,两边屋舍里都没有一个人探头。白花花的街当中只滚着那个红彤彤,圆滚滚的苹果,忒好的一个大果子,给所有人彻底遗忘了,就跟街边的小叫花一样,他们便是在墙根躺上一排也不会有人过去看一眼,问半句,在上阳城里破茅舍、穷乞丐,但凡与这流光溢彩的城市格格不入的,人人都当是死物。如今这苹果也是死物了。
小叫花微微抽搐一下,是半晌一动也不敢动地窝着把半边身子窝麻了。他一拐一拐走到街心捡起苹果用破衣服用力揩,又放到鼻子底下用力地嗅着。细看他其实是个很好看的孩子,一张沾满灰尘的小脸长得极秀气,眉眼都是长长的,此刻眼中盛满亮晶晶的笑意。如果生在富贵人家这是个多么漂亮有福气的小公子。他小心翼翼地将苹果揣在怀里仿佛那是一个大宝贝,顾不上腿脚的酸麻高一脚低一脚地跑回家去。
可是在低矮的茅草顶板房里他彻底地被忽略了,两个哥哥刚刚收工回来,他们分享了这份意外的“盛筵”。在这个家里十四岁以上的男性都像牛马一样整日干活,养分总是优先供给能养家的劳力。父母偏疼幼子那是稍有富余的家庭吃饱肚子才能有的情怀。就像茅草的屋顶已经在频繁的春雨下沤出霉味,肚子还没有填饱的人并没有精力去管这种影响生活质量的小事。
这个叫樊四儿的小乞丐远远地望着,他还是觉得很快乐为这个家带来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如果有一天,他自己能吃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就好了。
在他剩余的人生中,这对于一个苹果的渴望始终在追赶着他,逼迫着他,直到他将目光投向整个雍阳皇朝最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