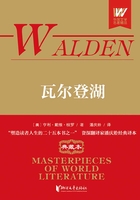二月十九,是昿武将军百里归的忌日。
徐玄策的府里,这一日照旧茹素,一杯薄酒相祭。如今整个大雍,昿武将军的令牌仅次一方而已。徐陆依着父亲的意思,行父母礼,将一把细香进在灵前。
酒是“女儿妆红”,来自百里归南方的家乡。徐玄策也陪着喝了一杯,在灵前默立良久。有时这些活人为死人做的排场,与其说怀念故人,不如说宽慰自己。但有些事却无论如何也抹不去了。徐陆面色沉郁站在父亲身后,跟那天看着皇子们打架一样,失魂落魄,又像百无生趣。过了许久,徐玄策说道:“皇帝说,百里归是为大雍而死,但他不是。他是为你而死,为我的私心而死。他死了,只因为他不像你一样,有个手握重兵的好父亲。”徐陆低下头,低低地应道:“是。”
“到战场上去吧。”徐玄策叹息一声,将一杯“女儿妆红”轻轻放在儿子面前,说:“去证明你不只能依靠你的父亲。如果回不来,就替昿武将军死在战场上。”
徐陆的眼睛忽然亮了,就像垂死的人看见灵药,完全丧失斗志的人重新握住自己心爱的武器。
夜雨。
山鬼的面前也有一杯酒,也是一杯“女儿妆红”。
这种酒曾经是他的妻子最喜欢的,春寒料峭时,她总是亲手为他温这一壶酒,加上两枚青梅,坐在边上不说话,细细为他斟满酒杯,看着他翻看兵书。
有一位词人写过“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斯人已逝而旧景犹在,最是断肠。
许久,他伸手端起酒杯。一年之前他还握不住任何实体的东西,一年以后,能饮一杯无?他端详许久,仰头一饮而尽。只听得汩汩水声,清亮的酒液不知从何处流下,在坐席上汇成一滩亮亮的水渍。
云山居——那白衣纸伞的青年站在门口,轻轻地说:“酒是至烈至阳,你想要再饮一杯酒,恐怕还要很多年。”百里山鬼接道:“我不怕。我有的是时间等。”眼光瞟向屋子一角,古玉镶饰,异兽踏云雕纹的“大荒夔”正静静地躺在刀架上。
云山居叹了口气,转身脚步极轻地走开。沿着滴水的屋檐,穿过满院碧绿高大的翠竹。这院子没有墙,根本就是和满山的竹海融为一体。他的眼睛始终蒙着干净的白色布帛,但丝毫也不影响他在庭院间漫步,最后走到山居最前面的小院。
“朽异”两个斗大的字悬于翠竹间。叫云牧野的少年坐在下面的轻灰石阶上,轻轻地揉着裸露白净的脚丫,旁边那高大憨厚的昆仑奴半蹲半跪在地上,担忧地看着年少的主人,全然不顾自己两只蒲扇般的大脚上尽是污泥和血泡。昆仑奴身旁还扔着小小一只座椅,有扶手有凉棚。这一路上多半时间云牧野其实都是坐在木罗伽蓝背上回来的,现在这副样子既可怜,又着实有些可疑。
云山居收起纸伞靠在墙边,在廊下的竹木矮桌边坐下来,一张俊秀的脸上挂满和煦的笑意:“你回来啦。”
云牧野瞟他一眼,有些气鼓鼓地说:“是呀,可真不容易。”这孩子和云山居本来就有七八分相似,已是不可多得的秀美皮相,微微发起怒来苍白的脸色带上红晕,透出一种难以言喻的艳丽,和兄长的淡雅温和又不一样,是个倔强的小孩子。
云山居好像完全没有感受到他的不高兴,微笑道:“你在瀚州的遭遇我都知道,不要那么夸张。”
云牧野小孩子一样微微地撅起了嘴:“是啊。我都忘了哥哥的瞳术,是九州之内无可匹敌的。”
云山居微笑着摇了摇头:“又耍小孩子脾气。让你吃一吃亏也好,免得你总是嚷嚷要回云州。南陆那边的人,可比北陆的蛮人要复杂多了。再说你不是也稍微教训了那些狂徒?还有什么愤愤不平的。”说罢伸出一只干净修长的手,将矮桌上的一只酒杯向前推了推:“呐,你最喜欢的桂花米酒,酿得很淡,不会醉人的。”
云牧野叫着“哥哥”两个字的时候就已经像只小猫儿一样软了下来,此刻听见有好喝的米酒酿,早就小小地欢呼一声蹭了过去。云山居微笑着为他摘掉头发上沾的竹叶。他连喝了两杯,忽然坐直身子,微带警觉地向四周看看,问道:“哥,有外人?”云山居笑着说:“等你发现,这朽异山居的牌匾都给人拆下来了。放心,是一位客人。”云牧野好奇地追问道:“什么客人啊?朽异山居都好几百年没有客人了吧?”“你才几岁?还好几百年。”云山居无奈地笑着敲敲陶罐:“你到底还喝不喝了?”
再淡的酒,喝多了也醉人的。云牧野喝着喝着就睡着了,一觉醒来迷迷糊糊睁开眼,满天星辰笼在高高的竹林上面。他正枕在哥哥腿上,云山居抬头静静“看”着天空。云牧野睁着惺忪的眼睛迷迷糊糊地问:“我明明是去帮瀚王的,为什么他不领情呢?”
“你看那颗贪狼星。”云山居遥遥地指向天空:“人心就像这贪狼星一样,就算知道大祸将要临头,也没有人愿意放弃欲望,每个君主,都想要手握天下啊。”
空中贪狼星芒闪烁,云牧野不知咕哝了些什么,又安静地睡去了。
陆槐儿趁着月色溜出来,在瀑布边的空地上反复琢磨两天前所学的招数。这一招“明月照大江”他已经琢磨了两天,无论如何也练不好,每到第三剑的末尾变招时,他的剑就控制不住斜着切出去,下一招自然无从谈起。姬老头教完他这一招就不知跑到哪里饮酒去了,按照以往的经验,就算能找到他也就是一句“你要靠悟性!悟性懂不懂?要慢慢领悟。”就把他打发了。他只好靠自己一遍又一遍地琢磨。
月下,他再一次舒展全身的骨节,摆出架势,凝神静思片刻然后出剑!
头两剑都很顺利,也练得很纯熟,转眼就到了第三剑,第三剑是一个上撩然后转剑平削,他在上撩的收尾用力灌注于手臂上,然后平移,剑锋又一次斜斜地划了出去,成一个难看的弧线。陆槐儿重重叹了一口气,几乎要气馁得趴在地上。
旁边树上忽然传来声音:“你不能只靠手臂的力量。”那人说道:“手臂笨拙,不够灵活。你需要先将力量集中在腰,将腰身和手臂完全稳定,然后靠手腕的力量来带动这一剑。”
陆槐儿闻声望去,龙离坐在极高的一根粗树杈上,难得没有望着天空,而是低头看着他。
陆槐儿照着他说的方法试了一试,第二剑结束身体转回来,立即将力量注入腰部和上臂的肌肉,将整个身体稳住,然后以手腕带动剑柄,成功了!虽不太完美,但削出平且直的一条线,接下来只要将速度加上去就可以了。他欣喜若狂地抬头看着龙离,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
龙离有些意外,怔了一怔,拍拍身边的树杈轻声道:“过来吧。”
树杈离地两丈有余,如今这样的距离难不住陆槐儿。他轻身一跃,在空中转身坐上树杈,哪还有半点初来时的青涩笨拙。
距离龙离陡然近了,他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抽了抽鼻子道:“好香。龙离你在喝酒?”
龙离看一看手中一只小小的酒坛:“是‘凉州烧’,我家乡的酒。”他又看看陆槐儿的馋样儿,犹豫了一下,将坛子递过来。陆槐儿接过来就迫不及待地灌了两大口,享受冰冷的烈酒流过咽喉,从胸膛一直滚烫到喉咙口的感觉,刚来岛上时他可没有这般的豪爽。他回味许久,将酒坛递回给龙离,龙离却有些别扭,说:“你喝吧,我喝够了。”
对这少年来说,能跟你一起分享什么那绝对已经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了,要他用别人喝过的杯子喝酒,还是算了吧。
陆槐儿早已习惯了他这个鬼样子,干脆抱着坛子咕咚咕咚又灌了一气。龙离却好像对自己的不近人情有些歉意,所以说他绝对是喝高了,忽然神秘兮兮地冲着陆槐儿说:“你想不想知道这岛上好酒好菜,是靠什么赚钱的?”陆槐儿将头点得鸡啄米似的,他早就好奇死了。
龙离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悄悄的,跟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