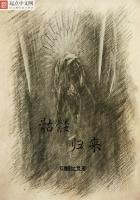几乎是一把钥匙。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比所有同时代的俄罗斯哲学家更深刻地表现了西方的人生哲学及其世界观的分裂。相比之下,中国的《金瓶梅》几乎是一家暴发户社会关系与情欲发泄的琐屑记录,而同是描写性关系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则以象征的技巧集中表现了劳伦斯的“反异化哲学”小说以查太莱象征现代的工具理性与工业文明,以梅乐士象征感性生命、审美直觉和生机勃勃的自然,康妮离弃丈夫查太莱而投入情人梅乐士的怀抱,象征着现代人应该厌弃工具理性与工业文明而走向充满生命活力和审美直觉的自然。另一方面,从柏拉图到柏格森(H.Bergson),西方有文采的哲学家并不少,但这不是西方哲学的特色,与中国哲学相比,西方哲学的特色就在于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抽象分析传统,文字以远离生命与直觉语言的逻辑分析见长。而中国的哲学文本从不缺乏文采。《论语》虽然是孔子教学的实录,却一点也不缺乏诗性。孔子很少抽象的说理,而是以各种比喻和象征而启示学生的思维。《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似乎他的著述有点故意远离艺术,但是由此也使得《老子》五千言文辞简约,显得朦胧、模糊、含蓄,并且还用韵,如果分行排列起来,简直就像诗: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孟子好辩,一改《论语》、《老子》文辞简约的文风,已经显示了带有逻辑色彩的论证,但是《孟子》在论辩中并不客观,显得“气盛”而曲尽其情,而且还经常以生动的比喻和寓言辅以论辩,使得《孟子》文采飞扬。当人们读到从《孟子》中节选出来的“揠苗助长”与“齐人有一妻一妾”等篇章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孟子》进入文学史的合理性。
比《孟子》更喜欢用比喻和寓言阐发道理的是《韩非子》,“守株待兔”、“涸泽之蛇”、“三虱食彘”等寓言就出自《韩非子》。《荀子》之文虽然少用比喻,但却喜欢用对偶、排比等修辞技巧润色文章,而且行文中也不缺乏感性的形象语言。这种文学性很强的诸子散文对于后来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类是身为文学家但偶作哲学著作,或主要是哲学家但偶作文学作品。文学家写作哲学著作,往往也具有文学色彩,而哲学家创作文学作品,也会带有较强的哲思。德国的席勒(J.C.F.Schiller)主要以《强盗》、《阴谋与爱情》等戏剧和诗歌名世,但他的《审美教育书简》等著作却是很有深度的哲学著作;中国的鲁迅是以其小说和杂文名世的,但他的《文化偏至论》则是一篇哲学论文。他们对于哲学的爱好,使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富有深度。当然,席勒处理得并不好,他为了表达哲思经常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时代观念的传声筒;而鲁迅后来在创作中处理得当,使得《野草》等作品既有深刻的哲思,又没有损害艺术的感性。在现代法国,加缪主要是以作家名世的,但他的哲学著作《西绪福斯神话》对现代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过在文化史上,文学家写作哲学著作的并不多,而且也未必见得成功。但丁写出《君主制论》等哲学著作,但是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评价说:但丁“做为一位诗人虽是一个革新家,但做为一个思想家不仅没有影响,而且还陈腐得不可救药。”相比之下,创作文学作品的哲学家不仅人数多,而且成就也较大。尤其是在中国,秦汉以后的哲学家几乎很少有人没有文学创作的,即使强调“理”的理学家,也作有不少诗文。朱熹的名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已经成为中国人可以背诵的名诗,而其《春日》中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也已成为人人称道的名句。
第三类著作家既写文学作品,又写哲学著作,很难分辨其以那种表现形式为主,甚至他们在文学史与哲学史上的地位也难分伯仲。
将他们当作哲学家固然是不错的,将他们当作文学家也完全合理。
在法国文化史上,这类著作家特别多。伏尔泰是著名的讽刺作家,文艺上的古典主义者,但也是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卢梭是浪漫主义哲学与文学的双重鼻祖,他不但著有《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哲学论著,而且也创作了《新爱洛伊斯》、《忏悔录》等文学作品,而《爱弥尔》似乎是用小说的文体创作的教育哲学著作。
从狄德罗到伯格森、萨特,类似的著作家在法国不绝如缕。一方面,文学史不会漏掉他们的名字,研究西方的讽刺文学不能绕过伏尔泰,而从悲剧与喜剧演变为现代的市民剧,狄德罗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尤其是卢梭与萨特,前者是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始祖,后者是现代存在主义文学的主要作家。另一方面,哲学史也不能不提他们,启蒙运动是一场“哲学运动”,而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则是这个运动的主要领袖。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是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齐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名著,讲存在主义哲学而不讲萨特,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由于这些哲学家又同时是重要的作家,所以他们的哲学著作对于其他作家的影响,远远要超过那些专门的职业哲学家。将卢梭看成是对现代西方文学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似乎并不是夸张。中国的著作家也有这种特点。“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对于古人论道今人的哲学写作同样是适应的;而对于某些使命感很强的儒家士大夫来说,“文以载道”是他们进行文学创作时的“道德律令”。因此,对于法国和中国的著作家来说,像德国思辩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那样的枯燥无文采的文本,一般而言是比较少见的。
第四类文本最能体现本小节“在文学与哲学的交汇点上”的精神,即文本的哲学含量与文学含量难分伯仲,文本本身就难以分清是哲学文本还是文学文本。《庄子》是哲学文本,但也是富有想像力的文学文本,可以说,情感性、想像性、虚构性与创造性等文学性的诸要素,在《庄子》中都不缺乏。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与《庄子》类似的文本,这类文本处在哲学与文学之间的交叉地段,既可以当哲学文本读,也可以当文学文本读。中国编著的一些文学史不会不写庄子,却在编写的外国文学史中将尼采忽略,就是一个极大的疏漏。无论中外,没有那个文学史家会忽视歌德的《浮士德》,有的文学史家甚至将其推为最伟大的诗歌巨著之一,但是,如果将《浮士德》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放在一起,人们会感到二者有着很多的共性,原因就在于,《浮士德》是诗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而《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哲学是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我们想在比较中加以辨别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将华兹华斯与中国的田园山水诗、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文本再加进来,这时我们就会发现,《浮士德》与较为纯粹的田园山水诗相比更接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纯粹理性批判》相比更接近《浮士德》。有人说哲学比文学更能代表一种文化,但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恰恰是以“浮士德”做为西方文化的象征符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浮士德》等文本也应该进入哲学史,而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已经将诗人拜伦做为专章讨论了。
文学与哲学的交叉关系,表现在文体上,就出现了哲理诗、哲理小说与哲学剧等由文学与哲学交汇而成的文体。其中,哲理诗是被诗人经常运用也为社会广泛认同的一种文体。就中国诗歌而言,唐代之前,哲理诗还不多见,尽管六朝的山水诗都蕴涵着哲理,但是,哲理诗的大量出现是在宋诗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宋诗是以哲理的丰富而与唐诗相区别的。这就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谓的宋人尚理而唐人尚意兴,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所谓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中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就是对儒家“敏于行”哲学的说明。邵雍的《善赏花吟》则是理学哲学的艺术外化:“人不善赏花,只爱花之貌;人若善赏花,只爱花之妙。花貌在颜色,颜色人可效;花貌在精神,精神人莫造。”欧阳修的《赠无为军李道士二首》,几乎将道家哲学几句道破:“无为道士三尺琴,中有万古无穷音。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觉天地白日愁云阴。”苏轼不仅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哲理名句,而且苏轼的艺术哲学许多都是以诗的形式表现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可以看出,苏轼以诗表达的艺术哲学比他的其他论著更接近空灵妙悟的诗学境界。
以上是对人类已经产生的文学与哲学交汇的文本的归类与分析,文学与哲学是否应该交汇,或者应该怎样交汇,是一个更为艰深的课题。一些追求“纯美”的人,总在贬低这种交汇,以为美就应该是纯粹的,与哲学是无关的。但是,很不幸的是,人类迄今为止的审美评价标准,却更以具有哲学内涵的文学文本为伟大的文本,而将“纯美”的文本看成是二流或三流的作品。其实,“纯美”的文本相当于康德在界定美之为美的时候只对形式感兴趣的“纯粹美”,而与哲学交汇的文学文本则相当于康德推崇的“依存美”。这也是康德哲学的背谬,因为既然美之为美在于它的纯粹形式性,那么对形式的追求就应该是至高无上的,现代的形式主义美学正是从这里生发开去发展了康德美学的。但是,既然美没有一个客观恒定的判断标准,那么,康德在审视人类已有的文学成果的时候,发现那些被称为天才杰作的,往往不是注重纯粹的形式美的作品,而是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作品,所以他又将票投向了“依存美”。另一方面,“纯粹美”毕竟是美之为美的规定性,如果脱离这个美的家园太远,就可能以哲理摧毁了这个美的家园,一些说教性很强而人们很难读下去的文本往往在这里失足。因此,怎样把握这个黄金的度,就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