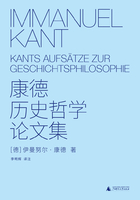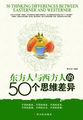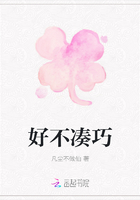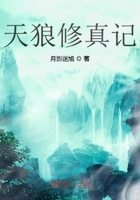既然艺术幻象的真正功用是作为“抽象之物”,作为“象征”,即“思想的荷载物”,它与实际之物的根本区别也在这里;那么,这种抽象又是如何进行的呢?朗格认为,呈现事物于视觉而终被作为幻象为人了悟,是从通常环境中抽取可见形式的一种便当(然而决非必要)的方法。在艺术中,形式之被抽象仅仅是为了显而易见,形式之摆脱其通常的功用也仅仅是为获致新的功用,即充当符号以表达人类情感。但人们在理解艺术时常常认为形式与本质“内容”相对立。朗格认为,关于形式与内容的问题,是可以找到解答的。因为,第一,艺术作品是一种其相关因素常为本质或本质特征(如它们强度的大小)的结构;第二,本质进入了形式,本质从而与形式合二而一,如同本质所具有而且所仅有的关联一样;第三,说本质是形式在逻辑上赖以被抽象的“内容”毫无意义。形式借本质特有的关系而建立,本质是艺术结构中的形式因素,而不是内容。 这样以来,形式既为空洞的抽象之物,又具有自己的内容。即是说,艺术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内容,即它的意义。在逻辑上,它是表达性的或具有意味的形式。它是明确表达情感的符号,并传达难以捉摸却又为人熟悉的感觉。它作为基本的符号形式存在于与实际事物不同的范畴之内。它与语言同属于一个范畴,虽然两者的逻辑形式互不相同,也与神话和梦同属于一个范畴,虽然两者的功用也互不相同。这样的一种艺术幻象是如何抽象的呢?朗格以延伸的线条为例进行了说明。她认为,一方面,在某些完全静止的线性图案里,虽然没有什么变换位置,却有某种运动产生;另一方面,在运动实际发生的地方,即使它没有留下痕迹,也仍然规定了一条持续不断的概念上的线。如跑动的老鼠似乎跑过了地板上的路,那条静止的、假想的线似乎也在延伸。其道理就在于:两者都体现了抽象的趋向原则,借助这一原则,它们在逻辑上得到一致,即互为符号。我们平常放眼观看以了解事物时,一直让它们互相代表而不自知。这正是一种在非推理层次上呈现的机能,它早在得到科学手法的承认之前就为人察知了。因次,朗格说道:“运动在逻辑上与线性形式有关;而且,在线条连续、支承的图形又倾向给它以方向的地方,人们对它的感知就充满了动的概念;那种感知通过对实际感觉材料的印象而突现出来,并在统觉(apperception)中与它融合在一起。其效果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艺术幻象(并非幻觉,因为它经不住分析,而幻象却经得住),我们称之为‘生命的形式’。” 朗格十分赞赏音乐家罗杰·塞申斯(Roger Sessions)在其《作曲家及其信息》一文中的分析:“视觉艺术控制着一个空间世界,而我们得自空间的最深刻的感觉,我认为也许不属于扩张,而属于永恒。在最本原的层次上,我们觉得空间是某种恒久的、根本不能发生变化的东西;运动通过眼睛而为人了解时,永恒就产生了,可以说它是在静态的框架中产生的。这一框架在心理上的影响,远比它局限之内的运动更为有力。”朗格认为,正是这种“运动在永恒中”的双重性,实现了纯动力的抽象,创造了生命的表象,或者说,创造了维持其形式的活力。逻辑意义上的“表现”,亦即概念通过富于表达力的符号的呈现,这就是艺术的主要功能与目的。
在朗格看来,组成艺术作品的幻象并非特定材料在产生审美趣味的形式里的纯粹排列,而是这一排列所产生的东西,并且确系艺术家所创造的、并非发现的某种东西。符号始终是创造出来的某种东西。因此,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提供并维持这种基本的幻象,使其明显地脱离周围的现实世界,并且明晰地表达出它的形式,直至使它准确无误地与情感和生命的形式相一致。为此,艺术家可以使用任何能够作技巧处理的材料——如乐音、色彩、可塑物质、词语、姿势或其他实际手段。所以,表象的创造和生命形式在其框架里的明晰表达,就成了艺术领域主导性的论题。
其次,关于艺术幻象的特征,在朗格的论述中有两点是特别重要的,这就是“他性”和直观性。所谓“他性”(otherness),朗格解释道:“这是包罗作品因素如事物、动作、陈述、旋律等的幻象所造成的效果。即使在诉诸表现的因素缺乏的地方,即没有什么被模仿、被虚构的地方,如在一块可爱的织物上、一只奖杯上、一幢楼房上或一段奏鸣曲里,这种虚幻的即充当纯意象的神韵,也依然如在最逼肖的绘画或最动听的叙说里那样强烈地存在着。” 很显然,“他性”就是指一种离开现实的虚幻的充当纯意象的神韵。朗格指出,关于这个“他性”,已经出现了种种描述语,如“奇异性”、“逼似”、“虚幻”、“透明”、“超然独立”、“自我丰足”(self-sufficiency)等。朗格极其重视“他性”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种脱离现实的“他性”——它甚至给实际的生产品如一幢楼房或一只花瓶以某种虚幻的光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它寓示着艺术的本质。因此,艺术家们一次又一次地考虑它。也正是在这种非现实的因素中,有一个通向非常深刻、极其本质的问题的线索,这就是关于艺术创造力的问题。甚至在谈到艺术的抽象形式时,朗格还一再强调:“首先要使形式离开现实,赋予它‘他性’、‘自我丰足’;这要靠创造一个虚的领域来完成,在这个领域里形式只是纯粹的表象,而无现实里的功能。其次,要使形式具有可塑性,以便能够在艺术家操作之下去表现什么而非指明什么。达到这一目的也要靠同样的方法——使它与实际生活分离,使它抽象化而成为游离的概念上的虚幻之物。”
在朗格看来,正是这种代表艺术对象特点的“奇异性”或“他性”,使艺术形式具有了一种两重性:形式直接诉诸感知,而又有本身之外的功能。它是表象,却似乎荷载着现实。正如语言那样,它不过是响度不大的营营之声,却充满着本身的意义,而它的意义即为现实。朗格认为,在一个富于表现力的符号中,符号的意义弥漫于整个结构之间,因为那种结构的每一链结都是它所传达的思想的链结。而这一意义则是这一符号形式的内容,可以说它与符号形式一起诉诸知觉。
有时朗格还把艺术独有的“奇异性”称作“透明性”,认为这是艺术具有符号性质的证明。如果被模仿对象的意义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这一透明性就会在我们的面前隐遁而去,于是艺术作品呈现出实际的意义,并引起我们的情感,从而掩盖了艺术形式的情感内容,即逻辑地表现的情感。当然,这是表现上的危险。但艺术大师的作品,其表现形式则十分得心应手,其透明性则十分清晰醒目,使得举凡已发现艺术含蕴现象的人无不有此见解。奥特加在其《艺术的非人化》一文中就指出:“人们大多不能调整对玻璃加透明性——艺术作品的注意,而是透过艺术作品痴情地沉浸在它所涉及的人类现实之中。如果有人劝他们放弃那种执着的追求,而专门去注意艺术作品本身,他们就会说他们一无所见,因为在他们眼中,那里没有人类现实,只有艺术的透明性,即纯粹的本质。”朗格赞赏奥特加的观点并进而说道:“艺术作品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所有美好的事物,就因为它是‘玻璃加透明性’,这即是说,在任何有关的情况下,它都根本不是一种事物,而是一种符号。” 而要使艺术幻象做到透明,就如朗格所说的那样(前文已有引述),要在艺术创造中抽象形式,摒弃所有可使其逻辑隐而不显的无关因素,特别是剥除它所有的俗常意义而能自由荷载新的意义。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使形式离开现实,赋予它“他性”;这要靠创造一个虚的领域来完成。其次,必须是形式具有可塑性,以便能够在艺术家操作之下去表现什么而非指明什么;这同样要使它与实际生活分离,使它抽象化而成为游离于概念之上的虚幻物。
综观朗格对艺术幻象“他性”特征的论述,可以看出其重点在强调艺术作品所创造艺术形象与现实事物的区别,她对模仿理论持否定的态度,明显具有反自然主义艺术观的倾向。这当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她主张艺术幻象必须具有与现实世界相脱离的倾向性,正表明她是从一个更高的水准上去把握现实、透视现实,而不是被现实所左右,仅仅以模仿现实为务。同时,她的理论也与根本脱离现实或抛弃现实的“自我表现”观保持了距离。
艺术幻象的另一个特征是直观性。所谓直观性,就是指幻象的具体可感性和生动形象性。从最后结果看,它类似于镜子中的物象,但它是经由艺术家的主观创造与转换而成的。朗格对此论述道:“意象纯粹是虚幻的对象。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并不用它作为我们索求某种有形的、实际的东西的向导,而是当作仅有直观属性与关联的统一整体。它除此而外别无他有,直观性是它整个存在。” 朗格认为,“意象”一词几乎与视觉形影不离,这是因为我们说起它就千篇一律地以镜中之象打比方,而镜中映象除在目击时与镜前物象一模一样之外,却不能诉诸触觉和其他感觉。因为艺术中一切形式均为抽象的形式。它们的内容仅是一种表象,一种纯粹的外观,而这表象、这外观也能使内容显而易见,也就是说内容的表现会更直率、更完整。艺术幻象是对虚象的提炼、抽象与升华,它内含了某种具体事物的本质特征,反映了具体事物的一种关系结构,因而它具有某种具体的理性特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切艺术都是抽象的。艺术的实质即无实用意义的性质,是从物质存在中得来的抽象之物。以幻象或类似幻象为媒介的范型化使事物的形式抽象地呈现它们自身。” 这也就是说,艺术幻象的直观性中含蕴着深刻的理性与抽象因素。
在论述艺术幻象的特征时,朗格多次运用了诸如幻象、虚幻的意象、意象、表象、纯表象等一系列概念与范畴,这些概念与范畴的含义是否完全相同呢?只要认真研读朗格的着作就会发现,作者对表象与意象的基本内涵还是作了某种程度的界定的。说到表象,她认为,“每一事物都有一个方面的外表,以及一个方面的因果价值。即使像一件事或一种可能性这样非感官觉察之物,也似乎是对这个人这样,对那个人那样。这就是事物的‘表象’,人们借此说此物与彼物‘相似’,也借此说事物与其本质‘不同’。”当说到幻象时,她则认为,“如果我们了解到一个‘对象’完全由表象组成,即除了表象之外它无法聚合,无法统一,如彩虹、影子,我们就说它是纯粹虚幻的对象,或者幻象。在这种精确的意义上,一幅画就是一种幻象。我们在上面看到了一张脸、一朵花、一片海景或一处陆地风光等等,也知道伸手触摸就会碰到涂抹颜色的画面。” 这种看见的对象仅止诉诸视觉(如“写生”或“写实”画的主要目的即是)。凡呈现事物于视觉的最后往往要作为幻象被人了悟。而表象通常不致使人产生误解,一件东西就是它那个样子。但朗格也指出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对象如一只花瓶或一幢楼房也可能专门刺激人们的一种感觉,以致使人除了这一感知而外觉察不到其他所有的特点。它还是它,没有耍什么花招,但它却只对于一种特点譬如说视觉特点有重要意义。于是,我们倾向于作为视见之物来接受它。在事物的外表上,视觉特点是如此集中,结果人们有一种纯见外表的感觉,即觉察幻象的感觉。朗格认为,这里面包含着艺术的“非真实性”,它甚至给完全真实的物体如罐子、织物、庙宇等也染上了非真实的色彩。我们无论观察实在的幻象,还是观察经艺术家强调的这种类幻象(Quasi-illusion),在两种情况下所呈现出来的无不是席勒所说的“纯表象”。朗格把纯表象看作“在自然世界丰富多彩的现实中是一位陌生的客人”。它醒目的标签是:奇异、离异、他性等,你愿意叫它什么,就叫它什么。